理雅各:中国经典西译的一代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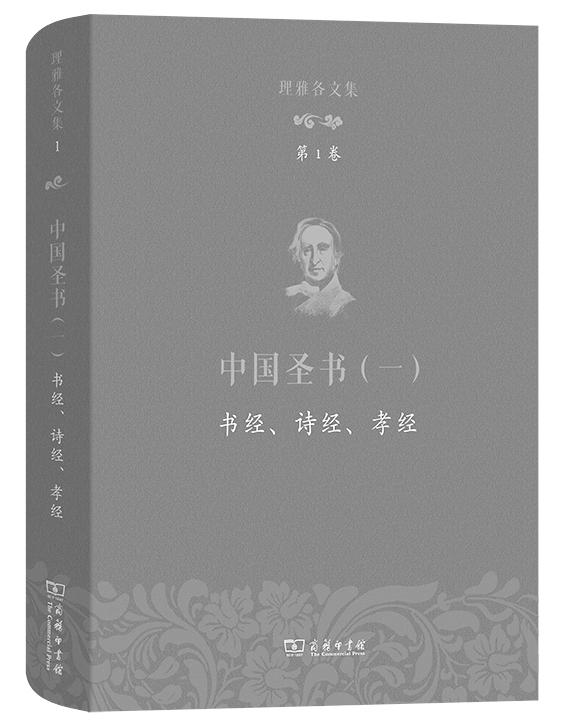
1873年,欧洲首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巴黎召开,肯定了法国从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到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汉学成就;次年,第二届大会在伦敦举行,已从中国返回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成为核心人物。“伦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东方学、比较科学以及汉学研究成就的火炬,已经从欧洲大陆传递到英国。这是汉学研究的一段进程,也可以说从儒莲时代,进入理雅各的新时代。理雅各最终返回英国的1873年,也是伟大的儒莲在巴黎辞世的那一年。”
理雅各1840年抵达马六甲,1873年从伦敦会退休,1897年去世。他终生勤奋治学,每日四点起床写作的习惯直到晚年都未改变;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作为19世纪西方汉学大师与中国经典英译的实践者,理雅各在整个西方汉学史和中国经典外译史上的学术地位都不可动摇。
首先,在翻译数量上,他前无古人。西方汉学史上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始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传教士。其中集大成者、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1)的代表作是《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显然在数量上无法和理雅各相比;新教传教士的中国典籍翻译则是零星展开的。而理雅各从1861年起便在香港出版五卷本《中国经典》,收录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1875年与马克斯·缪勒(Fr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合作,为其主编的《东方圣书》贡献了六卷本的《中国圣书》,译注了《书经》《诗经》《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中国重要典籍。此外,在牛津期间,他还先后翻译了《佛国记》《景教碑》,写出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等著作,开展了一系列汉学讲座,并修订了早年译作《中国经典》,完善了自己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即便在整个17至20世纪西方汉学史中,他的学术地位也举足轻重,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顾赛芬(Couvreur Seraphin, 1835-1919)并称为中国古代经典三大翻译家,且翻译数量居首。
其次,理雅各译本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1875年,他荣获首届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得到了欧洲汉学界的权威认可。汉学家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 1838-1908)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中评价道:“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抑或国外,没有一个外国人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经典之花的熟悉,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在可靠性上,能够与理雅各博士相匹敌。”
更重要的是,理雅各开创了英国汉学的新时期。19世纪的英国汉学尚处起步阶段,理雅各来到牛津大学任教。他的到来使汉学成为“英国学术界第一次在东方学的学科海洋中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同时,他和欧洲汉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教授(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代表作《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的热情赞扬,对青年汉学家们的帮助,都显示出一位长者的大度与宽容,这些都提高了英国汉学的地位。1893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荣誉研究员头衔,足见他在欧洲汉学界的地位。即便是曾与他有过争论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其去世后也坦言:“理雅各的著作对中国研究是最伟大的贡献,在今后的汉学研究中,人们将铭记他的贡献。”
作为19世纪西方汉学家的代表,理雅各通过翻译中国经典,表达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这些观点的形成,与其广泛阅读中国历代经典注释著作,特别是清代学者的训诂著作密不可分。在相关研究中,理雅各也表达了他的学术见解。将这些观点和见解纳入中国19至20世纪的学术史框架下考察,其价值更得以凸显。例如,他对《春秋》真实性的评论与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疑古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理雅各翻译的《春秋》出版后,“中国学术界首先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经今文公羊学派,他们对于《春秋》《左传》的态度与理氏正好相反。……到了本世纪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一切儒家经典都被视为过时的历史垃圾,激烈抨击的程度不知要比理氏高多少倍。尽管疑古学者与理氏在正面的方向指引上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同视中国文化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了,在这一点上双方则完全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把理氏对于《春秋》的见解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远见,他竟然先于当时中国学者而有见于此。当然,那也并非理氏个人的见识高于当时中国学者的问题,差别在于他和中国学者身历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
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大大开拓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疆域,展示了中国文化研究走向世界后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将他们的研究纳入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思考?如何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路数和话语?如何在与其对话中合理吸收其成果、推进本土研究的发展,并坚守中国本土立场、纠正其知识与观点上的不足?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自说自话已经不再可能,随汉学家起舞显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立场。从陈寅恪提出的“预流”到清华国学院的“汉学之国学”,前辈学者都有所尝试。今日的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仍显准备不足,十分可喜的是继刘家和先生之后,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理雅各的汉学成就,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相较于儒莲所代表的欧洲汉学界,前者的治学更得益于中国的实际经验,尤其是1873年的华北之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中国文人的密切合作,对此,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 1951-)教授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详细考辩了理雅各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与互动。其中,因太平天国关系于1862年逃到香港的晚清学者王韬,对彼时在香港布道的理雅各翻译后三卷《中国经典》,尤其是《诗经》,大有助力。理雅各在谈到王韬时说:“有时候我根本用不着他,因为一整个星期我都不需要咨询他。不过,可能有时候又会出现这样的需要,而此时他对我又有巨大帮助,而且,当我着手撰写学术绪论的时候,他的作用就更大了。”王韬也盛赞理雅各:“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正如余英时所说:“理雅各如果不到香港,他便不可能直接接触到当时中国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译注的学术价值将不免大为减色。另一方面,王韬到香港以后,接受了西方算学和天文学的新知识,这对于他研究春秋时代的历法和日蚀有莫大的帮助。”
理雅各在19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个介乎传教士汉学家和专业汉学家之间,或者说从传教士汉学家转变为专业汉学家的代表。这种身份使他对中国经典有着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直接反映在其翻译之中。
在香港期间,理雅各翻译的立足点是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一神论信仰,在《五经》中有着和四福音书类似的信仰。这一观点将他的《中国经典》翻译事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敬与其每日的布道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如他所说:“传教士们应当祝贺他们自己,因为在儒家思想中有那么多关于上帝的内容。”这样的一个立足点自然使他对孔子、孟子的评价不高。在对《春秋》一书的翻译中,他对孔子的看法表明了他的文化立场。最初他相信此书为孔子所作,后又转而否认,并在《中国经典》第五卷的绪论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证明《春秋》非孔子所作。直言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促使中国人“离开孔子而另寻一位导师”。这一中国古代文化观并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继承了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适应政策”——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和西方一样的“上帝信仰”,传教士的任务就是唤醒中国人的这种信仰。所以,崇先儒而批后儒成为利玛窦的基本文化策略。理雅各在华期间在译名问题上坚持用“上帝”,晚年翻译《景教碑》时,也延续了利玛窦的调和思路。
离华前的华北之行与返回牛津后与比较宗教学家缪勒的共事,成为理雅各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缪勒在第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提出:“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还有别的宗教、别的神话、别的法则,而且从泰利斯到黑格尔的哲学史,并非人类思想的所有历史。在所有这些主题上,东方都为我们提供了平行的相似性,即在所有包含在平行的相似性之中的比较的、检测的和理解的可能性。”显然,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连在一起的,尽管这种对异文化的宽容,仍以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为比较基准,但它已承认了文化的多元性,承认了“还有别的世界,还有别的宗教、别的神话、别的法则”。这已经走出了基督教思想具有唯一性的狭隘理解。受缪勒比较思想的启发,理雅各获得了重新理解中国思想的角度和方法,并据此在《东方圣书》中重新修订出版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
如何看待理雅各的文化立场呢?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1943-)将“理雅各主义”称为“汉学东方主义”,但这一后现代思潮的标签难以涵盖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中国学术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者看来,理雅各直到晚年仍未透彻地理解中国上古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关联、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从而无法解释儒家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对孔子地位的起伏与变迁,很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给予合理的说明。同时,他的翻译也有许多可商榷之处。
尽管“理雅各将自己整个生命用来发现、理解和评价这个古老的中国世界”,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他者”,他在苏格兰时期所奠定的世界观,即“苏格兰常识哲学学派,特别是此流派与福音教会形式的新教世界观之间的关联,业已成为了他强大理智的全副武器”。理雅各永远不可能像一个中国学者那样来理解中国文化,在他对孔子的解释中呈现出其文化本色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他者”作为“异文化”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永远是其所阅读和观察的文化,反思自身和确立自身的对话者。跨文化之间的“误读”是文化交流与思想移动的正常现象,对于这种“误读”,既不能将其看成毫无意义的解释,或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扭曲的铁证;同样,也不能因为这些架起东西文化桥梁的人的辛劳和对中国文化的尊敬而忽视他们的“误读”。简单套用西方学术界“乌托邦”“意识形态”等概念来审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或解读文化间的“转移者”的复杂心性与特质,显然难以触及本质。对西方汉学研究而言,方法论层面亟需理论创新——不加批判地移植西方流行理论,用以阐释西方汉学史上的复杂人物与多维进程,终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汉学史上对理雅各的评价是复杂的,他的立场始终受到来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的批评。无论是理雅各坚信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宗教性,还是当代汉学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理雅各所认同的中国古代思想宗教性的论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都困扰着西方汉学家。用“东方主义”是说不清这种文化间移动的复杂状态的,我们必须看到理雅各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最有影响力的翻译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变化、最终呈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底色的坚持与对东方文化的重新理解,都是文化间移动的必然产物,这些都必须从跨文化的角度给予理解和解释。
因此,要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放入西方近代思想史中考察,这样的翻译研究绝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技能问题,而是西方对东方思想的理解问题。但这只是我们考察中国经典外译的一个维度,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从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推动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角度看,理雅各的工作是伟大的,是前无古人的。他是19世纪后半叶西方汉学的真正领袖。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理雅各去世后曾这样评价:
如今,甚至即便在理雅各已经离开了我们,不再与我们一起的时候,他殚精竭虑经年累月的付出,那些卷帙浩繁的译著,依然包含着丰富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欧洲和美国的观察者可以如此正确地判断中国人,……,这些儒家经典通往普遍的中国思想。将这些书置放在那些绝望地看着《孟子》或者《书经》某一页的人手上,就是一种最坚实的服务,一个最为有用的成就。
为系统整理理雅各的学术遗产,《理雅各文集》应运而生,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系统整理和翻译理雅各的译作、著作、手稿和档案文献。文集共15卷,由张西平、费乐仁任总主编,潘琳、丁大刚任分卷主编。
第1—6卷影印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圣书》,包括《书经》《诗经》《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并附费乐仁所撰“导读”与“索引”。赵倞、刘霁、顾庆瑞等人参与了翻译。
第7卷编译了《中国经典》的“序言”与“导论”。因《中国经典》已影印出版,故文集不再收入。
第8卷收录了理雅各的牛津讲稿与期刊论文。杨慧玲、程熙旭等人参与了翻译。
第9卷整理出版了理雅各指导何进善翻译的《正德皇帝游江南》和理雅各的《河南奇荒铁泪图》《佛国记》《景教碑》等译著。其中,《佛国记》的序言、导论和注释由法显研究专家张梁(笔名东夷)翻译。
第10卷为理雅各的游记、自传、他传等。
第11卷辑录了理雅各晚年的未刊翻译手稿和两份藏书目录。
第12卷收录理雅各自1830至1890年代所写的信件,另附部分回信,便于读者了解某些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第13—15卷收录理雅各的宗教研究论著及手稿。
这部筹备十余年的文集,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支持:理雅各的重孙克里斯托弗·理雅各(Christopher Legge)授权了早期在牛津大学的档案复制;费乐仁为文集的出版倾注了很多心血,并撰写了35万字的导读;潘琳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文献复制时,曾得到傅熊教授(Bernhard Fuehrer,1960-)及夫人的热心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辛岩老师翻译了《中国的宗教》以及《中国人的鬼神观》初稿;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现名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杨慧玲、康太一等师生都参与了翻译工作;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斌老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拍摄了《理雅各牧师书房存书目录》;上海师范大学的多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文献录入和整理工作;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各位编辑也为文集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十载耕耘,十五卷巨献,然而受限于篇幅,诸多相助者难以尽列,谨此一并致谢。此外,要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鼎力支持,没有北外的慷慨资助,本文集将不会有机会问世。
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华文明的研究,当以学术史的梳理、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为基础,唯此才能展现文明互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