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文学遗产》(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聘为编委,赴京参加座谈会。当时,担任副主编的张白山先生主持会议。被聘为编委的,在座还有傅璇琮先生等好几位,都是和我年龄相若,四十岁开外的学人。
会议间歇时,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免不了围在一起聊天。这才知道,我们都是在“文革”前,担任过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通讯员,也不约而同想起了前主编陈翔鹤先生。后来,这些通讯员,大多成了各高校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骨干。
一
1952年,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记得王季思教授在给我们上写作课时说:“以后如果你们发表文章,不要忘记,其中有一半是编辑同志的功劳。”当时,我才读一年级,曾大惑不解,文章明明是我们自己写的,怎么能说编辑先生有这样大的作用?后来,我有幸遇上陈翔鹤先生,才理解王老师所说的是至理名言。当我和璇琮兄等几位,谈到陈翔鹤先生时,都一致认为,当年以陈翔鹤为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正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成长的摇篮,是教育我们学会做人做事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我能认识陈翔鹤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
那时候,学校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要撰写“学年论文”。我在求学阶段就对中国古代诗词很感兴趣,加上二年级时刚学过魏晋文学史,又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陶渊明集》,于是,三年级伊始,便开始研究陶诗,学写论文。上学期快结束,论文《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特征》写成了。那时正在提倡“向科学进军”,到寒假,我把论文重抄了一份,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
老实说,当时我属于“黄毛未褪”的大学生,在图书馆里,常见到与文学有关的期刊,不外是《文艺报》《人民文学》《语文学习》等几种,只有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才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我不知高低,也不懂得它在学术界中的分量,随手贴上邮票,把稿子塞进邮箱,寄交《文学遗产》编辑部。那时,女朋友知道了,便嘲笑我说:光明日报的一个版面,最多能刊载八九千字的文章,你的论文却有一万四五千字之多,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等着退稿吧!我一想,她说得有道理,但稿件已成泼出去的水,只好自认晦气,噬脐莫及,不敢作刊登之想。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一封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寄来的信,信很薄,不像是退稿,我心情忐忑,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只有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只署名“编者”。
这编者是谁?我不知道。后来才晓得,这封信原来是当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给我的。
我看了信,满脸通红。确实,我一向做事马虎,不重视写字,况且想趁假期外出游耍,心不在焉,便“龙飞凤舞”地抄了稿子,塞进邮筒。看了信,我想,完了,编者这样严厉批评我的文稿,哪里还会采用?那就等着退稿吧!我的女朋友倒看得细心,她认为排字工人在骂,不是有可能在发排吗?我一想,似乎有理,于是以后每周都找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留意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连翻了两三个月,没看到,我心也就凉了。正好那时董每戡老师建议我转攻中国古代戏曲,我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
谁知到了学期之末,我又收到《文学遗产》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是《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我的论文,就登载在有关陶渊明研究的一组文章上。原来,陈翔鹤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认为一些可取而又篇幅较长的论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版面容不下,于是另辟《增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抽屉里找出陈先生给我的信,又看看被采用的论文,不禁百感交集,既高兴,又羞愧;既感动,又震动。试想,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百务烦冗,竟不惮劳烦,对一个陌生青年抄写的潦草得像“鬼画符”般的文稿,耐心阅读,这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而当发现文稿有一得之见,既严肃批评,又注意栽培。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一位胸怀如此广阔,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的老师。
二
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就接到《文学遗产》的通知,告诉我被聘为编辑部的通讯员,以后每周给我赠阅该刊。而通讯员的任务,是要阅读该刊的文章,征询师生们的看法和对编辑部的意见,每月写信汇报。这一来,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必须仔细阅读,不敢囫囵吞枣,也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当然,在书写通讯稿时,更注意字迹端正,再不敢潦草苟且,写得像“天书”那样了。过去说字如其人,写字时心态的改进,也让我端正了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
到1958年暑假,我到天津探望在那边工作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老伴),和她一起到北京游览,逗留一周,也抽空去看看《文学遗产》编辑部。我不敢惊动陈翔鹤先生,只想访问一下这名闻全国的期刊。作为通讯员,也顺便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谁知那天下午,陈翔鹤先生正好也在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来了,很高兴,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也是唯一一次有幸和陈先生接触。只见他个子较矮,身材略胖,穿着灰色的干部服,眯着眼睛看我。我有点紧张,甫坐下,他过来给我递上一杯茶,笑着说:“好呀!写‘天书’的来了呀!”我手足无措,他却哈哈一笑,说:“你写来的通讯,我看了,写得认真,字也写得好多了!”听了这几句话,我绷紧了的神经,才松弛了下来。
陈先生问了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也问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的近况。大约谈了十多分钟,他站了起来说:“天骥同志,我有事,正忙着,不陪您了!这样吧,我让刘世德陪您吃饭,由我请客。”我一怔,正想推辞,他却不由分说,把刘世德同志叫了过来,吩咐他带我俩去吃晚饭,并且说:“天骥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他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要吃得好一些,贵一些不要紧!”
我在《文学遗产》上,早就拜读过世德兄的论文,这回第一次见面,看到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年纪也比我稍大,顿生敬意。当时,他正在《文学遗产》当实习编辑。我跟着他走出编辑部,他便问我,想吃些什么,不必客气。我心想,北京的烤鸭最有名,我从未吃过。又一想,烤鸭可能价钱很贵,怎好让陈先生花费太多。正迟疑间,世德兄和我商量,不如到莫斯科餐厅,那里比较清静。我虽初到北京,更未尝过俄国餐,但在广州时,却早知道近来“莫斯科餐厅”在京开张,便欣然跟着前往。
我进入餐厅宽敞的大厅,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它虽然不是金碧辉煌的,却显得优雅大气;食客们都只喁喁细语,绝不像广州茶楼那般嘈吵喧闹。世德兄领着我俩,拣一个角落坐下,便问我想吃些什么?我哪里懂得该吃些什么,只见邻桌的食客,吃着一锅土豆烧牛肉,便指着要了一份;我的女朋友跟着我,也要了一份。当服务员把金光灿灿的铜锅端过来,揭开盖子时,扑面而来的是热气腾腾的肉香。那一年,广州供应已经很紧张,我久已不知肉味,也就不客气了,狼吞虎咽地把一锅土豆烧牛肉塞进肚里。我吃饱了。一看,女朋友只吃了半锅,便放下了刀叉。当时,还没有“打包”的习惯,她不再吃,浪费了岂不可惜!世德兄便劝我,把她剩下的牛肉全吃掉。那时年轻,无所谓消化道出什么问题,也就端过来一口气吃了。这顿饭,我饱得差不多撑破了肚皮,半天弯不了腰。细看世德兄,他只点了一份鱼扒,一份冰激凌,慢条斯理地品味。结账时,我不知他替陈翔鹤先生花费了多少?但肯定不会便宜。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顿饭,也许世德兄早已忘怀,但当时的每个细节,我一直记得。虽然,那时我还不至于沦为饿殍,但这“一饭之恩”,却让我明白陈先生了解广州食品供应的状况,明白他吩咐“要吃得好一些”的含义,更感激他从心底里流露出的对后辈无微不至的爱护。我也想,得到陈先生厚待的年轻人肯定不少,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到现在,我还学着陈翔鹤先生做人做事的态度。每当和那些还没有收入的学生吃饭时,一定首先说明由我“埋单”,也会让学生们点菜,说大家只管点,“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贵一些不要紧”。
三
在担任通讯员的几年里,我陆续收到了编辑部寄赠的几套书,一套是《聊斋志异汇评汇注本》,一套是《敦煌变文录》。到1962年,还收到一套由范文澜先生编注的《文心雕龙注》。在这套书中,附有编辑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写道:“通讯员同志:你们替编辑部做了很多工作,很感动,今后还望你们多加支持。现在编辑部买到了一批《文心雕龙注》,这本书想来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买,所以每位赠送一部,作为学习上一点微小的酬劳。”在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笔添上的两句话:“此书得来不易,望好好学习。”一看字迹,认得是陈翔鹤先生的手笔,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我明白,陈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正是以联系通讯员的方式,来培养各个高等院校年轻的学者。
在1961年岁末,我读到了陈先生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知道他对陶渊明有很深的研究;知道了为什么在五十年代中期,在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中,《文学遗产》启动讨论陶渊明问题的意义;知道了通过解剖这一只具有典型性的“麻雀”,可以辩证地历史地理解古代作家思想复杂性的问题。当年,我那稚嫩的论文能够发表,正好碰上了这机遇,而它又影响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影响了我的一生。
后来,我听说陈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严酷批判,含冤逝世。翘首北望,不禁泫然。我把《文学遗产》寄赠的三套书,排在一起,放在书架里当眼的位置,得以时常望见,纪念陈翔鹤先生对我的培养。
学人的成长,固然要靠学校、老师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同时,离不开出版部门编辑同志的栽培。像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的编辑,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私地耗费心血,他为了什么?无非是为国育材,发展文化事业!我虽然只见过陈先生一面,但他的栽培和教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年,是陈翔鹤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写下这篇短文,不仅是一己的感恩知遇,更是期望有更多的人,继承和发扬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做人做事的传统,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私奉献。
(作者:黄天骥,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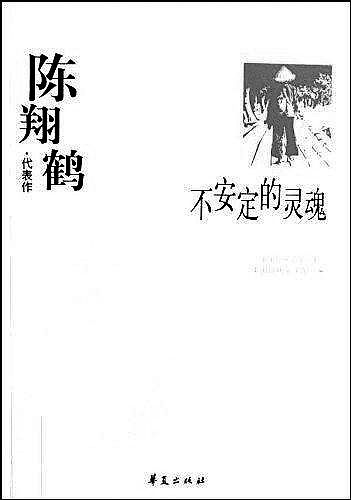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