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田野,哪会儿想来哪会儿心肠热乎。
那时的乡村孩子,吃不饱,衣服单薄,肚子里填的经常是清汤清水的菜叶粥。穿补丁衣,穿露脚趾鞋。补丁衣两边袖口结了嗄巴儿,鼻涕抹过的痕迹发亮光,露脚趾鞋像鲇鱼大张着嘴。脖子瘦得“蹦筋”,而黑得像“车轴”。可即便这样,最有想象力的现在的人们,也想象不出当初他们多么快乐。在广大天地间,他们如小虫子一般无忧无虑。
大片田野,是无须花钱买门票的大型“游乐场”,随处都是天然的游乐“设施”。没有水泥地,不怕摔倒;没有铁柱、铁架,不怕撞伤;可以由性儿奔跑、追逐,骑一根梢条当大马,不同季节,不同环境,随意“发明”各种“游戏”。游戏规则,可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变动。
春天,孩子的心痒得难受,四处逛荡,寻找玩玩乐乐的契机。夏天,深厚的绿铺天盖地,好玩的地儿玩不过来。三伏以后,秋的气象越来越繁华,好吃的好弄的不请自来。冬天冷也捆不住贪玩的手脚,受诱惑的派遣,款款心花处处开。
一年四季,大自然提供了游戏场地。大高坡暄土地,光脚丫演抬花轿、甩龙尾儿、摔跤、开土仗、撵兔子,学驴叫马叫牛叫大小羊叫,向天空吼;树荫底下“猜头家”,分出了先后,玩剋瓦、弹玻璃球、摔洋人儿、拍三角、斗草;土道上,滚铁环、抽汉奸、编柳帽、吹柳哨,进行打弹弓演习;小河中,摸鱼摸虾,捞苲草,打片儿溜,追灯油香油、黑老婆儿,捧蛤蟆骨朵儿;大秋有了柴草垛,玩藏闷儿哥、登草垛;大青杨的叶落下以后,玩赛老根儿和撞拐。在昆虫鸟兽活跃季节,少不了的是打长虫、掏鸟窝、粘唧鸟、粘蚂螂、捉刀螂、逮蝈蝈和大驴驹,拿柳条串蚂蚱。
特别要说的,还有几样。热天的雨停了以后,打谷场泥土地一片湿滑,孩子就去那里滑泥。光着脚,呱唧呱唧跑入场院,选在了正中位置,即开练。紧跑两步,停住脚,在惯性驱动下往前出溜,“嗞溜溜”滑出好远,像滑冰、滑雪一样畅快。脚丫巴里挤着泥汤。这项娱乐大人不太高兴,因为滑过了泥,场院就不整洁了,净是脚趾头杵的道道泥沟,干了硬邦邦的铲脚。逗疥蛤蟆不碍大人的事。在场院一角用竹批儿或瓦片剜一土坑,用木棍把一只疥蛤蟆拨进坑里,看它怎样爬。土坑不过半尺多深,因为是直上直下的“竖井”,蛤蟆无论怎样用功就是爬不上去。它东挪挪,西转转,急得撒尿却没有办法,特别可乐。春节前后,哪里都有积雪,雪地上常有散养的猪拉的猪屎。孩们兜里有炮仗,就想出“嘎主意”。见行人将要走过,就在猪屎上插上炮仗,掐算时间点燃了炮,崩起来的猪屎、雪面儿会溅人身上。男人还好说,若是溅在准备走亲戚的大姑娘小媳妇新衣上,就闯祸了。她们被吓一跳,还没顾发现衣服上的脏迹,孩子已经哈哈乐着逃走了。“谁家的孩子这么坏?”那通斥责甩在了身后。
孩子在野外淘气,也有受伤害时候。头一宗,就是蒺藜扎脚。那蒺藜像个什么?它整个是一荞麦型,但比荞麦粒大的三角体,上边的木质刺虽然不是很多,但无论怎么搁,总有一面朝上,总有刺儿戳着。路边,野地,哪处都有,爱光脚男孩总会遇上。木质刺虽然不长,但因为有药性,扎了脚生疼生疼,男孩就吸溜一口气,屏住呼吸坐地,把蒺藜拔出脚。酸枣树爱住马蜂窝,捅马蜂窝。虽然有柳帽伪装,但马蜂数量不会少,招惹了马蜂,必然受到报复。如军团一样的马蜂群不离头部左右,给抱头鼠窜的孩儿狠狠一嘟子。挨了蜇,脑门很快鼓一个包,变成了“大哞牛”——不信哪个小孩没挨过马蜂蜇。多种树上有蟪子,数核桃树蟪子毒性大。挨了蟪,那块皮肤发凉,起鸡皮疙瘩,一片起疹子似的红点发的痛痒能像电流,传至胳肢窝或大腿根,隔很长时间,蹭了伤处还会隐隐作痛。
自然界与大人传授,教给了孩子疗伤办法。比如,挨了蟪子蜇,就用鞋底将蟪子碾烂,用那绿汁儿抹上,伤口就减少酥酥地痛了。使用镰刀不小心划了口儿,不必惊骇,掏出小鸡鸡朝血口子尿尿。急射之下,冲了一冲,再随地抓一把黄土敷上。摁一会儿,就止血了。不知啥叫感染、发炎(那时的土地没有污染,土地干净)。陆地有什么,河里有什么,孩子蹚水,腿腕常被蚂蟥叮上。这虫子太讨厌,吸附能力太强,它叮了以后,脑袋深陷肉里,你就是把它身体扯断,它的头还在肉里边。孩子懂,不揪,用凉水掴;掴一掴,蚂蟥就突噜了。
田野上,山好,水好,村边有小河的更好。而那时乡村,泉水有多清澈?老辈冠名叫“甘池”的多极了,水质如何,不用细说。处处是玉泉山嘛!下过了连日雨,小河涨水,裸露的岩层湿漉漉的滴水。把嘴挨上岩层,直接着吸——那叫“控山水”。放羊的孩子把羊领到水潭,在羊饮水的时候,就挨着羊蹄,蹲着捧起水,咕哒咕哒地来上一气,别提多过瘾。有河,自然要学游泳,而小孩光会“打扑腾儿”。手乱抓乱挠,抬起俩脚丫拍打水面,击浪花。有的将长裤腿用榆梢扎紧,抻开裤口朝下一掼,充上了空气,成饱饱的了。着了水的布丝不容易跑气,就扎上口,就成一艘游艇了。头仰在卡巴上,其乐无比。
不贪吃的小孩,不像小孩;不会识别五谷杂粮和人能吃的树叶树花的小孩,不是农村长大的小孩。
田野岂止是一大型游乐场呢,它更像是一个场面开阔,可黏手而来的大型“超市”。在那样的一个超市,无照价付款一说。摘桑葚、摘青杏儿、摘巧瓜儿、摘欧洛儿、摘羊叶角、嘬小鸡喝酒;啃甜棒儿、吃酸枣、吃青核桃仁、吃冈儿挑和野葡萄;钩烘柿、钩黑枣、钩皮豆、搜寻黑裙儿和红姑娘秧……样样物事,都发生在应季。不怕吃着“中毒”。
最是偷吃瓜果梨桃和一些庄稼作物使人害羞。瓜园看得紧,小孩就与看园老汉演“孙庞斗智”。另支小分队入了地,扽着瓜秧就往回跑,拖回的瓜有时是生瓜,里边还是白瓤呢。长大以后才明白长辈人为何说“瓜熟蒂落”、“强扭的瓜不甜”。有时得手抱回几个好瓜,非常喜悦,个个往饱了吃。撑得弯不下腰,就找个斜坡,头朝下,控一控肚儿。“偷瓜偷枣不算贼,逮着挨一顿王八捶”,孩子有这句话壮胆。麦子过了乳熟期,进入蜡熟期,是很好吃的。揪一兜麦穗,一穗穗在手心揉搓,将麦粒挤出来,吹走了麦鱼儿,一手心的净粒,像一个个小胖猪儿。上口嚼,黏黏的香。玉米粒刚定珠儿,那味道是甜的,孩子就掰下玉米棒儿“吹横笛儿”,嘴角流玉米珠的白浆儿。芝麻干了角儿,上部敞开,四棱型芝麻角儿像朝天喇叭花,孩子就哈下腰,手把着“花嘴”往嘴里吸芝麻。白薯还没到刨的时节,但埂上裂了口,表明结白薯了。用手抠开裂缝,把薯块掏出来。你找棍儿,他找草,找最容易引燃的东西,另挖个坑儿,放上柴草,搁上薯块,架火烧。火燃尽,再蒙上几把土,等着焖熟。耐心等待的时候,田野散发烤白薯的甜香。几个玩伴黑着嘴回家。
若是孩子只顾贪玩,只顾淘气,不顾家,那是不对的。孩子也没那么做。不管有没有大人指使,他们念家的心很重。他们知道怎样为家庭出力。捋榆钱、捋榆叶、捋槐花、捋白薯叶;旱地找黑豆芽,大田找黑疸;捡麦穗,捡谷穗,拾豆子,拾花生,拾白薯,供给家庭“生活物资”。在贫穷年代,饭桌上“丰盈”有着孩子的一份劳绩。并且,他们老早老早就胜城里孩子一筹,能够识别谷子和“莠草”,这两种植物在幼苗期极易混淆。
田野是乡村孩子开蒙的大课堂,每个孩子都享受到了大自然的温情教育。寒暑假不必上辅导课、才艺班,大量时间置身野外,在“漫长”的假期,有自行热闹的空间,而且节目很丰富。长大成人,脑子里储藏的记忆,几乎都和田野、溪流紧密相关。
(作者:董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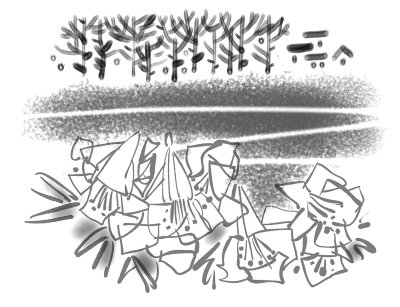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