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前的记忆,模模糊糊,影影绰绰。遥远的一片破碎的印象中,我叫爸爸的那个人,还有我叫伯伯的那个人,他们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轮流抱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后来,在若即若离的乡音中,他们把我安置在湘西一座叫洪江的小城中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里。
爸爸在安江的一家纱厂拥有股份,老盯在那儿,到了月底才回家陪陪我;姆妈大户人家出身,抽上了大烟,晨昏颠倒,整天懒洋洋的。与我做伴的,唯有一只温顺的小狗:天亮了,它用舌头把我舔醒;天黑了,它叼着我的裤脚,往我们一同睡觉的床上拖。不会说话的小狗和没人说话的我待在一起,在空空荡荡的大院里,我们显得既孤单又寂寞。
有一天,门口响起了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是送信的邮差来了。我迎到大门口,邮差叔叔对我说:“小姑娘,叫你爸爸妈妈拿图章来,领邮包。”姆妈正躺在床上过烟瘾,她美美地吐出一大口烟,乜一眼我踮起脚尖递给她的单子,说:“这是寄给你的东西,你自己去领,自己收起来。”
记忆中,我在湘西的那座小城待了四五年了,生活上,比如穿衣服啊,梳头啊,偶尔去小街上买点盐,打个酱油啊,我都能做了。但才五六岁,到底还是个孩子,是谁给我寄东西呢?在人们的印象里,收信和寄信,还有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邮东西,那可是大人的事情,我怎么也有这种好事?从邮差手里接过包裹,回到自己的房间,急不可待地打开一看,都是常用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小物品,有小鞋子、小袜子、小手套什么的。在床上摊开这些东西,我既高兴,又有点失望。你想啊,我是个长得比桌子还高一点的小女孩了,都有自己的好朋友了,给我寄东西的人也太粗心了,为什么不给我寄一些好看点、好玩点的?
之后,每隔一两个月,门口就会响起邮差叔叔丁零零的车铃声。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不识字,不知道邮包是从哪里寄来的,也不知道是谁给我寄的邮包。但邮局经常来送邮包,让我孤单的生活有了盼头,就像平静的湖面,突然泛起一朵朵美丽的浪花。
一次次收到的邮包里,最多的,是给我的衣服,偶尔也有糖果,还有用旧了但洗得很干净的布娃娃。奇怪的是,每次收到的衣服,都是用黄军装改小的;更奇怪的是,每次收到衣服,爸爸都让我穿在身上,带我到照相馆照相。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两张照片,一张穿着小八路的衣服骑在木马上,一张穿着截短的露出密密麻麻针脚的军大衣。
有一年,从春天到冬天,我都没有收到邮包,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了什么,不知不觉走出了院子,走到了附近街道上的小邮局。我踮起脚尖问柜台上的阿姨:“阿姨,有我的邮包吗?”叔叔阿姨们像见到一个小怪物,纷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你就是经常收到邮包的那个女孩吗?你可真有本事,是谁给你寄那么多邮包啊?”我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围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吓得要哭了。这时,经常来我家送邮包的那个邮差叔叔挤进来,蹲下身子,用大大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莫哭,孩子,这段时间真的没有你的邮包。”接着,他从人群里把我拽出来,推出自行车,让我坐在上面,一路摇着铃铛,把送我回家。
我有个小伙伴叫红莲,她的爸爸在邮局工作,就是常来我家送邮包的那个邮差叔叔。她家和我家在同一条街上,走几步就是邮局。一次,我看见红莲在玩一卷细长细长的电报纸,很是羡慕。红莲说,你也想玩对吧?那你得用东西给我换。刚好我收到的新邮包里有几个子弹壳,黄灿灿的,贴着嘴唇可以吹出呜呜响的声音。我送红莲一个弹壳,她送我一卷电报纸。我们坐在邮局的台阶上,各得其所,玩得很开心。
和蔼可亲的爸爸回来了。奇怪的是,他一回到家,就走进我的房间,掩上门,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经常和街上的孩子玩,还往邮局跑?现在一条街上的人都在议论我们家多了一个女孩子。你知不知道,这太危险了!”我被爸爸吓坏了,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从此再也不敢出门了,直到爸爸血肉模糊地被人抬回家。
原来,爸爸老不回家,不光是在纱厂忙活,他还到处为八路军筹集物资。这次,他去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送药品,不幸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伤了。离世前,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他和姆妈只是我的养父养母。我的亲爸爸,是赫赫有名的贺龙将军,正率领八路军在前线打鬼子。我的亲妈妈也是八路军,我收到的邮包,就是她从前线寄来的。邮包寄来的衣服,是我爸爸妈妈用节省下来的军装改成的。所以,妈妈每次寄来衣服,养父都要带我去照一张相,寄给他们。养父不让我出门,是怕我暴露身份。我爸爸贺龙在湘西拉起了一支红军队伍,长期坚持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是他们的基本斗争方式。红军长征离开湘西后,一些躲藏的土豪劣绅,还有一些被杀了的土豪劣绅的家人都回来了,要是让他们知道贺龙贺胡子的女儿寄养在湘西,非要了我的小命不可。
养父刚去世,日本飞机飞到湘西来了,扔下一串串炸弹。有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邮局的屋顶上,熊熊火焰把天都烧红了。在小城没法生存了,姆妈和我汇进了逃难的人群中,俗称“跑日本”。
逃到湘西的另一座叫乾州的小城,我和姆妈隐姓埋名,不为人知地生活下来。因为洪江的邮局被炸,联络中断,对爸爸妈妈来说,我就像从人间蒸发了。抗战胜利后,妈妈托朋友在报纸上登广告,想通过寻找我的养父再找到我。几十年后,我的朋友在档案馆发黄的报纸上给我复印来一条拇指大小的小广告,上面说:“瞿玉屏兄鉴:别后九年,不知消息,至念。望兄见报后,即将通讯地址示知。来信请寄重庆《新华日报》熊经理收转。”可惜,养父早在一年前就去世了,没能看到这条广告。
这时,离全国解放还有三年,我还得在茫茫人海中继续漂泊……
(作者:贺捷生,系军旅作家、少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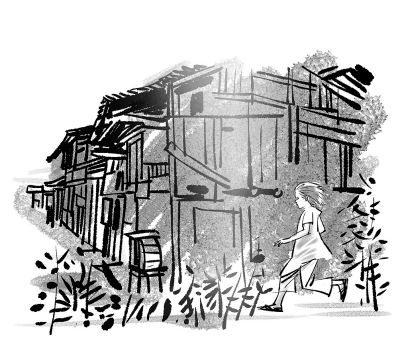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