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黄宗羲纂《明儒学案》,标志着“学案体”的成熟与正式定型。黄氏又草创《宋元学案》,未毕而逝,经黄百家、全祖望的续补以及王梓材、冯云濠的校定,最终刊刻成书。此后,“学案体”著作风靡一时。嘉道之际,唐鉴撰《学案小识》,姚椿、沈曰富等人欲撰《国朝学案》。民国时期,徐世昌又主编《清儒学案》。“学案体”蔚然成为学术史编纂中的独特体裁。与此同时,对“学案体”著作的节选、重编也方兴未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些选本多一瞥而过。其实,这些选本经编者的精心节选,蕴藏了编纂的思想寄托与内在关怀。于“学案体”背后,寻绎这一编纂语境,可以一睹学术与现实脉动的思想史轨迹,还有裨于重新认识这些选本的意义与价值。
一
史学大家梁启超对《宋元》《明儒》两学案素来推崇备至,赞誉两书为“中国完善学术史的开端”。早在1905年,他就纂有《节本明儒学案》。《例言》称,本书所抄“专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属于科学范围者,一切不抄”,因此多采明儒之道德修养言行,书中还附有众多针对现状而发的眉批。这些均显露出梁氏此时的关切所在。考察此书的背景,正处维新运动失败,梁氏流亡日本期间。他目睹革命党人一味追求功利,忽视道德修养,因此著《新民说》呼吁国民重视道德之培养。在他看来,拯救国家首先在于个人道德之修习,而不能光凭豪杰之气与功利之事。他认为,真正的豪杰无不注重道学涵养,因此他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鼓励仁人志士敢作敢为,但又不能效仿泰州学派“现成良知”的流弊。梁氏采撷明儒的道德言行,正欲从中汲取重铸国民道德之资。因此,节选本之样貌、用意与《明儒学案》以存阳明之学的原旨相去甚远。
吴虞在1907年辑有《宋元学案粹语》,书中选录了从胡瑗至郑玉共91人之语,这些言语多“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吴虞独节此类修身、论世、讲学、为文之语,亦有其自身的考虑。在他的视域中,近代以来,西学大量涌入,科技与知识虽代谢迅猛,但道德并未俱进,反而大衰。国家衰败、社会激荡的重要症结很大程度缘于世道浇漓,道德沉沦。因此,节选古人粹语,借古人德言善行之表举,呼吁德育建设,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国家危难的局面,有识之士汲汲于救亡图存,从政治、实业、教育、体育等途径多层面、多渠道寻求救国之方。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将国家衰颓归咎于世风败坏、人心沦丧,因此追本溯源,聚焦并呼吁社会的德育建设,通过宣讲圣贤言行,陶铸心性道德,培养德智兼备之士,达到重塑社会的目的。梁启超、吴虞对学案的节选即是重视德育、重建道德秩序的诉求表现。
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缪天绶选注了《宋元》《明儒》两学案。缪氏认为《宋元学案》属学术史著作,并为之增补罅缺。在《学说》一栏,缪氏取法哲学史的模式,按宇宙论、心论、修为方法论的次序采录各家之学。在《附录》中又列“遗事”“批评”,补充人物传记与后世评价。对原著遗漏的重要材料,亦稍采他书补入。此外,他又稍改全祖望的思想观,站在近世以来朱陆之争的视域上,遴选、编排思想人物。选注《明儒学案》,一改黄宗羲以阳明学为中心的路径,而以朱陆消长作为主线,将明代学术分为述朱期、王学盛期、王学修正期。可以看出,缪氏力图在这两部选注中,最大可能地呈现宋明儒学的发展简史。
同一时期,胡秋原编有《节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节补》(1944)。前者按时间顺序,收录庆历、党争、新学、涑水等15个学案,大体介绍了宋元儒学史源流。如果说《节选宋元学案》基本依据原著,而《明儒学案节补》已越出原著,大有重写学术史之意味。胡氏不满足黄宗羲所收明儒止于刘宗周、孙奇逢,且仅限理学人物,他特别表彰西学影响下徐光启等人的时代意义,以及明末清初遗民的忠烈气节,因此在节补本中增补了西学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与明末遗民(朱舜水、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的传记。
缪、胡所选两学案,均属面向社会的系列普及读物,其目的在于让世人更多了解理学发展的真相,消除对理学的误解,因此以学术史视角裁剪两学案,简明扼要地梳理宋明理学史,全书结构亦有所变动,但用意或与两学案的初衷最为接近。
三
抗战期间启动《重编四朝学案》,由陈训慈、李心庄重编《宋元》《明儒》两学案,钱穆负责《重编清儒学案》。与原著相比,重编《宋元学案》在人物序列上略有调整。如按时间先后将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移于《横渠学案》后;将巽斋、介轩学案上移,仅次《双峰学案》;又将带有“盖示外之意”的《学略》一律改为《学案》。这些表明,编者已突破传统的程朱道统观,对王安石与苏轼的学术有了客观认识。
至于人物传记,重编本全部删削“理论深玄不易理解”“批评涉及意气近于排击”“迷信怪诞或晦涩或谤讦”之语,甚至删除反映全祖望宏大思想史观而具重要意义的《屏山诸儒学案》《元祐》《庆元》党案,唯保留“重其躬行实践可为世法者”。而在各家论著中,增补了“确有创获,足以牖发心智增长志气者”,如周敦颐的《通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又原著仅采王安石《王霸论》等九篇文章,但编者认为此不足以反映荆公经世之精神,因此“增《上仁宗皇帝书》原文,及节引《礼乐论》《大人论》等数节,俾更得见其经世治国之规略,与其学说思想之要谛”。对于传记、论著后的《附录》,重编本亦删除“琐行片语无关宏旨”而保存“足彰其人之学问行谊事业之大者”。显然,编者欲凸显的是学术的经世精神。因此,原本以议论见长的宋儒在重编本中被塑造成“重躬行实践”“有俾于经世治国”的豪杰人物。
李心庄重编《明儒学案》的原则一仍《重编宋元学案》,对人物传记的删选,“所留事迹,重在躬行、实践可为世法者”,强调诸儒的嘉言懿行。对于思想史上重要的儒释之辨、朱陆之争,以及理学中的心性、理气讨论,李心庄认为属“深玄晦涩”“攻讦琐屑”且无关治世,故悉数删除。由此可见,《重编明儒学案》意在推扬儒者的实践精神与道德品格。
钱穆的《重编清儒学案》也以理学精神为评判标准,重视气节的忠义与学说的实践,如颂扬晚明遗民理学而贬低清初理学名臣,认为孙奇逢、刁包属“吾儒一线之真脉者”,却訾议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李光地“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全书所选人物仅限理学范围,故给人一部清代理学发展史的印象,这与《清儒学案》的旨要大不相同。但因为原著坚持广收博采,熔汉宋之学为一炉,大体反映了清代学术整体而复杂的学术生态。
纵观四朝学案的重编本,重在表彰儒者的品行与学说的经世,一改学案原著关涉儒学源流与学说思想的旨要,活生生成为儒者的言行录与品行史。考察这一重编的缘由,可从编者所处的语境推勘得知。当时正处抗战烽火,为砥砺民族自信,一大批学人纷纷表举历史上的忠烈人物,宣扬民族气节,诠释抗战必胜的信心。《重编四朝学案》,彰显躬行的忠义与学说的经世,即是学术救国运动下的一帧剪影。
从上述对学案节本的考察,可清晰发现,历史文本的节本虽以原典展开,但历经不同人的重编,全书框架、结构已发生变动,呈现出与原著不同的面相与内涵。这种节选,与其说是对经典文本的介绍,不如说是改编者自身寄望与诉求的表达。毫无疑问,以文献学的视野去评判这些节选本的文本价值,难免自落窠臼。事实上,经过这种自觉不自觉的“误读”,历史文本绽放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也一定程度实现了原著的再升值。在这种节选与重编的过程中,历史文本既为后人提供了“为我所用”的资源,也再度强化了自身的经典地位。
学案节选本的盛行,也折射出中国源远流长的选本传统。近代以前,中国学问方式以“经典诠释型”为主,通过对经典的注疏、发挥,如对四书五经或《老》《庄》文本的注解、节选,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寄寓自己的学术见解。从梁启超、陈训慈、胡秋原对学案的节选、补编,可以明显看出,在新旧更迭、中西交汇的近代,许多知识人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古典今释道路上,一方面积极引介西方知识体系以阐释中国传统学问,另一方面仍自觉继承中国固有的诠释方式,以选本的形式,对经典进行重新注解、重新阐释,昭示出选本传统在近现代的延续及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金晓刚,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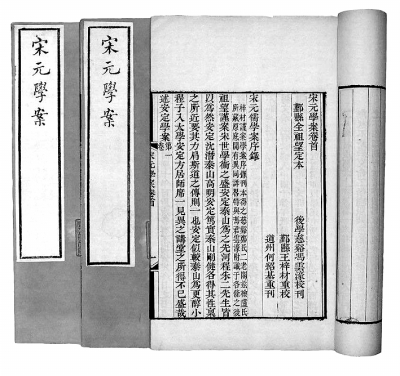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