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
看胡适视频,老先生笑容可掬,如秋月临江般和蔼飒爽,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极了。胡适的声音,我听过,纪念北大创办60周年的致辞,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丝毫不见官腔,更无学究气。相形之下,当下很多文人似乎不会讲话了,难见胡适那种含蓄委婉。
旧北大人说胡先生上课总在红楼那间最大的教室,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胡适的口音,谈不上字正腔圆,似乎略带沙哑略带疲倦,有着浓郁的中式情调。恰恰是略带沙哑的疲倦感,使得腔调中的分量上来了。
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修炼,并不稀奇。1932年11月27日,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随口几句话,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这是民国人的风度民国人的腔调。听过讲演的学生回忆,鲁迅声调平缓,不脱浙江口音,简练沉着,像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故事,与先生叱咤风云、锋芒毕露的杂文不一样。
这两年读中国古典文章,也读一些域外作品,越读越深,发现心里还是不能忘情民国文人。在人生年少时,在穷村僻乡里,偶然得见布衣长袍的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诸位文章,关怀前途崎岖,受用至今。都说人老了会念旧,人不老也念旧的,老人念旧事,我念旧人。深宵伏案,尽是线装纸墨的暗香,满心旧人,轻呼一声,恍在咫尺,就着一壶清茶与他们秉烛夜谈。
抱着这样朦胧的心愿,下笔试写旧人文事。顾不得许多,一路信笔,过程很奇妙很有趣也很长学识。那些人物尽管无从相识,一篇篇写下来的时候,内心却觉得他们是一辈子的至交。旧人们实在离散得很远了,烟水茫茫,故人何在,泛黄的老纸记载了曾经鲜活的面容。时间之别,哪怕一秒,也是永离。
最长的莫过时间,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时间,我们太多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如今倏然而立,30年眨眼而过,一个人就算长寿,活90岁,眨三次眼罢了。现在想到岁月人生的话题,心头泛起光阴似箭的怅惘来。写写青春岁月阅读民国人的记忆,也算作旧梦重温。
“民国的腔调”,腔调腔调,腔也调也。中国戏曲讲究唱腔讲究声调,腔调好坏是戏曲的评判标准,引申开来便是形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性格、风格、品位。民国的腔调,不单指腔调,更指民国文人的风格气度、文章姿容。
时过境迁,现在不会再熬夜读鲁迅读郁达夫读巴金,不会孜孜不倦于张恨水的小说,不会对书店里的一本《边城》念念不忘,不会为了借一本书翻山越岭20里。那时读那些前人文章,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写作。早先学《雅舍小品》,后来读王力、汪曾祺、孙犁,觉得气息不壮,却大有所得。废名天真烂漫,自说自话、一意孤行;郁达夫率真,有名士风度。他们都影响过我。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民国人取得的成绩不算多大,但行状很可追慕。阅读他们重述他们,让我从顾影自怜的小品文创作痴态中醒来,醒在不同人物的命运里,醒在不同人物的文字中。
他们星光灿烂,我在草地上乘凉。
(作者为“80后”作家,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此文为《民国的腔调》一书自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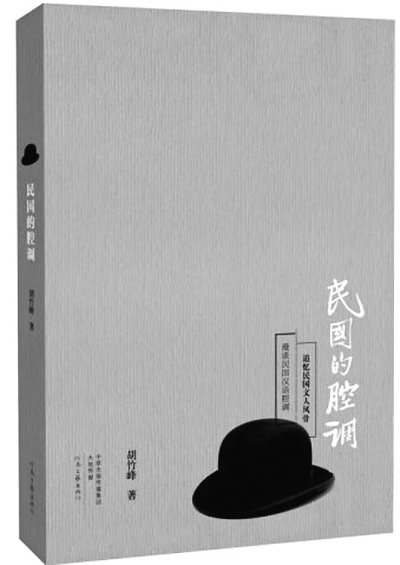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