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 折
邓友梅只读过4年小学,11岁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他12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
只干了一年,赶上精兵简政,部队发给邓友梅40斤小米和几丈粗布,让他复员。
邓友梅只好又去天津投亲。
天津街头有租小说的,租一本小说一天收几分钱。邓友梅打零工吃饭,别的娱乐玩不起,租书还算能承担,就读起了小说。《薛仁贵征东》《江湖奇侠传》《旧巷斜阳》……几乎碰上什么看什么。
有一次,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邓友梅见机会难得,求人家把他收下了,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做了一名劳工。
1945年,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没活可干,日本人又把劳工送回中国,打算叫他们在日军控制下的中国矿山劳动。邓友梅在几个大工人的带领下逃出工厂,参加了新四军。
最初,邓友梅在连部当通信员,营长见他爱读书,就送他去一所中学脱产学习,补文化课。可是,邓友梅当兵当野了,穿一身军装跟老百姓的孩子一块儿坐在课堂里念书,怎么也坐不稳当。碰巧军文工团排戏,郭沫若写的《李闯王》,其中有一个放牛小孩的角色,要求会说普通话。
文工团找了几个小孩去面试,最终选中了邓友梅。
放牛小孩的戏不多,没戏演时,邓友梅管小道具、点汽灯,更多的是帮演员提词。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后,就背下来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只能在战场即兴演出。部队走路行军时,邓友梅就和文工团的战友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看到什么现编现演。
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都来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戏,他们是专家,可没干过火线鼓动,不会扭秧歌,更不会编快板。邓友梅则靠自己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
有一回,邓友梅数快板被一个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吧!”不久,稿子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这就是邓友梅的处女作《国大代表》。
邓友梅的第一笔稿费是一斤花生和几个柿子。
此后,邓友梅就常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那时的他没读过什么书,也不会写文章,只是一心想当个好演员。
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邓友梅就只能又去点汽灯、管小道具了。就在他有点苦闷之时,遇到了一次机会调整,到了茹志鹃的班里。
日 记
在邓友梅的印象中,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女同志集中住,她怕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邓友梅一个人住在磨道里,单独有盏灯,茹志鹃就凑到他那儿去写。
“她(茹志鹃)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就找出本书扔给我看。”就这样,邓友梅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以至于后来,一天没书可读就会感到手足无措。
有一次,邓友梅读完鲁迅的《野草》,茹志鹃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邓友梅背了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茹志鹃就笑:“明白意思吗?”
邓友梅说:“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邓友梅被问傻了。他没想过为什么。
“这叫强调。”茹志鹃解释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邓友梅说,这是他平生第一堂文学课。此后,茹志鹃鼓励他写日记,让他往写作上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了《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女 兵
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从部队转业,调到了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有一次,他问赵树理:“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东西怎么总有疙瘩呢?我该怎么改进?”
赵树理回答:“第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第二,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得顺口,别人读着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
1951年,邓友梅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发表了小说《咱们都是同事》,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
写好后,邓友梅交给团长田汉审阅。田汉读完后很高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是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刊登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不久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让邓友梅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邓友梅赶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
其实,在邓友梅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就是这个女兵形象。他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王安忆。”
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品,邓友梅对写作有了信心。从此,他就往写小说这条路上奔了。他觉得写作不难,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
于是,邓友梅又猛补文学理论。这时他才知道,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他按这些“规定”去写,却是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一篇小说也没发表。
“赵树理、王亚平等人认为,我虽然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于是决定派我去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邓友梅回忆说,当时所长是丁玲,导师是张天翼。张天翼教给他观察生活、捕捉题材和形象的技能,也是记日记。
进入文学讲习所后,邓友梅认真读书,一天要读上十几个小时。讲习所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他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
讲习所没有专职老师,学哪一门就请哪一门专家来讲。比如讲屈原,就请游国恩,学莎士比亚,就请曹禺。
学习外国文学时,必读书目中有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后者是郭沫若翻译的,作家和翻译家都是名人,可是邓友梅怎么也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儿。他就在桌上放《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过来,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丁玲很开通,她知道邓友梅偷着看武侠小说,但并没有批评。“丁玲说,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我就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邓友梅的体会是,读书就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频道。
从文学讲习所出来后,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发表在1956年的《处女地》上,接着被《文艺学习》转载,引起文坛的关注,却又因此被打成“右派”,转送到辽宁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
从此,邓友梅22年没再写任何东西,直到后来的“拨乱反正”,他才又有了写作的机会。
强 项
直到1976年,邓友梅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
有一次,邓友梅听广播,获悉陈毅逝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陈毅是新四军军长。他从小就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工作,与陈毅有感情,于是写下了很多回忆性的文字。
恰好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看望邓友梅,看到这些文字,便鼓励他改成小说。
小说改了两遍,发表在茹志鹃担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学》上。这部名为《我们的军长》的短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段时期,刘绍棠、丛维熙、王蒙等陆续回京,他们的激情创作和不俗成绩成为当时的文坛一景。
在《我的写作生活》中,邓友梅写道——
“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自己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这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经过衡量比较,邓友梅琢磨出了自己的强项。
邓友梅小时候生活在京津地区,常听到汉族人说旗人爱面子没本事,好吃懒做。北京解放初期,他曾参加过安排旗人知识分子生活的工作,被打成“右派”后又长期和几位满族朋友共同劳动。
邓友梅渐渐发现,旧中国时汉族人对旗人看法带有偏见——
“其实旗人的平均文化素质相当高。他们不仅会吟诗写字,而且不少人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服装美食等方面,学问很深。只因大清国皇上夺得天下之后给了他们一份特权:子承父职,生来有一份钱粮。”
发现自己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的特长后,邓友梅试着写了《话说陶然亭》,发表后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成为文坛“京味儿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评论家认为,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他的语言特色是少用形容词、成语,多以鲜活的生活语言入文,叙述语言得北京话的方言精髓而又用于无形,清爽利落,明净单纯,带着北京人亲切的民间声口。
20世纪80年代,“京味儿文学”一度非常繁荣,然而近几年却有些萧条。对此,邓友梅的看法是,当时一大批老作家在“文革”中无法从事创作,他们有积累,有创作冲动,一旦条件宽松自然喷发出来。但在这些老作家之后,没有了继承者——
“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10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儿。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为‘全国的北京’了,并逐渐转为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的丧失。”
邓友梅觉得,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而老北京的那种温情,那种踏实,也随之逝去了。
有 趣
邓友梅担任过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对于茅奖,他的评价非常客观——
“多数作品得不上奖,得奖有一定比例,也有个平衡,比如反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的都应该有所体现。现在发表意见的平台大了,争论也会越来越多。不光茅奖,整个文学界都这样,这没有什么不好。”
邓友梅回忆起自己当年参与茅奖评选的情形——
“大家关在一个屋子里读几天作品,然后很直爽地发表意见,整个过程是民主、认真、严肃的,没有人拉票。文学界很看重自己的声誉,不注重物质方面的东西。在评奖方面,你想说服我,得有说服我的文学理由。对作品的不同意见那个时候也有,但不像现在这么多。记得有个作品,大家意见不一,后来就投票决定。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住读者的检验。”
一次茅奖评选中发生了争论,有几位评委拍着桌子说,如果某部作品评上奖,他们就辞去评委职务当即退席。邓友梅说,我有点儿犯“痴呆”了,先休息一会儿行吗?休息完再进会场后,他发话说:我想明白了,投票选哪个作品是评委神圣的权利,别人无权反对;当不当评委也是各位的权利,别人也无权反对;投谁的票自己决定,当不当评委也由各位自己决定,我一律尊重你们的选择,上午的会到此结束,自愿退出评委的同志下午可以不来了。
结果,下午的评委会一个人也没少。
邓友梅既写“京味儿”作品,也写战争历史作品,他觉得,自己在写战争作品上花的功夫最大,但除了《我们的军长》和《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两篇得了奖,其他并无太大反响。相反,他写的那些轻松有趣的“京味儿”作品,却更受读者欢迎。
邓友梅反复思考过其中原因。他认为,读者读书首先要选有趣的,有趣才好看。他写“京味儿”小说,首先是想怎样把它写得好看。“要把小说写好看,就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与你的性格最易呼应又是你最易于表现的生活素材。生活内容复杂多样,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写小说。”
邓友梅说,最体现本质意义的才是最值得写作的,但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人眼里看来感觉却未必一样。
“张天翼同志让我养成随时观察有趣事物的习惯。第一是有趣,但光有趣也不行,还要有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邓友梅说,在自己的所有小说中,90%是大路货,只有10%才是自己特有的产品。哪篇小说写得特别顺,这篇小说故事的结构、情节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写得顺,说明酝酿得成熟。但在语言上要想写出特点就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这是苦功夫。
“真正讲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说,有一句废话都很刺眼。”邓友梅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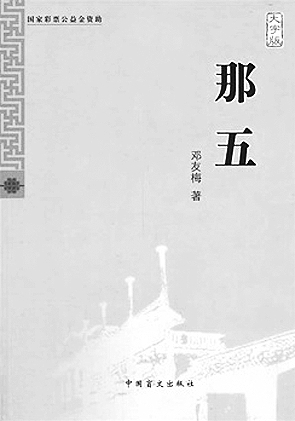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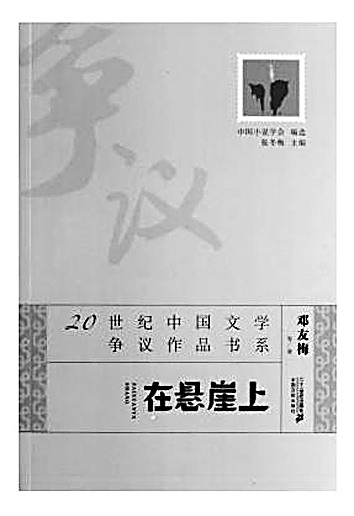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