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是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其运用西方逻辑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的手法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他在行文中反复强调,古诗词的核心精神是对往事的感怀追忆。他提出了新颖的、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风格的观点:一位作者在追忆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成了被追忆的对象。“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
以《江南逢李龟年》为例,该诗作于770年,杜甫已进入晚年,安乐繁华已成过眼烟云,他再也回不了家乡,回不了京城。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想到,李龟年是安史之乱前京城最有名的歌手,是最得玄宗赏识的乐工之一。但是,乐工们在安史之乱后四散逃亡,李龟年的声望和阔绰生活也随着丧失。这时,已到暮年的李龟年流落江南,靠在宴会上演唱为生。这首诗写道,他在听众面前不单单是歌唱者,也令听众想起他的往昔,想到乐工们的境遇变迁和世事沧桑。他站在我们面前歌唱,四周笼罩着开元时代的氛围,他就像是那个恣意纵乐又懵然无知的年代的幽灵。宇文的文章在这里告诉我们,杜甫与李龟年是“互文阅读”的关系:一方面,杜甫写作了这首诗,是该诗的作者;另一方面,他通过介绍李龟年的身世,也观察到了自己身世的坎坷。也即宇文所指出的:作者在追忆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成了被追忆的对象。
总的来说,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偏向于抒情感怀风格,习惯分析具体词句的意蕴、辞藻的精致华美,着力于探究具体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作者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或忧郁深沉或激昂壮阔的叙述文体。与此迥异的是,宇文所安倾向于分析不同年代、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普适性因素,即回忆与追忆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精神价值。作者提到五月花这种花卉植物,它因为新移民抵达美国所搭乘的“五月花号”而闻名于世,因此当他看到一幅标注着1903年所摄的五月花照片便产生了追古抚今的感伤之意;但如果看到一幅未标注所摄年代的五月花照片就不会产生任何追忆之感,只是觉得一幅普通花卉照片而已。这便是历史,年代的印记让人产生回忆。李清照追忆亡夫的诸多名篇,是宇文最乐意研究的对象。例如,她为丈夫赵明诚《金石录》写的《后序》,宇文提醒读者注意,李清照所藏书画古器不只是稀有物品,它们还凝聚着她与丈夫共享的往事。追忆这些东西即追忆夫妇感情,指认战乱才是导致它们散失和夫妻生死分离的根本原因。本书指出:“到手的东西丢失了,它们同样从记忆中丢失了;失去的东西现在却保存在记忆里。这就是记忆的本性。在这里以及整个《后序》里,凡是涉及到失去的东西和力所不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这种本性。”
作者对于追忆的一段描述能够更加具体地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细腻感伤的情愫:“我们读到这首小诗,或者是在某处古战场发现一枚生锈的箭镞,或者是重游故景,这首诗,这枚箭镞或这处旧日游览过的景致,在我们眼里就有了会让人分辨不清的双重身份:它们既是局限在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是它们自身,同时又是能容纳其他东西的一处殿堂,是某些其他东西借以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场所。这种诗,物和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我们身边。”
(程旸,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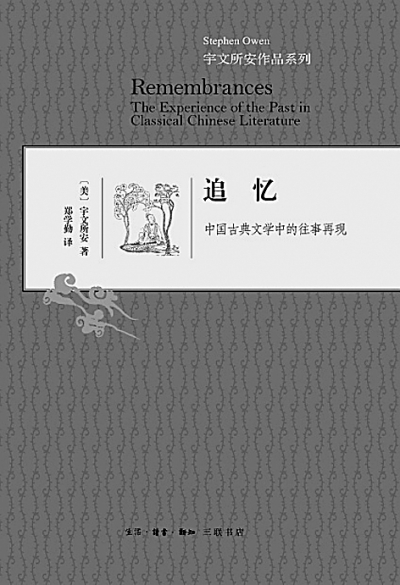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