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忘史亡国。这一段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势不可当,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同时也不排斥从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急剧的转型阶段,反映这一时期经济状况和抗战救国方略的中国经济学也应运而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抗战时期力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达、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钱俊瑞、何廉和方显廷等人。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译著200余种,其中一大半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出版的,这为加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例如,陈望道的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译本1930年1月问世,陈启修的《资本论》第一个节译本即《资本论》第一分册于1930年出版。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及其马列著作编译部,翌年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为中央出版局),以解放社名义出版马列著作。
李达是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问世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述,力求“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与去迹。”毛泽东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王亚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与郭大力一起最早译介了《资本论》三卷本(1938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全力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研究的重心。他一生有著、译四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其中,《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就是他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经济形态的中国经济学。
许涤新为建立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道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做了可贵的探索。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特点。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香港撰著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本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理论、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意义,是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读本。
薛暮桥和钱俊瑞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他们主持《中国农村》刊物的出版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独辟蹊径。钱俊瑞在《怎样研究中国经济》(1936年)一书中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应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他陆续出版有《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的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和《中国国防经济建设》;薛暮桥则发表了《江南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缩影》《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等文章,均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代表作,对研究中国经济、抗日救亡和指导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何廉和方显廷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擅长从学理的角度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具有本土特性的工业化理论。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动荡严峻的抗战环境中,他们系统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工业的调查,编制与发布了著名的“南开指数”以及中国工业化系列调查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主持编制的《(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1945年竣稿),集中展现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此外,他们还致力于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在南开大学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
二、战时统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统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备战。193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迅速将平时的经济体制向战时的经济体制转轨,对金融、贸易、物价、物资、工业等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其中包括发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设立了中、工、交、农四行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专卖政策与统购统销政策;集中全国财力保障抗日战争的需要,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将原属于地方财政的田赋、营业税、契税等主要税源收归中央,形成中央税权高度集中的战时财税体系。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聚焦于统制经济这一救国富国方策,多次展开了关于“统制经济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例如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一届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当时的国内各主要刊物如《经济学季刊》《银行周报》《东方杂志》,甚至以标榜自由主义为宗旨的《独立评论》等杂志,都参加了这场讨论。统制经济成为热门词汇,以致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统制经济就不足以显其本色。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李权时、罗敦伟、张素民、陈长蘅等人拒斥自由经济,主张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倡导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强调中国再要走欧美列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老路已不合时宜。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顾翊群、唐庆增、梁子范等处于守势,并力图把这一场争论引向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纯学术之争。这场关于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是学术界在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与民族危机下重建经济的一种积极思考,为国民政府实行全面经济统制即战时经济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三、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两种评价
1936年问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并且风靡中国。中国经济学社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对凯恩斯的《通论》最早做了介绍;姚庆三的《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1938年)一书,认为“凯恩斯此书不愧为一空前之贡献……可知凯氏之新说已浸浸乎成为今后新经济学之柱石矣。”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1945年)一书以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来建构其货币相对数量理论体系,并获得国内最高学术奖杨铨奖金和中国财政学会奖金。
反对者和商榷者也大有人在。蒋硕杰在影响力颇大的英文期刊《经济学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1943年)一文,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胡代光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做了对比分析,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正统派理论的叛逆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障碍就在资本的本身;凯恩斯注重分析全社会生产量与就业水平的决定,只是一种短期经济变动的理论,而《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擅长于长期的动态分析。樊弘的《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及利息等理论》(英国《经济研究评论》1939年第7卷第1期)则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见解。
中国经济学界还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展开了有意义的争论和独到的阐述。其中,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问题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以徐毓枬、杨叔进、丁忱两、桑恒康等为代表的否定派成为主流。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基于中外国情的异质性,对凯恩斯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提出了质疑,他基于9大理由而得出的结论是:《通论》“是完全根据于极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英美两国的情形而写成的,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此外,万一华的《凯恩斯理论能中国化吗?》、吴大琨的《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书》也对此持否定意见。
四、财政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脱颖而出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研究特别是战时财政学和战时金融学,受到经济学界尤其是各个研究部门、大学、各银行研究部门学者的关注,成果颇丰。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1940年)、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1942年)、马寅初的《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1940年)等,建议加税(如临时财产税)发债、财政战时转轨为统制财政,并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但国民政府并没有采纳马寅初的主张,主要依靠通货膨胀和发行公债来筹措战时经费。1935年的法币改革虽有助于统一币制,解除因白银外流引起的金融危机,但纸币的财政性发行在战时加剧了通货膨胀,促使物价飞涨,最终成为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一大导火线。
理论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抗战时期财政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和贸易经济学、会计学与统计学、人口学、世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发展风生水起,蔚为大观,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杂志应运而生,有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已跻身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例如: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对于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及法国重农学派的研究(赵迺抟、李肇义)、经济通史研究(马乘风)、关于现代中国人口的统计(陈达)、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林霖)等。
以史为鉴,忘史亡国。这一段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势不可挡,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同时也不排斥从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武汉大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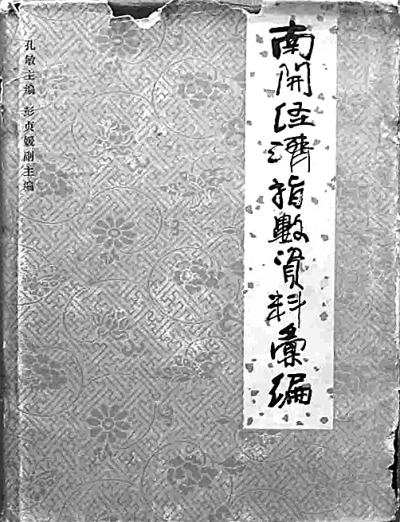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