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8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改选》,随后受到严厉批判。次年,我就被下放到了新建铁路的隧道工程队,位于豫西北、晋东南交界处的大山深处,劳动改造。
离开京城时,还是满城飞花的五月天,寒意袭人。可我到了河南新乡,再由焦作到九府坟,村野田头,遍地青翠,河边渠畔,无不尽绿,已是春意盎然的初夏景象。再从九府坟搭上工程车,沿着丹河的临时公路,到我要去报到的工程队,那才是真正进入太行山区。一路颠簸磕碰,步步攀升,朝眼前的高峰方山前进,还要向更远的崇山峻岭驶去的时候,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壮观的绿,蓝天白云之下,层峦叠嶂之中,朝阳山坡上那浓浓的绿,阴山凹地里那淡淡的绿,草丛点缀着花朵那彩艳的绿,河水跳动着阳光那闪烁的绿,老树枯枝近乎苍黄的绿,菟丝牛蒡那柔曼荏弱的绿,无一不透露出蓬勃生机,也无一不展示出活泼生气。就在这触目皆绿的视觉冲击下,在车的前方,蜿蜒曲折的盘山道上,吸引住我眼光的,竟是一辆绿色加重的自行车,一位绿色制服的骑车人,正吃力地推车爬坡。那行走的绿,那活动的绿,那不停歇地前进的绿,至今还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绿,最温暖的绿。
虽然,匆匆忙忙离开北京,奔赴工地,但对于自己的命运,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忐忑不安的焦虑;对于妻子的思念,孩子的牵挂,始终是推拭不去的阴影,但眼前这位推车者的倔强身影,却使我生出心理上的激动。尤其,我搭乘的这辆拉水泥的大解放,行驶到他身旁停了下来,估计是驾驶员或者在副驾驶位上坐着的干事,示意他上车载他一程,他笑了笑,摆摆手,这就更让我对他生出敬意。于是,车子就接着向前驶去,不一会,那绿单车绿制服的乡邮员,就落在视线以外了。凡修新线铁路,必先建简易公路,而这种简易公路是为汽车设计,而不考虑自行车的骑行,第一,坡度大,第二,路不平,第三,不搭桥梁顺山而建,不得不绕很大的弯。就在我们这辆卡车拐过一个山口,才再次看到那位推车者的绿色身影,显然,他在抄近道的下山路上摔倒了,车子歪在一边,邮件散落满地,他正在忙着收拾。车突然停下,这位开车师傅太好心了,然后,原路倒回去。这样,我帮他将自行车架到车上,然后,他又递上绿色的“中国人民邮政”(即中国邮政,编者加。下同)的挎包,这才翻身上车,拍拍驾驶室的棚顶,车又接着开动。这时,他第一个动作,从我手里拿过装信件的绿色“中国人民邮政”挎包,郑重地抱在怀里。当时,感到他有些鲁莽,后来,熟悉了,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习惯。因为这个挎包里,有挂号信,有汇款单,还有邮局特有的那种日戳。也许他察觉到我的变化,对我憨厚地一笑,拍拍包说,这是我全部家当。接着他告诉我,他姓常,家住山下博爱尚庄,初中毕业,没有考上师专,现在做乡邮员。然后,腾出一只手来握住我,特别认真地说,往后,有事只管找我。
看来,这是一双牢靠可信的手,没想到,当我走出别样人生途中的第一步,碰到的第一位旅伴,是这样一位和善憨笑的绿衣使者。
乡邮员,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来说,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一步步推着自行车的身影,便是他们全部工作的艰苦写照。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烈日当空,汗流浃背,他们都得在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行走,把万千挂念的平安家书,带给远方的亲人,又把殷勤嘱托的深情回信,送到家人的手中。这手托着心与心的思念,那手拉近地与地的距离,在天地山海之间,无处不留下这些最基层的乡邮员的踪迹。那时,我真的没想得那么远,离开京城,再回到古都,竟是磨炼熬煎了二十多年以后的事。在这期间,随着铁路工程队,走遍南北,除了深山,就是旷野,不知和多少乡邮员打过交道?粗略地算一笔账,每月往家汇一笔生活费,每月给家寄一封信,再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二十多年,如此积累下来,那是相当惊人,也是相当辛酸的数字。然而,所有这些汇款和收发信件,无一不是要经过像小常这样牢靠可信的手,才得以完好无损地到达目的地啊!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感情最值得看重的,是托付;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信任最值得珍贵的,是担当。因此,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绿衣使者,也许是最可托付的,更是最敢于担当的信得过的朋友。
卡车开到了隧道九队,就在那里将水泥卸下,当天还要原路返回九府坟。那位干事也不想在山上过夜,就对我说,你就跟这个乡邮员去隧七队吧,已经摇电话通知他们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没有手机这一说,工地甚至连拨号、按键的电话机也没有,只能靠手摇,由接线生转接。我不能说这位干事,没有摇这个电话,很大可能接电话的那头没当回事。幸好有这位乡邮员小常,正如那位干事,还包括热心的卡车师傅所讲,这一带的单位、工人,村庄、老乡,没有他不认识的,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说到这里,我看到小常脸上露出憨厚的笑。这样,我到太行山的第一餐饭,就是吃小常从家里带来的馍,第一夜晚,就是在小常的邮政点落脚。
山林的夜,很静,睡不着的我,不禁思索,天地很大,世界很广,人生无限,前途漫长。怎么活,不是活呢?挫折,也许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只要山在,石在,泥土在,绿色就会在。而绿在,春在,温暖也会在。
我的这位乡邮员朋友,睡得很香,虽然他有一辆加重的自行车,但实际上只是装载邮件和包裹之用,他永远弯着腰推,很少看到他骑行,因此,他很劳累,他很辛苦,所以,一倒头就睡着了。后来,我还知道,他的收入实际很低,甚至舍不得多花钱在段部食堂买饭吃,总是从家里带来干馍。可他,乐乐呵呵,快快活活,他被大家所需要,他也乐意被大家所需要。由于他经常往返于山上山下,拜托他买个什么,带个什么,总是满口应承。甚至山村里的老乡,连针头线脑,大事小情,也好意思张嘴求他的。我还曾经陪他爬到山顶一户人家,送去那老爷子要抽的一口进嘴就吹掉余烬的怀庆府毛烟。总之,他活得很充实,他常勉励自己,我穿着这身制服,我是公家人,我得对得起它,李老师,你说是不是?
显然,昨天,那位干事在与我们分手前,将我的背景情况对小常说了一点,但我非常感激这位乡邮员,他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始终友好如初,叫我老师,没嫌弃我,不隔阂我。第二天一早,他穿起那绿色制服,背着那绿色挎包,陪着我从段部到隧七队报到。第二工程段上属设在九府坟的第二工程处,下管三个隧道施工队,从三个方向开挖一条超长隧道。因为一下子涌进千把工人,再加上当地山村居民,博爱县邮局就在山里一个叫东铁村的村子,也是二段段部所在地,开设了这个邮政点。
正是夜班和白班交替的时刻,一路上,来来往往的工人师傅、技术员,队干部,还有家属,都会跟他点头打招呼。到了隧七队,进了队部,交班的,报表的,领料的,测量打杆的,虽然乱作一团,但大家也不把他视作外人。小常找了一圈,抓住队里一位领导,一说,队长又开始摇电话。最后,终于明白怎么回事,这样,很快将我分到工班,于是,从那时那刻起,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别样人生。
小常站在坡下,看我背着铺盖卷,拎着洗脸盆,走向坡上我的工班工棚。本来呆站着看我的他,当我快要进工棚的时候,突然快跑了两步,追上来,伸出手抓住我。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离得不远,一句是有空来坐。要不是小常转头很快走掉的话,我的泪水就会忍不住夺眶而出了。
他那绿制服,绿挎包,很快消融于满山遍野,林海苍翠,弥天漫地,天外青山山更青的视野之中,这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绿色。什么是春天呢?绿色就是春天,也是我始终想提起笔来礼赞绿色的隐衷。
(作者为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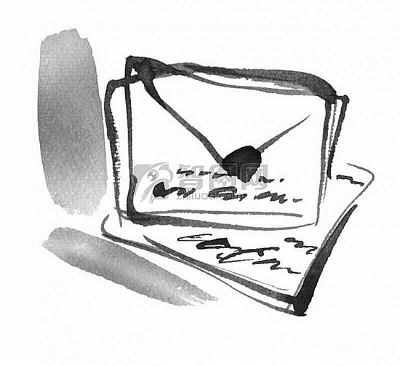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