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海》是爱尔兰语言大师约翰·班维尔2005年的布克奖获奖佳作,小说讲述了艺术史学家马克斯·默顿回到他儿时的海滨小村后所发生的故事。如今的他,既要逃避人生新的离愁,又同时要面对往昔记忆的折磨。他被格雷斯家的双胞胎姐弟克洛伊和迈尔斯深深吸引,并很快卷入了他们的生活——既充满诱惑,又狂躁不安。接下来的故事则困扰了马克斯的余生……
这部小说在当年获得了布克奖评委的高度评价:“《海》运用了约翰·班维尔精准而优美的散文体语言,既包含着对人生确实的妥协,也有对记忆和认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它完全令人信服,又有着深刻的感动与阐述,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语言大师最好的作品之一。《海》对悲痛、记忆和冷静的爱进行了精妙的探讨。在班维尔的作品中,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
本期节选《海》中的一段场景,主要讲述主人公马克斯·默顿在妻子安娜去世后,回到儿时小村故地重游,见到古怪的布兰登上校和旧识瓦瓦苏小姐的一幕情节。让我们在这段主人公对往昔清晰而感伤的回忆和冷静而复杂的情感中感受这位语言大师的语言美学。
在安娜去世之后一个像那天一样的傍晚,周日的傍晚,我来到了这里。尽管已是秋日,却仍有镏金的阳光和伐倒的柏树浓墨般细长的暗影,仍能感觉到万物湿润晶莹闪亮,还有大海那青色的反光。我感到无以言说的放松;好像这黄昏,浸透了漫溢而出的虚伪的悲怆,像是个沉痛的负担暂时控制了我,我们的房子——或者理论上说现在是我的房子——还没有卖掉,我虽仍无心将它曝之于市,但却已不能在里面多待一刻了。安娜死后它就空了,变成个巨大的回声洞。空气中也残留着什么不怀好意的东西,像是一只老猎狗因为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喜爱的女主人离去而迁怒于苟延残喘的男主人,粗鲁地嚎叫着。安娜不许我们通知任何人她的病情。人们都猜测出了什么事,但是直到最后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了。即使克莱尔也只能推测她的母亲是在病危中。现在这些都结束了,另一些则开始了,对我来说,则是我作为一个幸存者的脆弱事业。
瓦瓦苏小姐对我的到来表现出羞涩的兴奋,她皱起的脸颊像粉色的绉纱一样闪光,她的双手一直在身前紧扣着,紧闭双唇以克制住脸上的笑意。当她开门时,布兰登上校正在她身后的走廊里来回踱着步;我能清楚地看出来他不喜欢我。我感到同情;毕竟,在我来以前,他是这通道的主宰,而我来了,还把他从他的栖木上推下来。他愤怒的眼神直盯着我的下巴——这里恰好与他的眼睛水平。他个头不高,脊背僵直,使劲握了握我的手,清了清喉咙,开始一针见血地评论着天气,我感觉他夸大了老派军人作风。关于他的有些事情是不准确的,有些地方太出跳,表现出过于故意的似是而非。那些光滑的粗革皮靴,肘部袖部镶有皮补缀的哈里斯呢外套,他在周末运动时穿的淡黄色背心,所有这些都完好得不像是真的。他像是个毫无纰漏的演员,将同样的角色扮演了太长时间。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个老军人。他非常巧妙地隐藏他的贝尔法斯特口音,但又不时露出马脚,就像关不住的风一样。为什么要隐藏,他究竟害怕它会泄露什么?瓦瓦苏小姐说她曾不止一次看到他参加周日教堂的早会。一个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上校?奇怪,非常奇怪。
窗户的尽头是休息室,以前那里是客厅,放着一张喝茶用的打猎桌。这个房间跟我记忆中的差不多,或者说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因为记忆总是努力使自己更加天衣无缝地适应重游的故地。这张桌子,就是那只狗带着球闯进来的那天,格雷斯夫人正站在旁边插花的那个?它布置得很精巧,银质大茶壶和配套的过滤器,上好的骨瓷,古董奶盅,取方糖的夹子,还有桌饰巾。瓦瓦苏小姐一副日本风格的装扮,头发挽成小布恩,交叉着插着两根大簪子。这让我想起,不太恰当地想起,那些十八世纪带有性意味的日本印刷图案——瓷器般的女子,泰然地承受扮着怪脸的男人粗俗的注视,还有那总是吸引我的弯曲的脚趾。
谈话并不十分流畅。瓦瓦苏仍然非常紧张,上校的胃则隆隆作响。迟暮的阳光透过外面花园中的灌木丛,晃着我的眼,使桌子上的物体看起来都在摇摆着,移换着。我感觉自己笨拙,拘泥,像是个大个子的不良儿童,被失望的父母送到乡下被一对年老的亲戚看管着。这是可怕的错误吗?我是否应该喃喃地找点借口,逃到一家旅馆过夜,或者回家,或者,继续忍受这些无知与附和?这时我反省,我对这里过分苛求细节了,所以它应该是个错误,应该是可怕的,应该是,我也应该是,用安娜的话说就是,不得体。“你真是疯了,”克莱尔说过,“你在那里会闷死的。”“她很满意啊,”我反驳道,她给自己弄到了一套不错的新公寓——倒是一点都没耽搁。“那过来跟我一起住吧,”她说,“这里足够两人住的。”跟她一起住!足够两人住!但我只是谢了她,淡淡地表示拒绝。我希望能住自己的房间。我不能忍受这些天来她看我的那种样子——所有女儿似的亲切关心——她的头晃到一边,就像安娜经常做的那样,扬起一边眉毛,额头热切地皱着。我不想要关心,我想要愤怒,谩骂,暴力。我像一个被牙疼折磨的男人,刺向舌尖的疼痛能带来一种报复性的快感,一次一次深入到颤动的口腔中。我想象着一只拳头到处飞过来,满满地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能感觉到那种撞击,听到鼻梁骨断裂的声音,这种想法为我提供了一点点可悲的满足。在葬礼后,当人们回到这所房子——这是可怕的,几乎无法忍受的——我用力抓起一只酒杯,用拳头把它捏碎了。带着满足感,我看到我的血滴下来,像是一个被我粗暴地砍伤的敌人的血。
“你是搞艺术营生的,那么,”上校小心地说,“那个一定很多,对吗?”
他指的是钱。瓦瓦苏小姐撇撇嘴,皱着眉狠狠看着他,责备地摇摇头。“他只是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她轻声说,仿佛要把吐出的每个词都吞下去,似乎这样我就听不到了。
上校飞快地把目光从我转到她的身上,又转了回来,默默点点头。他期望把事情弄乱,他习惯这样。他喝茶的时候,小指跷起,另一只手的小指则永远正对着手掌心平勾着。这是一种综合病征,比较常见,但名字我不记得了;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痛苦,但他说没有。他的那只手做出端庄的、横扫一切的手势,像是一个指挥家在召唤着木管乐器或是催促着合唱队的强音。喝茶时,他有着轻微的颤动,还不止一次噼啪响着碰到门牙,那肯定是一副假牙,这么白。他饱受岁月侵蚀的脸和手背上的皮肤都打着皱,褐色,像是闪亮的牛皮纸,还包过什么不能包的东西。
“我知道,”他说,其实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在1893年的一天,皮埃尔·勃纳尔在巴黎偶然看见一个从电车上走下来的女孩,被她那脆弱而苍白的美所吸引,皮埃尔尾随她去了她工作的地方,一家殡仪馆,她在那里缝制葬礼花圈上的珍珠。死亡在最初就将黑色的缎带编织进他们的生命中。他很快与她相熟了——我猜这种事情在巴黎的“美丽年代”(指欧洲社会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至一战爆发而结束。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很容易也很自然——后来,她离开了她的工作,离开了她生活中的一切,和他走到一起。她告诉他,她的名字叫玛特·德·玛利格奈,十六岁。实际上,直到三十多年后他终于能和她结婚时,才发现她的真名叫玛丽亚·布尔辛,而且当他们相遇时她也不是十六岁,而是跟勃纳尔一样,已经二十五六了。他们仍然在一起,不畏艰难,或者应该说,同甘共苦,直到差不多五十年后她去世。勃纳尔最早的资助人之一塔代·纳坦松,在画家的回忆录中,用洗练的笔触勾勒出小精灵玛特的印象,回忆她像鸟儿一样的面容,她踮起足尖的动作。她很神秘,爱妒忌,有强烈的占有欲,被一种迫害情结折磨着,并且是一个伟大而专注的忧郁症患者。1927年,勃纳尔在位于蓝色海岸的勒卡内的普通小镇波士基买了一所房子,在那里他与玛特生活在一起,牵绊着过着间或折磨的隐居生活,直到十五年后她去世。在波士基她养成一种习惯,喜欢花大量时间在浴室中,当她在浴室中时勃纳尔就为她画像,一遍又一遍,甚至在她死后仍然继续着这个系列。《浴缸里的裸女和小狗》是他作品的巅峰。这幅画从1941年也就是玛特去世前一年开始创作,但直到1946年仍未完成。她躺在那里,粉色,紫红色,金色,诸般色彩交汇幻动,像一位漂浮世界中的女神,虚弱,永恒,亦生亦灭。在她身旁的瓷砖上是她棕色的小狗,她的密友,我猜那是一只德国小猎犬,正警惕地看着它的垫子,或者可能是一方不知从哪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庇护着她的狭窄的空间摇晃着包围她,在无数色彩中悸动。她的双足,左脚在不可思议的长腿的根部拉紧,看起来像是把浴缸抻得变了形,使它的左边格外突出,而在那边的浴缸下面,同样的受力点,地板也被扯乱了,看起来正要流到角落中,与其说是地板,不如说更像是一池流动的有斑点的水。一切都在流动,安静地流动,水的宁静。你听得到一滴水滴,一圈波纹,一声悸乱的叹息。在浴者右肩旁的水上,依稀有铁锈红的斑记,是锈,或者,是干枯的血。她的右手搭在大腿上,保持反掌的姿势,让我想起第一天我们去看托德先生回来时安娜的手搭在桌上的样子,她无助的手掌向上翻着,仿佛在向一个并不存在的、站在她对面的人乞求什么。
我的安娜也是,当她生病时,总是在午后没完没了地洗澡。这能让她平静,她说。在她缓慢地走向死亡的十二个月里,整个秋冬,我们都把自己关在海边屋子里,就像勃纳尔和他的玛特在波士基那样。天气温和晴好,几乎从没有变过天,夏日看起来似乎牢不可破,令人觉察不到,这一切终将让路给被不分季节的薄雾笼罩着的寂静的年尾。安娜恐惧春天的到来,所有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匆忙与喧嚣,她说,所有的那些生命。一种幽深的梦境般的静默聚拢在我们周围,柔软,厚重,像是淤泥一般。她在二层拐角的浴室中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我常常会被吓到。我想象着她无力地滑倒,悄无声息,在那巨大的带爪脚的老浴缸中,直到她的脸浸入水下,最后呛了一口气。我从楼梯上爬下来,站在拐角处,一声不发,看起来像是定在那里,好像我是那个被呛在水下的人,透过门上的嵌板拼命地听着里面生命的动静。在我心中污秽邪恶的密室中,我希望她是如此,希望一切都如此结束,为了我也是为了她。然后我能听到她轻轻搅动水的声音,当她抬手去拿肥皂和毛巾时溅出水花的声音,于是我转身,步履沉重地走回我的房间,关上身后的门,坐在我的桌旁,看着窗外夜空闪亮的灰色,试图什么都不想。
“看看你,可怜的马克斯,”有一天她对我说,“不得不小心自己说的话,永远要保持友善。”那时她正在疗养院中,住在厢房尽头一间有转角窗的房间里,从那里望出去是一片帅气却粗野的草坪和一棵在我看来永不安静的墨绿色的大树。她恐惧的春天来了又走,而她已经病重得无法再介意它的打搅了,现在已经是湿热的夏天,她能看到的最后一个夏天。“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不得不友善?”她说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好像她已经是身在别处,远远地离开我,到了一个语言难以表述的地方。她转了转枕头上的脸,对我笑着。她的脸上是深入骨髓的疲倦,带着一种可怖的美。“你甚至不能够再对我有一点点恨,”她说,“像你以前常常做的那样。”她看了一会儿窗外的树,又转过头望着我,笑着,轻轻拍我的手。“别这么担心,”她说,“我也恨过你,有一点点。我们毕竟都是普通人。”在那时,过去式是她唯一小心选择的东西。
“你想现在去看看你的房间吗?”瓦瓦苏小姐询问道。最后一束阳光穿过我们面前的凸窗照过来,像是着火的屋中玻璃的碎片。上校正在刷着他的黄背心的前面,上面是他溅上的茶水。他看起来像被完全排除在外了。可能他在跟我说什么但我没听见。瓦瓦苏小姐领路到大厅。我对这一时刻感到非常紧张,这一刻,我将披上这座老房子,将它穿戴于身,而它就好像我堕入尘世前戴过的一顶曾经时髦的帽子,穿过的一双过时的靴子,或者一套婚礼套装——樟脑丸的味道以及不再合适的腰身,肩膀下太紧,但是每个口袋里都鼓鼓地装满了记忆。我完全没有认出大厅。它很短,狭窄逼仄,光线很暗,墙被装饰着小珠子的线槽水平分开,在下半部还糊着着了色的浮雕,看起来像有一百多年的样子。我不记得那里有过走廊。印象里前门打开是直通——嗯,我不确定它会直通哪里。厨房?我提着我的袋子跟在瓦瓦苏小姐身后,像是过去的恐怖小说里描写的教养良好的凶手,我在自己的脑海中找到了这所房子的模型,努力让它去不断抵抗那些顽固的残留记忆。所有东西都有点不合比例,所有角落都有点不真实。楼梯更陡,平台太窄,浴室的窗户看起来不是朝向大路,对面是一片旷野,而我记得它是的。我经历了一场几乎是恐慌的感受,而现实,这愚笨的自满的现实,控制住这些我自以为记得的事情,将它们打回原形。一些宝贵的东西被毁坏了,从我的指尖流走。然而,最终,我轻易地放弃了它。往昔,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往昔,并没有我们假装的那样重要。当瓦瓦苏小姐离开,留下我在这间从现在开始属于我的房间,我把外套扔到椅子上,坐在床边,深呼吸着陈腐的空气,感到自己已经跋涉了太久,疲惫经年,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一直以来,我并没有意识到的、将我束缚着的目的地;我必须待在这里,现在对我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唯一的庇护所。
(摘自《海》,[爱尔兰]约翰·班维尔著,王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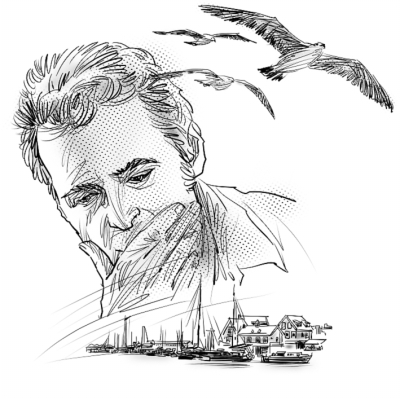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