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史之所以使部分读者产生质疑,原因多多。包括“距离过近,判断容易出现偏颇”,史家难以平衡的学术与人情关系等等。比如“某史”若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选题”,导师带领几个研究生你一章我一节,导师通稿,领导签字,报销科研经费,结项,出书,评科研奖,然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我们的后人很可能把如此出炉的“当代诗歌史”当成正史、定论——这是我日前在八宝山送别韩作荣先生之后的“忧天”之思。
我重新阅读了韩作荣十几年来送我的若干诗集、随笔(评论)、报告文学集。作为一个“虽九死犹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负情怀,他发自内心追随时代的歌唱,他对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不倦学习,不禁让我感慨:这是一位被中国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诗人。
众所周知,韩作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任职,后来任《人民文学》主编;他有20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随笔、报告文学,并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奖项。然而,我们却鲜有看到对韩作荣诗歌写作进行深入研究的文字,当代诗歌史也少有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继诗集《裸体》之后,韩作荣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多数诗人所望尘莫及的成就。尤其是以《重叠的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达到了当时整个诗坛的一流水准。
1995年上半年,我从《中国诗坛》杂志首次拜读韩作荣《重叠的水》这首近400行的长诗,颇受震撼。它回环往复的细密情绪,错落有致、远观近看皆宜的意象造型,弥漫在诗中人物身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的语言光滑而有质地,悄悄抵达读者意识深处,使人在感同身受之后心生敬佩。这样一次“向爱忏悔”的低吟,也许是一个诗人一生中最想说出的话,最难说出的话,总也找不到时机与方式说出的话。这是这个时代一部难得的作品,然而它也被批评家和诗歌史家轻易地忽略了。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这一文体的表现方法上有所创新的作家却较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作荣反映长沙历史文化、现实情境的《城市与人》高屋建瓴、别具一格,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印记。评论家唐达成先生盛赞其“率笔写来,重理虽繁,而无纷丝之乱,百思丰赡,别具淋漓之姿。统篇涵括甚大,但气势流畅,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某些段落,写得潇洒舒卷,如读散文小品,韵味悠然。这在报告文学的体裁中,或可说是别开生面的。”然我们所见的多种报告文学丛书竟常常看不到《城市与人》的影子。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文学史家的沟通太艰难了,或者可以说,很多人忙的不是地方。
我认为哪怕只凭《重叠的水》和《城市与人》这两部作品,韩作荣就已经无愧当代重要作家的名号了。我们重新评价韩作荣,并不是韩作荣本人所需要,而是我们需要,诗歌研究需要,相对客观、公允的文学史诗歌史更是需要。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冒昧地向诗评家、诗歌史家谏言。撰写批评文章、撰写当代文学史的确是件非常需要功力,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做到完全不遗漏也近乎不可能,何况各家之言见仁见智,读者众口难调,但做得比现在更好些完全是可能的。批评家要提高自己的识别力和敏感度,保证自己的书斋工作时间;文学史家对重要作家要有适当的追踪阅读,有条件的甚至可考虑建立自己的“追踪阅读队伍”;不要盲从潮流,不要把文学史写成“流派史”,向《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者学习,以作家、诗人,而非流派、组织划分章节;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评价标准,兼收并蓄他人观点,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更具学术价值,更可信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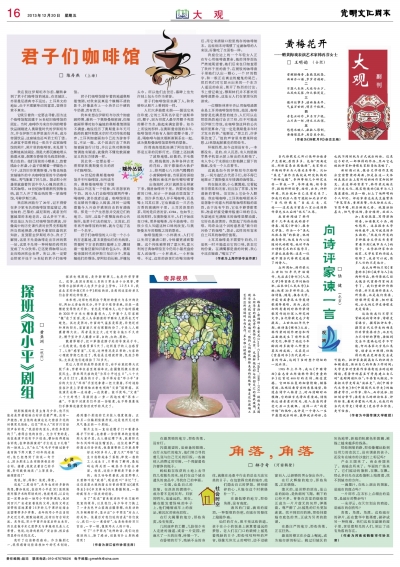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