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的散文,是青藏散文、高寒散文,伴着风雪和冰碴的散文。
王宗仁的散文,是军旅散文、生命散文,与严寒缺氧做生死较量的散文。
王宗仁经常作为亲历者向读者娓娓讲述那生死线上的历险故事,描述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汽车部队和各个雪域兵站中的艰险生活。他摸透了昆仑、唐古拉山的脾性,最懂得高原战士和兵站人的大美大爱。
他极为擅长描写令人惊骇的绝境之美、严酷之美。作品中,他反复展示西部雪域的严寒奇观。在《雪山无雪》中,他毫不掩饰地说:“唐古拉山离太阳近了,也离死亡近了!”“阳光在雪山上、雕像上都不会永存。云可以把它遮住,风可以把它卷走。”“太阳结着冰,月亮锈蚀了。”在《苦雪》中说昆仑山的太阳“真毒”,“每一缕阳光都如芒针刺背,射在雪地上连弯也不带打又反弹射回,晃得人眼睛里像揉进了灰石末一样极不舒服”,但他又猜想“那太阳肯定结了冰”。青藏大地有冷也有热,在唐古拉山下的可可西里大戈壁中,太阳则是“要把每粒沙子蒸透、融化才罢休”。更为可怕的是高原反应。作者用女站长宋姗的话说:“不冻泉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鬼门关,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地。来了还不是送死?”缺氧能使人头疼得像要“爆炸”一样,战士们“一律赤红脸膛,青紫嘴唇。手指关节肿大,指甲陷凹”,而且头发稀少,有的甚至成了秃顶。五道梁的水,“人喝下去肚子发胀、剧疼,闹肚子让你立卧不宁”。奇寒与奇热,紫外线照射,加上高原反应,王宗仁写出了那里极端的恶劣环境。
但是“冻死也不能哭”的王宗仁,在上百次翻越唐古拉山中也体验到了“缺氧的美丽”,发现了冰雪中也有温暖的美丽,戈壁滩也有荒凉的美丽。19岁当汽车兵时,他的车曾经半路抛锚,便无奈地呆在车里看那神秘的星星。“星星很亮,一颗跟着一颗闪烁着”,他觉得星星好像是对自己“笑着”,好像“自己整个身子都在星海里游荡”。他还惊呼那山岚流动的奇幻。这是他身处严寒绝境时的乐观审美。在停火断粮的危境中,他又发现了一处温泉:“它在雪山的肚子里。弥漫着热流,扩散着幸福”,“包容着一个诱人的世界”,惊呼原来高原的美丽“储存在冰层的中心”!在戈壁滩上,他由蛮荒景象想到了此地人的苦难,引用当地民歌,形容“生活像七彩霞,那也是一幅难描的画;生活是一片霞,却又常把那寒风苦雨洒!生活是一条藤,总结着几颗苦瓜;生活是一首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苦乐年华!”这凄凄惶惶的歌声,似乎能让戈壁沙地“渗出眼泪”。他慨叹“悲伤是一条河,有的人用尽一生的力气也难以渡过”。但在高原上度过了青春年华、中年以后又多次故地重游的王宗仁,一方面重温那与死神交手的噩梦,又看到了“可可西里的夜真美”。也通过别人的口批评有的人“不会享受生活”,强调“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包括这个人烟稀少的可可西里。”
王宗仁的青藏散文,总是反复咏颂那些葬身绝境的英雄儿女,歌唱那些不屈的英魂。他一直关心沿途所见和兵站旁的那些冰块或黄土垒成的坟墓,是汽车兵和兵站人在那里长眠。他们中的许多人生前都有过与冰雪、严寒、山洪、风沙或野兽做生死搏斗的经历。作者十分关心他们的故事,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他们生命的顽强、精神上的无怨无悔,比如《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中的“篓子班长”,还有那个歌声甜美的女文工团员,那个背冰做饭的大姐等。作者沉重地写道:“在这个‘生命禁区’,死人的事太常见了,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地没名没姓地长眠在这里。没有亲人在身边,一个土坑,几锹黄土,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地。”又怀着悲悯的情愫告诉读者,“他们都是父母的骨肉,他们都曾经有过温暖的家,甚至是一家之主……有的还是从中国名牌大学走出来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选择自己的未来;但是,他们肩负着使命来到西藏,离世时却来不及完成使命了。”这正像古人所说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是使命未竟已丧生。然而“他们也是支撑共和国的一部分基石……”他们是共和国的忠魂,谁敢上生命禁区的高原谁就是英雄。在王宗仁笔下,他们都是冰山上的雪莲,是生存能力极强的格桑花,常年经历着大自然的严酷考验,留下了自己的刚强与壮丽,演化成一首首令人荡气回肠的生命浩歌。
在那部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藏地兵书》的套封上,清楚地印着“神秘磅礴、钢铁旋律、冷山热血、荡气回肠、铁骨柔情、青铜品格、高天厚地、英雄史诗”,这是编者对王宗仁散文艺术美学特征的准确概括。王宗仁的散文创作始终钟情大美,始终在攀爬精神高原,放射着生命之光。
(作者为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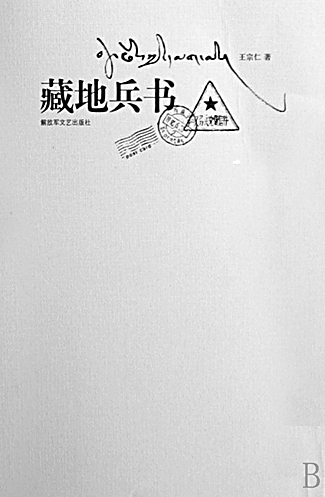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