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威:舒老师,我对您最初的了解是从《在法律的边缘》一书开始的,其中对法律的时间结构和地理空间的探究,对“司法广场化”与“司法剧场化”的比较,都给我们留下了独特而鲜活的印象。除了这种独辟蹊径的法美学研究,在您早年的其他文论中,也一直表现出对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权利义务关系等法理学或法哲学基本问题的剖析和整理。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您的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
舒国滢:如果将我的学术探索之路向前推移,那么我早年的学术兴趣还是法学领域内的理论问题,比如早在1985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法理学研究生的时候,就曾在《法学评论》上发表过《刑事法律关系初探》的文章,在风格上偏重概念分析和逻辑推演。当然,1993年我去德国进修并阅读了大量德文著作之后,我才有可能在更加宽泛的学术视野内——比如社会学、政治哲学、美学——去思考法学的问题。
1999至2000年这段时期正好处在世纪转型的时间节点,从整个人类层面看,交织着一种世纪末的惆怅与对新世纪的渴望。作为其中的一个个体,我突然有了这种双重的意识,回顾过往世纪的历史,有很多思考的沉淀,也有很多没有结论的困惑;对于新世纪未知的世界,又充满着渴望:比如,21世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它的前途、走向如何……在我当时的思考与形诸文字的那些作品中,这些都构成了很重要的主题。而这种意识对我法学思考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学研究到底是一种专业内的研究,还是应当向人文社会科学开放的研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恰好有一种写作的欲望,这个时期,我为一些专栏写了一系列有关法美学、法律与时间、地理和音乐的文章。2000年我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在法律的边缘》。这本书出版后在学生读者群里受到了好评和欢迎,他们从我的写作风格、文字中感觉到比较特别的东西,直到现在此书仍然行销不错。
冯威:我注意到《在法律的边缘》的序言题名为“寂静的旅途”,沿着这条“寂静的旅途”,我们隐约感受到了德国法哲学大师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身影。在您翻译的《法律智慧警句集》与《拉德布鲁赫传》中,可以发现同样诗性的语言、隽永的哲思、相互交织的理性与激情。您后来将译介拉氏的作品视为您“精神的宿命”,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舒国滢:对拉德布鲁赫的作品与思想的关注,说起来是很偶然的。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时注意到:拉德布鲁赫在东方比如日本、韩国特别受欢迎。他的思考方法、智慧和洞见比较贴近东方人的思考方式。我遭遇到拉德布鲁赫,正好符合我当时的学术性情。尤其是他的语言具有诗性的美感,特别强调运用简洁的、具有很大的语义含量与张力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这种语言表达本身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我阅读并翻译他的作品《法律智慧警句集》,以及他的学生阿图尔·考夫曼的《拉德布鲁赫传》时,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感。
冯威:您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的翻译,使得国内对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的研究走向了“理性论辩”“有效证成”的前沿和纵深地带。而随着《走出“明希豪森困境”》、《从方法论看抽象法理学的发展》、《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等文论的发表,您大力提倡回归到一种“内在观点的法学”或“法学之内的法学”。您早年作品中诗性的、形象化的语言一转而为严谨的、分析性的语言,对法哲学以及交叉学科的关怀也一转而为对法学方法论的探究。这些能否视为您理论旨趣的“转向”?
舒国滢:通过阅读德国法学家们的著作,我注意到:中国的法学与德国的法学存在某种差异,我们法学家的思考和产出与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我想首先原原本本地搞清楚德国最前沿的法哲学或法理学的理论发展,试图将其展现给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德国法学家到底怎样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在我看来,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对有关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的引介。这就是我为什么“转向”的最重要原因。我认为中国法学需要有一个对比和参照,要使我们的法学家开始注意在思考和研究中重视方法、重视论证。我们过去喜欢的大而化之、只给结论不重推论的研究或思考方式,确实不符合法学这门学科所需要的规范和标准。我们的法学家并没有过多地去思考法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法学家群体(特别是我们的法理学家)可能认为,法学是一个交叉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进入到法学的领域之中;在法学研究中,哲学、社会学、逻辑学、语言学都可以随意出入其间,最后形成的知识就是法学。我并不是说法学不能与其他学科交叉,而是说法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有它专属性的、作为学科架构的东西,这种架构使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我的研究发现,在西方的法学史上,法学首先有一个恒定的研究对象,即各个时代的实在法;其次,法学研究形成一个职业的群体,即法学家阶层。这两个原因使法学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即实践的、规范的、教义学的学问,其中,教义学构成了法学的基本性格和基质,它使法学在思考方式、方法选择、论证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法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知识标准、概念、规则体系以及信仰体系。法学家一般是尊重通说的,以通说作为其思考前提。而要推翻通说,必须有人提出一个更强的范式,来颠覆已经得到尊重的通说。这是法教义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谓的“内在观点的法学”或“法学内之法学”。
冯威:在我看来,您实际上熟悉三种语言:诗性语言,分析性语言,以及翻译的语言。它们又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思维特质与工作领域:法美学,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学经典的译介。您是否认同这种评价?
舒国滢: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我在自己的求学和研究中,有时候并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可能需要尝试着去做才会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还有一些潜力没有开发。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早就发现了自己运用诗性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以及用诗性语言思考问题的潜质。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古汉语很优美,1975年曾用古文写过一篇“大字报”(当时流行这个,但我是批判学生反老师的),不过当时对我写的东西是什么,甚至教语文的老师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想来不过趣事一桩。高考的时候,我首选的是想去大学中文系。但1979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读法学时,这种潜质受到抑制。直到我读到雅各布·格林、吉尔克、耶林和拉德布鲁赫的作品后,我才发现原来法学著作也可以用诗性的、文学的语言来表达的。我从他们的法学著作中重新发现自我潜在的诗性表达能力。实际上,法学并不限于条文叙述的机械表达,有些法学作品也可以如佐姆所说的那样,做到“犹如一道闪电照亮大地遥远的风景”。
至于理性、分析性、逻辑语言的使用,这种能力是我在阅读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哈特《法的概念》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的。我发现自己对分析哲学的语言并不是隔膜的,而是非常熟悉的。其实,这种语言与诗性的语言并行不悖。
翻译语言,并不是一种独立于诗性语言、分析性语言之外的语言。就翻译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时要有所选择,因为并非任何作品都适合某个人来翻译。对我而言,专业领域内作品的翻译是有必要的,我也很感兴趣。此外,翻译最好要参考两种以上的外语译本,比如,在翻译德文时可以借助英文译本或日文译本,以达到平实、正确的把握。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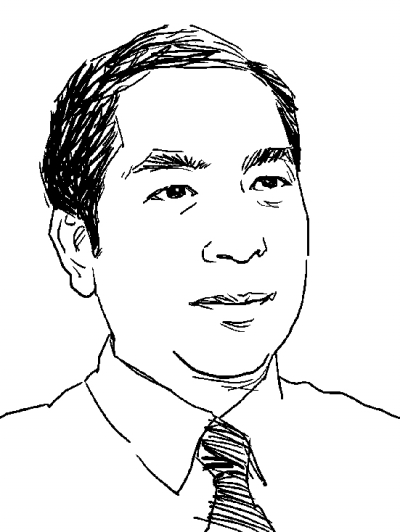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