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1986)写有两本谈论美学的小书,一本叫做《谈美》,写于1932年,一本名为《谈美书简》,写于1980年。尽管谈论对象(“美”)与书写形式(“书信体”)相同,却由于写作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作者的基本观点与关注问题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也就使得这两本书的内容有了巨大的时代差异。
美与“人生的艺术化”
写作《谈美》一书时,朱光潜正就读于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由于经济拮据,他不时地写点小文章,赚些稿费养活自己,叶圣陶等人创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他时常投稿的地方。此前他已出版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该书用书信的笔法,以朋友的口吻,谈读书、谈作文、谈人生、谈理想,语言平易而不失生动,自然而又亲切,一经出版即大获成功,成为当时青年最为喜欢的读物之一。《谈美》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在开明书店的初版封面上,这本书的副标题名为“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以示与前书的关联。这本书同样深受读者欢迎。一个有趣的佐证是,该书出版之后,坊间很快出现了一本跟风之作,名曰《致青年》,副标题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作者署名“朱光潸”。不惟书名、作者相似,该书的装帧设计也与《谈美》一书极为雷同,几可乱真。有意思的是,此书居然也行销一时。更有意思的是,朱光潜先生在看到此书之后,还给这位几乎同名同姓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发表在了《申报》上,大意是劝诫此君行事要磊落,做人要厚道。
《谈美》共由15篇文章组成。要而言之,可分成两大部分,第1至第8篇主要谈审美欣赏,第9至第14篇主要谈艺术创造。而全书之核心,是对美感的分析。朱光潜自称是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他认同克罗齐的“直觉”说,而又加以批判性地接受。所谓直觉,就是不假概念只见形象的认知,这种形象构成了一种独立自足的审美意象。他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中提到,人们面对一棵松树,可以有三种态度:科学的、实用的和美感的。科学的态度牵涉到真,需要抽象思维;实用的态度意在求善,心理活动偏重意志;美感的态度即是求美,它不计较实用,不考虑因果,靠的就是“直觉”。在他看来,美感就是形象的直觉,而美就是心物合一的产物。
朱光潜还吸收了康德对美的超功利性的分析以及19世纪末审美心理学诸流派的美学观,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审美距离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和游戏说等。他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美感经验,援以古典诗词、书法、音乐、绘画等文艺作品,将这些貌似枯燥的理论融入生动鲜活的实例之中,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娓娓道来,浑化无迹,令人耳目一新,欣然领会。还是引一段原文为证: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时“清苦”。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朱自清曾称赞朱光潜的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绝非过誉之辞。
20世纪30年代,国内局势岌岌可危,值此危急存亡之际,朱光潜先生对着中国的青年大谈美学,实在存有深义。他认为,局势之乱,人心之坏,与国人只知追名逐利而未能免俗息息相关。“俗”,就是缺乏美感的修养。其疗救之道,就是通过美与艺术。
朱光潜不是第一个开出这种药方的人。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在他看来,“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蔡先生在北大身体力行,力主开设美学课程。再向前追溯,1795年,德国诗人和美学家席勒出版了《美育书简》,主张通过审美来弥合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从而达至人性的完善。他们都将审美视为陶冶性情、完善人性的路径,将美学视为启蒙的手段。朱光潜在《谈美》的最后一篇中发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呼喊,认为人生与艺术紧密相关,不相分离,提倡过一种情趣化的生活。
学术思想的时代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思想界掀起过两次美学热潮。第一次是发生在1956年至1962年之间的美学大讨论。此次美学大讨论,有近百人参与,发表文章四百余篇,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广,实属罕见。比如,姚文元就写过多篇文章参与讨论,比较著名的一篇是发表在1958年5月3日《文艺报》上的《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在当时早已卓然成名的美学家朱光潜,正是这场美学大讨论的“领衔主演”。
作为著名美学家的朱光潜,因为素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艺的自主性,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与左翼作家格格不入,自然成为重点批判对象。1948年3月1日创刊于香港的左翼刊物《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郭沫若和邵荃麟分别撰文,对朱光潜展开批判。郭沫若将朱光潜定名为“蓝色作家”,直斥其思想的反动性;邵荃麟将朱光潜和梁实秋、沈从文三人视为“为艺术而艺术论”的代表人物,称其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1948年9月,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也发表了题为《论朱光潜》的文章,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反映了“没落中的地主阶级的士大夫意识”。新中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风势头更猛,蔡仪、黄药眠等美学家也继续撰文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朱光潜先生不得不反躬自省,认真检讨自己的学术思想。1956年6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号)上,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该文对他解放前所接受的西方“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痛彻心扉地否定与清理。在文章最后,他表态道:
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于我不断地关怀和教育,使我有机会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和学习,我才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思想的反动性。关于美学方面,我又得到蔡仪、黄药眠诸同志的善意的批评,加上近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初步学习,我自信在基本上已经从腐朽思想的泥淖中拔了出来。对于美学上一些个别问题,我至今认识还是很模糊的,我愿意对它们继续探讨。
朱光潜在自传中提到,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都向他打过招呼,告诉他此次讨论意在澄清思想,不是整人。此前,蔡仪、黄药眠、贺麟等人所写的批判朱光潜的文章也已组织好,蓄势待发。
恰在此时,“双百方针”正式确立了。这构成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背景。“双百方针”的确立,使酝酿中的对朱光潜的批判转变了风向,相对温和的学术探讨从而成为可能。《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的“编者按”印证了此点:
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它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
如果说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拉开了美学大讨论的序幕,那么“双百方针”的确立则极大地推其波而助其澜,使人们参与美学讨论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时之间,《人民日报》、《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量级的报刊杂志纷纷发表美学论文,形成美学大讨论的热潮。此次讨论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集中于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并形成了四大美学派别: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太、吕荧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不过,自始至终,这场学术论争终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操控下进行的,其自由也只能是相对而言。高、吕二人的主观派因为“政治不正确”很快销声匿迹。因此,争论基本是在其他三派之间进行。朱光潜对他在新中国前形成的“美在心物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主客观统一说。不过,蔡仪、李泽厚等人都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判,说他名为主客统一说,实为主观论。面对批评,朱光潜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与对手们辩难析理,显示了其人的学术尊严与人格风范。而很有意味的是,素来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正统的蔡仪,其所持的客观说因为具有机械性,同样受到了诸多批评,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场讨论的学术独立性。敏泽先生在忆及这场美学大讨论时指出:“由于没有外在的政治干预和政治后果,主要一点就是毛主席没有干预,所以,学术气氛相对说是比较好的。否则,那后果就可能比较严重了。”
不过,随着“文革”到来,美学讨论戛然而止。
《谈美书简》构成新时期实践美学的重要一环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迎来了第二次美学热潮,经历了十年“文革”的中国思想界“久旱盼甘霖”,此次美学热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思想启蒙的性质。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的李泽厚,成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灵魂人物。
此时的朱光潜已是80余岁的老人了。进入耄耋之年的朱先生,仍以巨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投入到学术工作中。《谈美书简》即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约稿而写。
《谈美书简》由13篇文章组成,依其内容可以分成两大方面:一方面谈论如何学习美学,另一方面论述了美学原理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如何学习美学,朱光潜提到了这样几点:一是学习跨学科知识,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将人看做整体的有机观,四是攻克外语关,五是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等。对于美学理论问题,朱光潜谈到了艺术的本质、美感、形象思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典型、悲剧和喜剧等基本问题。
朱光潜自承,新中国后,“这三十年来我学的主要是马列主义。译文读不懂的必对照德文、俄文、法文和英文的原文,并且对译文错误或欠妥处都作了笔记,提出了校改意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洗礼的朱光潜,其美学思想相比于新中国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他通过对《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解读,否弃了克罗齐的美在直觉说,提出美感是由生产劳动引起的,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劳动。
相比《谈美》,《谈美书简》所体现的不仅是思想的变化,还有文风的改变。正如朱光潜在该书结束语中提到的,他有位朋友在看过《谈美书简》文稿之后告诉他:“看过你在解放前写的那部《谈美》,拿这部新作和它比起来,我们感觉到你现在缺乏过去那种亲切感和深入浅出的文笔了;偶尔不免有‘高头讲章’的气味,不大好懂,有时甚至老气横秋,发点脾气。”的确,《谈美书简》少了《谈美》那种信手拈来的优雅从容。一方面,为了阐发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书中布满大段大段征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这就使得文气不免凝涩不舒;另一方面,亲历“文革”戕害人性摧残文艺的朱光潜,心中郁郁不平之气与激愤之情时时溢于笔端,批判性的话语亦俯拾可见。试举一例,在谈到要冲破江青等人设置的“三突出”禁区时,他概述了西方不同文学流派对人物性格的描写特点,然后指出:“我约略叙述这种历史转变,因为从此可以揭示‘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所吹嘘的‘三突出’谬论的反动性。这批害人虫妄图把封建时代突出统治阶层首脑人物的老办法拖回到现代文艺作品里来,骨子里还是为着突出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作思想准备。”
自然,我们需要充分肯定《谈美书简》的学术价值。朱光潜在书中提出的美感起源于劳动,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的观点,构成新时期实践美学的重要一环。不过,毋庸讳言,《谈美书简》也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其中论述的诸多问题,如形象思维、典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随着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的推进,很快就不再是美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朱光潜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实际上,在西方理论史上,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很多解答,如摹仿说、巫术说、游戏说等等,尤以巫术说最具影响,李泽厚提出的“巫史传统”亦与此不无相关。朱光潜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劳动说所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他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会造成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美学界,实践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即屡遭质疑,诸如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等所谓的后实践美学风起云涌,意欲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仍然坚守的移情说、内摹仿说,以及怀着矛盾心态提及的游戏说,因其形象地揭示了人类审美心理的特点,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至于他在《谈美》中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作为个体人生的一种终极生存美学,有着永恒的意义。
应该看到,作为一本“大家小书”,与《谈美》一样,《谈美书简》为美学的普及作出了杰出贡献。此书在1980年8月甫一出版,就大受欢迎,销量巨大。笔者手头的这本,为1982年6月第3次印刷,印数14.5万册,定价0.5元。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多次再版,常销不衰。在教育部指定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高中部分的36种书中,《谈美书简》赫然在列。不过,窃以为,相较而言,无论是从文学性的角度还是从高中生的接受能力来看,《谈美》似乎更为适合。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
(本文编辑 宋文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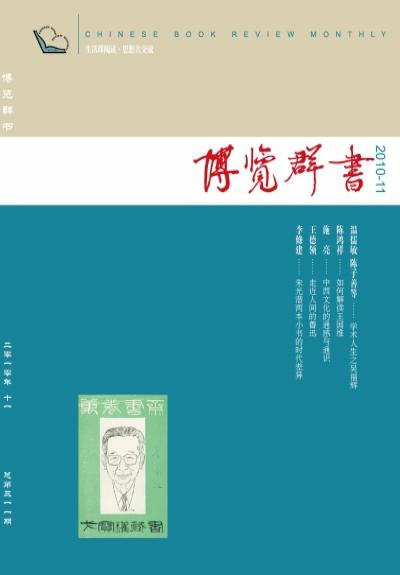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