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之际大诗人阮籍(210-263)的传记材料,有两处细节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晋书·阮籍传》记载他: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一是他不同意儿子阮浑(字长成)参加到林下之游当中来。《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浑长成,风韵气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前者可算是阮籍一生经历特别是精神历程中始终走投无路、非常痛苦的绝好象征;后一事则为前一事的重要补充。他本人与嵇康、山涛等人把臂入林、喝酒谈玄,似乎很高雅潇洒,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高明,所以不同意儿子也来走这条路;侄儿阮咸(仲容)加入进来,他大约也不赞成,只是隔着一层,无权多管,儿子也想挤进来“作达”则绝对不行,直接下死命令予以禁止。
中国的父亲最关心爱护的就是儿子,永远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阮籍不让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样子,可知他是自以为非的了。一个走投无路而又头脑清醒的人,肯定自以为非,否则他就是个糊涂虫,更完全不是阮籍了。
理想主义者阮籍曾经希望当建功立业的英雄;后来又设想当一名退出政治甚至社会的隐士;最后又想做一个绝对自由的“大人先生”,可官可隐,干什么都全无挂碍——可是几条路全没有走得通,心情始终不舒畅,只得一味酣饮,写些诗文以释愤抒情,寄托幽思。阮籍是个复杂而清醒的人,内心一直十分痛苦。大约是因为多年饮酒过量,慢性中毒吧,他只活了五十多岁。
阮籍青少年时代接受了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原想有一番作为,为建设一个稳定和平、礼乐齐备的理想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在诗中回忆往事,自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诗》其十五);又形容自己早年的大志是“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危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文武全才,堪称英雄。他在早年的论文《乐论》中对礼乐齐备的理想社会作了全面的描述,又在另一篇论文《通易论》中从哲学的高度论述社会应当阴阳协和、“万物莫不一”。这两篇文章调子都很高,很正统。对他的意见,连嵇康都不大赞成,其《声无哀乐论》一文就详细阐述了与《乐论》正好相反的音乐观。
当时的现实生活离青年阮籍的理想极其遥远:朝廷上是一个根本不能执政的小孩子(曹芳)当皇帝,当权的曹爽集团十分腐败,阮籍认为他们早晚要垮台;被他们挤到边缘去的司马懿父子正在准备全面反击。政局不稳,山雨欲来。阮籍当不成什么英雄,理想社会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由于阮籍才华横溢名声很大,当权派那边几次三番拉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干,或不得已出来敷衍几天,然后就托病回乡,当起隐士来:他不想陷入旋涡与他们同归于尽。他同嵇康、山涛等人结为“七贤”林下之游,肆意酣畅,就正在这阴云密布的正始(齐王芳年号,240-249)中后期;他那著名的《咏怀诗》也写于此时(详见拙作《诗史互证与诗心探幽——关于诗人阮籍的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组诗内容非常丰富而晦涩,怎样理解至今异说纷纭,尚待从容讨论;其中颇有游仙之作,写得活灵活现,而他其实明白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仙,谈谈神仙无非表示对自由的向往而已。
可是知名之士要想隐居也是不容易的,曹爽集团那边跳出一个叫伏义的官派文人,写来一封官气十足又臭又长的信,责备他不肯合作,劝他快快出山,否则后果很严重,其中有些话充满杀机。竹林之游似乎很潇洒,其实面临很大的压力。
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之变,迅速消灭了曹爽集团,阮籍开始在司马氏集团手下当官,参与机密,他看出了这个集团代表着政局的未来,他真心支持这一派势力(详见拙作《阮籍是支持司马氏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历史学版;又蒋寅先生对该文提出批评,见《阮籍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4日后海副刊);这一政治态度又见之于他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与晋王荐卢播书》等文章。阮籍不是那种写违心文章、做违心之事的人。但阮籍做不到全心全意支持司马氏集团,这一家子离他理想境界甚远,不能让他完全佩服;时局只不过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而已。司马氏父子杀起异己分子来毫不留情,他们手下的一批鹰犬尤其可怕,所以阮籍一向很谨慎,“晋文王(按即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这时阮籍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描写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大人先生”对儒家君子和道家隐士都提出批评,他自己披发居于巨海之中,游于异方奇域,徘徊无所终结,心态和行动都极其自由:“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繇于四运,翻翱翔于八隅……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彻底超越了现实世界,同时超越了自我,抛弃一切世俗的礼法习俗,遗世独立;不仅如此,还要超越自然,超越时空,回到宇宙初始的混沌状态中去,从而保持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幸福。这在某种意义上近于庄子哲学中“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庄子·在宥》)那种完全超脱的境界;而成为问题的是阮籍本人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积极进取建立功业的儒家之志,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道家的精神自由与儒家的有所作为思想进行了化合和改造,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如果我们还记得阮籍在官场中的“至慎”,就会明白这种“大人先生”式的自由不过是他的白日梦,完全无从实现;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置当时社会公认的礼俗于不顾,我行我素,并且一味酣饮,很“任诞”(放诞而不守规矩)地实行庄子所说的“全于酒”(《庄子·达生》),也就是在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中暂得无拘无束的解放和自由。当时司马昭面临极复杂极艰巨的夺取全部中央政权的任务,非常注意拉拢名士,扩大影响,增强凝聚力,因此容忍了阮籍惊世骇俗的生活作风,当他受到礼法之士攻击的时候一再予以保护。在皇位尚未到手之前,身边有这样一个色彩怪异的大名士,对自己有益无害,所以司马氏对于政治上支持自己的大名士阮籍礼遇有加。如果换一个背景,则阮籍将失去他“任诞”的自由。阮籍式的作风在中国古代颇为罕见,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阮籍同时又是个精于估计政治形势的人,是个明白人,所以他晚年虽然身居高位,却分明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所有的理想都没有实现。所以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他不许儿子走自己的道路,道理也正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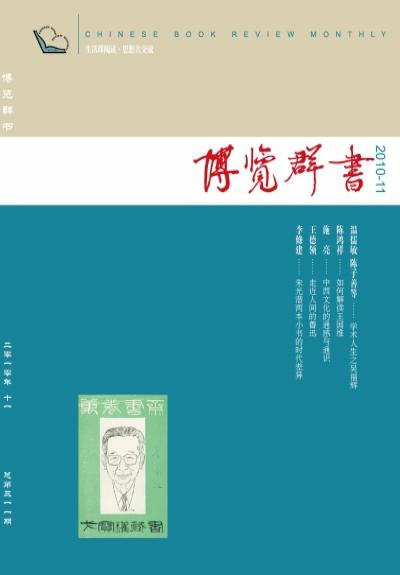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