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之吴福辉
吴福辉,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1939年生于上海。1959年起在辽宁任中学语文教员。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1981年毕业,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等职。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攻20世纪30年代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现代市民文学和海派、京派文学等。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游走双城》、《多棱镜下》等。
2010年,吴福辉推出力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本刊特邀温儒敏、陈子善、刘勇、王中忱等学者撰文,并通过专访,展现吴福辉对其个人乃至一代学者学术人生经历的思考。
突破: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实践
问: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中,您谈及今人研究文学史的五种提法:生态,文学地图和大文学,双翼论,常态与先锋,多元合力共生,并说大家都在思索文学史书写要往前突破的问题。您在今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如何解决“突破”的问题?
吴福辉:首先,这是一部文学史书写的实践性成果。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这几种观念,大家基本都是在文章中提出来的,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完完整整的成果。可以设想,假若鲁迅在课堂上或者书中跟你讲,小说不应该像宋明的“说部”那样写了,也不应该像晚清的谴责小说那样写了,应该怎么写,鲁迅给你说了一大套理论,这是一种效果。还有一种效果是鲁迅根本就不讲小说应该怎样写,但他写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关于现代小说究竟怎么写,你看他的小说就行了。也就是说,新的思想照耀了新的写作,这在当时达到了何种程度,鲁迅那代人也主要是通过写作实践来说明的。关于新的文学史该怎么去写,我不仅在文章中讨论过,更去做了,有了实践性的成果,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在我写出这部文学史之后,曾有刊物主编约我再谈谈如何书写文学史,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出来。我不是理论家,我的文学史写作成果应该比我所能说的理论多得多;后人或者今人可以从这本文学史里,按照他们的认识去理解的东西,也应该比我写的要多。
其次,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几种说法并非彼此隔绝,实际上倒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渗透的。我在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认识方式和书写方式之中,就综合考虑并借鉴了这些提法。比如我从严家炎先生的“文学生态”里面想到文学史不能无视人的生态,不能不写作家的心态以及与心态直接相关的文化物质环境。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很有警醒作用,我虽然不同意让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平行地进入文学史,却深受启发,考虑到如何将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市民文学,而现代市民文学自从“海派”浮出,就具有了先锋、通俗的双重性质,不那么截然分明了。这也是陈思和把“先锋”“常态”作为两种互动的文学态势提出的原因。我可以把握住文学史上典范的先锋文学来解剖,也要将大众化的常态线索紧紧抓住,把农民大众文学和市民大众文学扩大来书写。而杨义的“大文学版图说”,启示我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空间,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在这些意义上,我想到我这部文学史可以加上“发展”两个字。
再次,这部文学史在书写方式上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重新整理材料,用史料说话。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这两个概念提出以后,原来以政治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史就开始解体,我的这部文学史就是解体以后的产物。政治性的文学史解体之后,重写文学史,就要从原始史料开始,去探究现代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发展的,怎么传播的,怎么被接受的。
第二,把文学深入地放到文化环境中去理解。这个文化环境包括文字、教育、出版、传媒等。这本书就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包括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社团、流派;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文学批评、翻译;话剧、电影,等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的这本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另外加上丰富的插图,把文学的空间大大地拓展了。
第三,打破“主流型”的文学史,建立一种平等的、驳杂的文学图景。要排除把一种文学作为主流而把别的文学的地位降到很低的非真实状况,要打破这样一种“主流型”的文学史。比如过去把革命文学作为主流,其他的都要服从革命文学。在革命文学面前,或者被打败,或者被同化。假若现在我们把现代主义文学捧得最高,一切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都成次要的,在诗歌上就要以卞之琳、穆旦为主,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主义色彩是最浓,其他的比如艾青有现代主义色彩,就稍微低一等来叙述。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写法,为我现在所不取。我们要给予各种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比较平等地来描绘整个现代文学的图景。
实际上,这本书还暗含了我个人的一些理想,是一本个性化的文学史。既然是我个人写的,那么我的语言是个性化的,看法也是个性化的。所以说,这是一本比较新的、符合我个人个性的、尽量贴近读者的文学史。
问:“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时限性的学术史,您选择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让人耳目一新。请您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处理现代文学史的起点问题的?
吴福辉:文学的发生有一个“文化环境”。过去的文学史是从政治环境叙述起的,比如国民政府之前,就讲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政府怎么样对抗,再往前就是和清政府怎样对抗。这样的话,突出的是政治斗争。而文化环境才是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都要“折射”到文化环境中去发生对文学的作用。我选择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作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是为了强调以后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学,当年已经处于一个与古典文学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了。这个环境除去经济生产力的水平之外,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界的急剧变动和物质文化条件的重新构成,而这两个方面“折射”到文化环境中,都可体现在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上面。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第一章是“孕育新机”,主要是讲晚清时期的文学环境。我同意文学现代性就是从晚清开始发生的观点,所以我在书中特别提出了“文学大事1903年版图”,并指出晚清时期是文学现代性的积累时代。我不主张用一本书或一个具体事件来划定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确切时间,是因为没有哪个时间能够担当。现在所举的起源时间,换成另外一本书或另外一个事件,也可以讲通。既然是模糊的,我们就不如模糊地用较长的一个时段来描述它。但积累到“五四”时期就总爆发了。“五四”是一个“爆发期”,“爆”出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来。就像闻一多的诗《一句话》说的,“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不愧是从“五四”时代走出来的人。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常重要。
独立:个性化的文学史不是“百衲衣”
问:您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研究,是由“左翼”、“京派”、“海派”三种文学形态构成的,并形成了个人的学术个性。现在这本《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从不同的地域流派到一部多元空间的文学史。您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回顾“个人文学研究史”时,有什么感触?
吴福辉: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广阔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个性化的文学史,还要立足于自己以前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不妨碍你吸收学术界整体或个别的成绩)。特别是核心部位,写作者必须独立地掌握一些材料,独立地研究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人在分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就说这本书写得有些特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我的个别的独立性研究,比如地域文学研究、都市文学研究、城乡文学研究等。过去的这些研究构成了我这本文学史的空间叙述特色。这里面既有我原来掌握的资料,又有我新的思考和观念。有了对“左翼”、“京派”、“海派”的研究基础,有了我对上海、北平两大市民社会及其文化的认识,才使得这本文学史在广泛吸收别人研究成果之外,突出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文学史不能最后变成和尚的“百衲衣”,东拼西凑,却没有一块是自己的“布”。所以,钱理群对我这本书的评价是,“既是一个集大成者,又是一个新的开拓者”。
这里就京、海派多说几句。我的“个人研究史”,从研究左翼文学开始,然后是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对京、海派文学的研究,又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比如,我在12岁之前是在上海生活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既有上海繁华现代的一面,也有对下层市民生活的一些认识。记得那时上海的街头有很多书摊,白天摆开来,晚上一合起来就走了。书摊上层架子上一般摆的是连环画,下面摆的是有字的书,如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全是通俗文学。我童年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以说,我很容易理解30年代“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我也很明白夏衍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何在军管上海的日子里会关心市民有没有小报看的问题,会再去组织人办小报。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场,大量的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对上海的理解、对“海派”的关注,与我童年时期在上海的见闻自然密不可分。我的历史研究就有了自身的感性经验打“底”。
我曾经说过,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的文学研究就有了一种“回乡”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的文学研究和我的生命结合了起来。
历练:在时代的风雨中自习
问:您高中毕业后去了中学教书,又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您能具体说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读书治学的经历吗?
吴福辉:时代对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中专毕业时学习很好,原本是可以保送上大学的(有的老师也替我争取过),但是由于家庭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没获批准。这样就参加工作了。我的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主要是靠自学的。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我的课外阅读比较早,不是我的家里有闲书供我自由阅读,而是我身处市民文化的大环境之中有些便利条件。当时我家在上海东余杭路一家大南货店的楼上,窗下就有书摊,我可以像张爱玲说的挂下篮子去租书读(她是买吃食)。在东北,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全集》。我喜欢写作,记得读中学那会儿,语文老师特许我可以写长文,一篇作文写满一本作文簿也无碍。我曾把一首唐人绝句改编成一部短剧,是那种标明“化入”、“淡出”、“摇镜头”等提示语的电影文学剧本写法。这也得益于当时刚刚创刊的《中国电影》杂志。那会儿一个学生订不起一本杂志,我是向语文老师借来看的。杂志上刊有剧本,我也学着改编剧本。
在东北教书时,就结合教书进行自学。那会儿周六放假我经常不回家,就留在学校里,自己准备点干粮,中午就不出去吃饭了,一个人在教研室看一天的书。我读了大量苏俄、法国、中国作品,也读了一些文学史、文学理论著作。教书还锻炼了我独立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锤炼了我的艺术感受力。这对之后我考取北大研究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段经历特别有意思,那时一个被打成“右派”的音乐老师做图书管理员,学校不放心他,有一段时间就分配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们俩在图书库夹缝里放床,书架就在我的床边。我就有了随便从书架上取书的便利。
除了在图书馆看书,我还尽力买书。因为我觉得书还是自己拥有的好,用着方便。教书之初,我每月挣四十二块五毛钱,有时从中拿出五块八块来买书,剩下的合起来要养活四口之家。当时住的地方不到十平米,屋里除了炕以外全是书。有两书架的书,还有一些书占了本应放衣服、杂物的地方,用六七个木头箱子高高叠起来。因为附近是铁矿山,这些木头箱子是用来装爆破用的火药的,所以可以很廉价地买来装书。
当时买的书比现在还杂。除了文学方面的书,我还买了不少教育方面的书,比如列宁夫人文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他的教育理论。1963年前后,我在教书之余开始给辽宁的地方报刊写稿,写的都是教育随笔。我在自己的语文教学经验中寻找题目,写成短文投出去。起初退稿不断,多半是文不对那报纸的题。大约一年后终于成功了。得到第一笔5元的稿费我舍不得到邮局去兑现,将汇单放在手里好多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教书与自学。过去我还买了不少线装书,我还买了不少与中学语文课本对应的参考书,比如《论语》、《左传》、《战国策》等,都是从上海旧书店搜罗来的石印线装书,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烧了。
问:您怎么看时代对您这一代学人的影响?
吴福辉:可以说,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代学者。这一代特殊群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大学生。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在高中、初中读书的六个年级的学生,后来下乡当了“知青”被称做“老三届”。其实还有他们的老大哥即“文革”中的在校大学生。前者学习好的考了77届78届的大学本科,后者考了78届的研究生。当时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录取的六个研究生中,就有四个同学是有过“下乡”经历的,他们很容易被归到“知青”一代去。
另一部分是“知青”前的一代,就像我和老钱(钱理群)。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已经读完高中二年级了。“文革”开始时,我们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教了7年中学语文,老钱在贵州教中专语文)。这一代人不大好概括,我一般称作是“红领巾”的一代。像我是1950年带上红领巾的,是新中国后最早带上红领巾的。或者叫作“青春万岁”的一代,因为王蒙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的就是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我们。
“文革”后的第一代学者的特点,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最多是小学时期横跨了解放前后。我们接受的就是马列主义,后来又加上了毛泽东思想。受的教育就是要有理想、顾大局、服从集体,要从骨子里克服个人主义,实现百年来振兴中华、建成最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崇高目标。所以我们都很“听话”,很有激情,并在火热理想的指引下把专业上的努力全部献给既定的政治宏图。我们当时都很深入地参与到政治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参与进去之后,就会有不同的经历,有思想的困窘、波折,起伏动荡的反思。特别是在“文革”的痛苦经历之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过来激发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的强劲的责任感。比如钱理群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就是站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思考来尽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这种时代人格自然因人而异,有隐有显,但大都存在。比如我虽然没有老钱那样鲜明,但我也不会去做书虫,搞纯书斋研究。我所信奉的学术准则曾经借一句外国学者的话在文章中清楚表达过,就是: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
问:“文革”结束后,您考入北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北大的求学生活,对您个人在思想和学术上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福辉:我在北大读研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懂得了坚持独立的、自由的学术品格是第一位重要的,学会了一切要经过自己思考得出结论,绝不盲从,再不能做让自己的头脑叫别人马队去随意践踏的这种蠢事。可以说,即使我这研究生的三年什么都没学到,我也算挺起了思想的脊梁。
北大品格对我自身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这里的前辈学人。大学是大师之谓也。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却十分生动活泼。比如先生谈到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先生还常常鼓励我们,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先生的话,让我身上陡然升起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
在北大读研主要也是靠自学,跑图书馆抢椅子自习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也买了一些书。1970年代末期一个月拿出20元钱、30元钱来重购“文革”损失的书籍是要有点决心的。这时期我买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买现代文学的基本作品(有的人不买基本作品,只买理论著作)。但我也不是所有的基本作品都买,比如《郭沫若全集》,我只买了前面五卷,因为这五卷已经包含了郭沫若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这是我所看重的。他的历史剧我就去买单行本。海派京派的作品我就不放过任何一本了。古代当代的文学书自然也买。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作了很多注释,我们就根据那些注释去补书。但我已经没有可能做现代文学的藏书家了(后来我就依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这些旧版本的收藏是我在馆里的重要业务工作,我是尽了力的),我的书没有什么版本价值。所以,我现在的藏书只是基本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自己适用而已。
关于北大的学风,我曾多次举吴组缃先生讲课的例子来说明。那时吴先生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这个故事我多次讲过,因为我自认是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北大校风教育。对于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来讲,王瑶、吴组缃、林庚等先生,就是“活”的“现代精神”的教育和北大教育。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北大独立自由、相互平等的学术风气。这些先生学贯古今、视野开阔,从知识教育、思想承传的角度来看,高山仰止,是我们很难企及,又是需终身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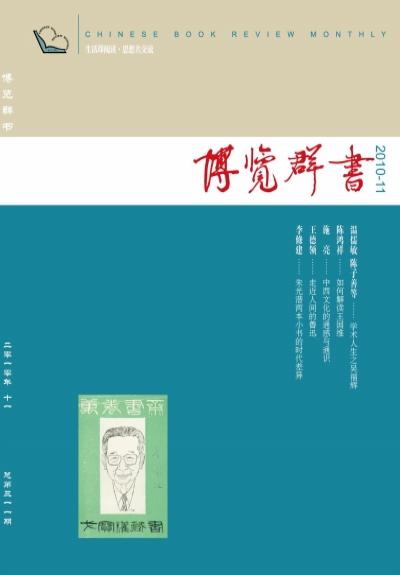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