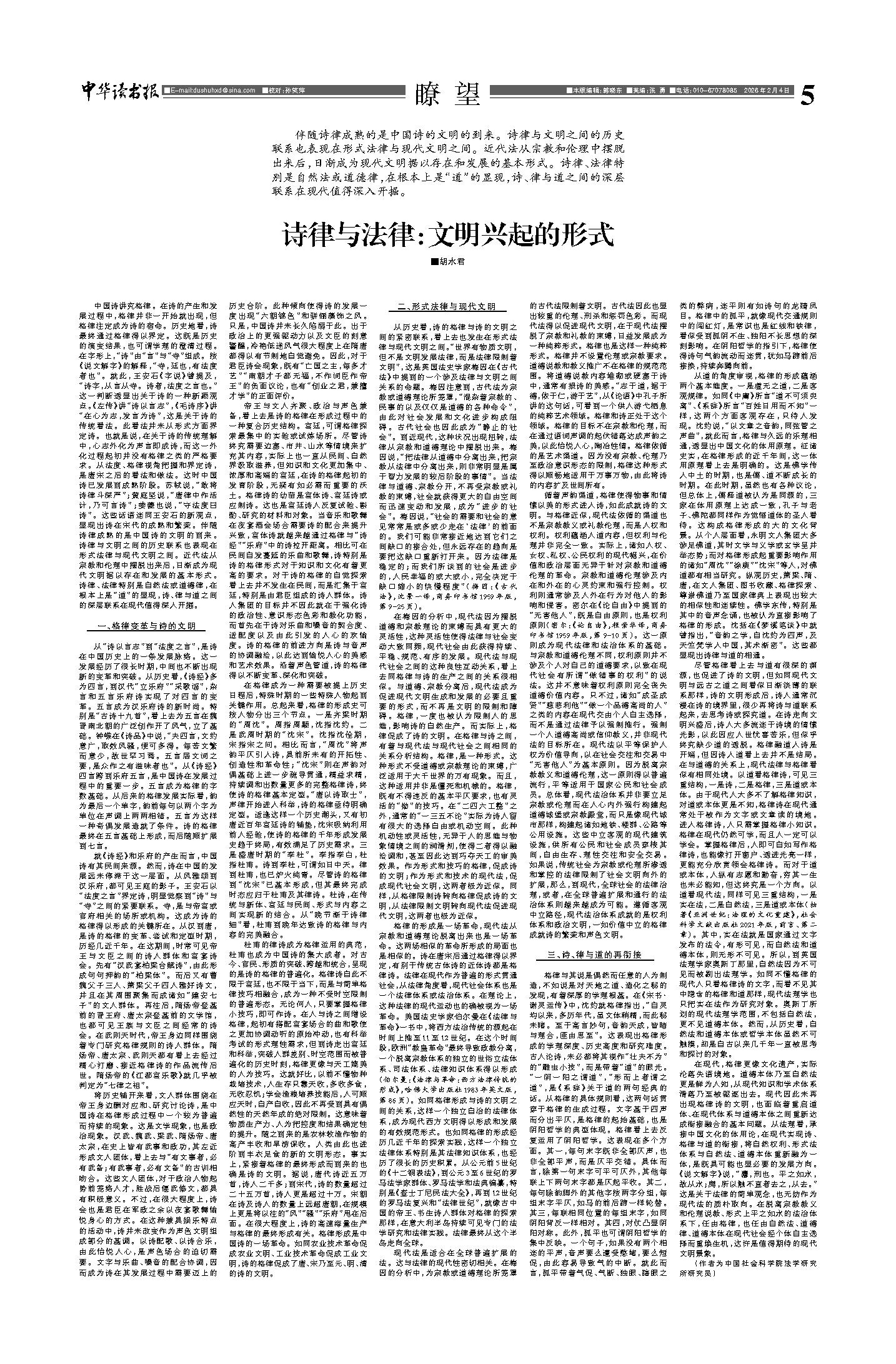诗律与法律:文明兴起的形式
伴随诗律成熟的是中国诗的文明的到来。诗律与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表现在形式法律与现代文明之间。近代法从宗教和伦理中摆脱出来后,日渐成为现代文明据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诗律、法律特别是自然法或道德律,在根本上是“道”的显现,诗、律与道之间的深层联系在现代值得深入开掘。
中国诗讲究格律。在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格律并非一开始就出现,但格律注定成为诗的宿命。历史地看,诗最终通过格律得以界定。这既是历史的演变结果,也可谓学理的澄清过程。在字形上,“诗”由“言”与“寺”组成。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就此,王安石《字说》曾提及,“诗字,从言从寺。诗者,法度之言也。”这一判断透显出关于诗的一种新颖观点。《左传》讲“诗以言志”,《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关于诗的传统看法。此看法并未从形式方面界定诗。也就是说,在关于诗的传统理解中,心志外化为声言即成诗,而这一外化过程起初并没有格律之类的严格要求。从法度、格律视角把握和界定诗,是唐宋之后的看法和做法。这时中国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苏轼说,“敢将诗律斗深严”;黄庭坚说,“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姜夔也说,“守法度曰诗”。这些话语连同王安石的新观点,显现出诗在宋代的成熟和繁荣。伴随诗律成熟的是中国诗的文明的到来。诗律与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也表现在形式法律与现代文明之间。近代法从宗教和伦理中摆脱出来后,日渐成为现代文明据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诗律、法律特别是自然法或道德律,在根本上是“道”的显现,诗、律与道之间的深层联系在现代值得深入开掘。
一、格律变革与诗的文明
从“诗以言志”到“法度之言”,是诗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条发展脉络。这一发展经历了很长时期,中间也不断出现新的变革和突破。从历史看,《诗经》多为四言,到汉代“立乐府”“采歌谣”,杂言和五言乐府诗实现了对四言的变革。五言成为汉乐府诗的新时尚。特别是“古诗十九首”,看上去为五言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创作开了风气,立了基础。钟嵘在《诗品》中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从《诗经》四言跨到乐府五言,是中国诗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五言成为格律的字数基础。从后来的格律发展实际看,韵为最后一个单字,韵前每句以两个字为单位在声调上两两相错。五言为这样一种奇偶发展造就了条件。诗的格律最终在五言基础上形成,而后随顺扩展到七言。
就《诗经》和乐府的产生而言,中国诗有其民间来源。然而,诗在中国的发展远未停滞于这一层面。从风雅颂到汉乐府,都可见王庭的影子。王安石以“法度之言”界定诗,明显觉察到“诗”与“寺”之间的紧要联系。寺,是与帝宫或官府相关的场所或机构。这成为诗的格律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从汉到唐,是诗的格律的变革、尝试和定型时期,历经几近千年。在这期间,时常可见帝王与文臣之间的诗人群体和宫宴诗会。先有“汉武宴柏梁台赋诗”,由此形成句句押韵的“柏梁体”。而后又有曹魏父子三人、萧梁父子四人雅好诗文,并且在其周围聚集而成诸如“建安七子”的文人群体。再往后,隋炀帝登基前的晋王府、唐太宗登基前的文学馆,也都可见王族与文臣之间经常的诗会。在武则天时代,帝王身边同样围绕着专门研究格律规则的诗人群体。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都有看上去经过精心打磨、接近格律诗的作品流传后世。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就几乎被判定为“七律之祖”。
将历史铺开来看,文人群体围绕在帝王身边酬对应和、研究讨论诗,是中国诗在格律形成过程中一个较为普遍而持续的现象。这是文学现象,也是政治现象。汉武、魏武、梁武、隋炀帝、唐太宗,在史上皆有武事和政功,其左近形成文人团体,看上去与“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古训相吻合。这些文人团体,对于政治人物起势前笼络人才,胜战后偃武修文,都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诗会也是君臣在军政之余以夜宴歌舞愉悦身心的方式。在这种兼具娱乐特点的活动中,诗并未改变作为声色文明组成部分的基调。以诗配歌、以诗合乐,由此怡悦人心,是声色场合的迫切需要。文字与乐曲、嗓音的配合协调,因而成为诗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迈上的历史台阶。此种倾向使得诗的发展一度出现“六朝锦色”和骈俪藻饰之风。只是,中国诗并未长久陷溺于此。出于政治上的更强驱动力以及文臣的刻意警醒,冷艳低迷风气很大程度上在隋唐都得以有节制地自觉避免。因此,对于君臣诗会现象,既有“亡国之主,每多才艺”“南朝才子都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的负面议论,也有“创业之君,兼擅才学”的正面评价。
帝王与文人齐聚、政治与声色兼备,看上去是诗的格律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复合历史结构。宫廷,可谓格律探索最集中的实验或试炼场所。尽管诗终究需要边塞、市井、山水等情境来扩充其内容,实际上也一直从民间、自然界汲取滋养,但知识和文化更加集中、浓厚和高端的宫廷,在诗的格律起初的发育阶段,无疑有如必需而重要的沃土。格律诗的幼苗是宫体诗、宫廷诗或应制诗。这也是宫廷诗人反复试验、斟酌、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当音乐和歌舞在夜宴酒会场合需要诗的配合来提升兴致,宫体诗就越来越通过格律与“诗经”“乐府”中的诗拉开距离。相比可在民间自发蔓延的乐曲和歌舞,诗特别是诗的格律形式对于知识和文化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于诗的格律的自觉探索看上去并不发生在民间,而是汇集于宫廷,特别是由君臣组成的诗人群体。诗人集团的目标并不因此就在于强化诗的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和教化功能,而首先在于诗对乐曲和嗓音的契合度、适配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心的欢愉度。诗的格律的前进方向是诗与音声的协调融洽,以此达到愉悦人心的美感和艺术效果。沿着声色管道,诗的格律得以不断变革、深化和突破。
在格律成为一种需要被提上历史日程后,特殊时期的一些特殊人物起到关键作用。总起来看,格律的形成史可按人物分出三个节点。一是齐梁时期的“周沈”。周指周颙,沈指沈约。二是武周时期的“沈宋”。沈指沈佺期,宋指宋之问。相比而言,“周沈”将声韵平仄引入诗,具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创造性和革命性;“沈宋”则在声韵对偶基础上进一步疏导贯通,精益求精,持续调和出数量更多的完整格律诗,终使诗的格律基本定型。“唐以诗取士”,声律开始进入科举,诗的格律亟待明确定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潮头,又有初唐近百年宫廷诗的铺垫,沈宋吸纳利用前人经验,使诗的格律的千年形成发展史趋于终局,有效满足了历史需求。三是盛唐时期的“李杜”。李指李白,杜指杜甫。诗到李杜,可谓如日中天。律到杜甫,也已炉火纯青。尽管诗的格律到“沈宋”已基本形成,但其最终完成时态应归于杜甫及其律诗。杜诗,在传统与新体、宫廷与民间、形式与内容之间实现新的结合。从“晚节渐于诗律细”看,杜甫到晚年达致诗的格律与内容的完美融合。
杜甫的律诗成为格律运用的典范,杜甫也成为中国诗的集大成者。对古今、官民、形质的突破、跨越和统合,呈现的是诗的格律的普遍化。格律诗自此不限于宫廷,也不限于当下,而是与简单格律技巧相融合,成为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形态。无论何人,只要掌握格律小技巧,即可作诗。在人与诗之间增设格律,起初有搭配宫宴场合的曲和歌使之更加协调动听的原始冲动,也有科举考试的形式理性需求,但到诗走出宫廷和科举,突破人群差别、时空范围而被普遍化的历史时刻,格律更像与天工媲美的人为技巧。这就好比,以前不懂物种栽培技术,人生存只靠天收,多收多食,无收忍饥;学会渔粮培养技能后,人可顺应天时,自产自收,因此不再受到具有偶然性的天然年成的绝对限制。这意味着物质生产力、人为把控度和结果确定性的提升。随之到来的是农林牧渔作物的高产丰收和旱涝保收。人类由此也进阶到丰衣足食的新的文明形态。事实上,紧接着格律的最终形成而到来的也确是诗的文明。据说,唐代诗近五万首,诗人二千多;到宋代,诗的数量超过二十五万首,诗人更是超过十万。宋朝在诗及诗人的数量上远超唐朝,在规模上更是将以往的“风”“骚”“乐府”甩在后面。在很大程度上,诗的高速海量生产与格律的最终形成有关。格律形成是中国诗的一场革命。如同农业技术革命促成农业文明、工业技术革命促成工业文明,诗的格律促成了唐、宋乃至元、明、清的诗的文明。
二、形式法律与现代文明
从历史看,诗的格律与诗的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看上去也发生在形式法律与现代文明之间。“世界有物质文明,但不是文明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着文明”,这是英国法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到的一个涉及法律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命题。梅因注意到,古代法为宗教或道德理论所笼罩,“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由此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构成阻碍。古代社会也因此成为“静止的社会”。到近现代,这种状况出现扭转,法律从宗教和道德理论中摆脱出来。梅因说,“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情”。当法律与道德、宗教分开,不再受宗教或礼教的束缚,社会就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而迅速变动和发展,成为“进步的社会”。梅因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25页)。
在梅因的分析中,现代法因为摆脱道德和宗教理论的束缚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得法律与社会变动大致同频,现代社会由此获得持续、平稳、规范、有序的发展。现代法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看上去同格律与诗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很相似。与道德、宗教分离后,现代法成为促进现代文明生成和发展的必要且重要的形式,而不再是文明的限制和障碍。格律,一度也被认为限制人的思维,影响诗的自然生产。而实际上,格律促成了诗的文明。在格律与诗之间,有着与现代法与现代社会之间相同的关系分析结构。格律,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受道德或宗教理论的束缚,广泛适用于大千世界的万有现象。而且,这种适用并非是僵死和机械的。格律,既有不得违反的基本平仄要求,也有灵活的“拗”的技巧。在“二四六工整”之外,通常的“一三五不论”实际为诗人留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或机动空间。此种机动性或灵活性,无异于人的思维与物象情境之间的润滑剂,使得二者得以融洽调和,甚至因此达到巧夺天工的审美效果。作为形式和技巧的格律,促成诗的文明;作为形式和技术的现代法,促成现代社会文明,这两者极为近似。同样,从格律限制诗转向格律促成诗的文明,从法律限制文明转向现代法促进现代文明,这两者也极为近似。
格律的形成是一场革命,现代法从宗教和道德理论脱离出来也是一场革命。这两场相似的革命所形成的局面也是相似的。诗在唐宋后通过格律得以界定,有别于传统古体诗的近体诗都是格律诗。法律在现代作为普遍的形式贯通社会,从法律角度看,现代社会体系也是一个法律体系或法治体系。在理论上,这种法律的现代运动也的确被视为一场革命。美国法史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将西方法治传统的源起在时间上推至11至12世纪。在这个时间段,欧洲“教皇革命”最终导致政教分离,一个脱离宗教体系的独立的世俗立法体系、司法体系、法律知识体系得以形成(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英文版,第86页)。如同格律形成与诗的文明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独立自治的法律体系,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有效规范形式。也如同格律的形成经历几近千年的探索实践,这样一个独立法律体系特别是其法律知识体系,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积累。从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铜表法》,到公元3至6世纪的罗马法学家群体、罗马法学和法典编纂,特别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再到12世纪的罗马法复兴和“法律世纪”,就像古中国的帝王、书生诗人群体对格律的探索那样,在意大利半岛持续可见专门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法律最终从这个半岛走向全球。
现代法是适合在全球普遍扩展的法。这与法律的现代性密切相关。在梅因的分析中,为宗教或道德理论所笼罩的古代法限制着文明。古代法因此也显出较重的伦理、刑杀和惩罚色彩。而现代法得以促进现代文明,在于现代法摆脱了宗教和礼教的束缚,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纯粹形式。格律也是这样一种纯粹形式。格律并不设置伦理或宗教要求。道德说教和教义推广不在格律的规范范围。将道德说教内容堆砌或硬塞于诗中,通常有损诗的美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论语》中孔子所讲的这句话,可看到一个供人游弋栖息的纯粹艺术领域。格律和诗正处于这个领域。格律的目标不在宗教和伦理,而在通过语词声调的起伏错落达成声韵之美,以此怡悦人心,陶冶性情。格律依循的是艺术渠道。因为没有宗教、伦理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格律这种形式得以顺畅地适用于万事万物,由此将诗的内容扩及世间所有。
循着声韵渠道,格律使得物事和情愫以美的形式进入诗,如此成就诗的文明。与格律近似,现代法依循的渠道也不是宗教教义或礼教伦理,而是人权和权利。权利蕴涵人道内容,但权利与伦理并非完全一致。实际上,诸如人权、女权、私权、公民权利的现代崛兴,在价值和政治层面无异于针对宗教和道德伦理的革命。宗教和道德伦理涉及内在和外在的心灵约束和强行控制。权利则通常涉及人外在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和侵害。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到的“无害他人”,既是自由原则,也是权利原则(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10页)。这一原则成为现代法律和法治体系的基础。与宗教和道德伦理不同,权利原则并不涉及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以致在现代社会有所谓“做错事的权利”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权利原则完全丧失道德价值内容。只不过,诸如“成圣成贤”“慈悲利他”“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之类的内容在现代交由个人自主选择,而不是通过法律予以强制推行。强制一个人道德高尚或信仰教义,并非现代法的目标所在。现代法以平等保护人权为价值导向,以在社会交往和交易中“无害他人”为基本原则。因为脱离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这一原则得以普遍流行,平等适用于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总体看,现代法治体系并非要立足宗教或伦理而在人心内外强行构建起道德城堡或宗教殿堂,而只是像现代城市那样,构建起诸如地铁、楼群、公路等公用设施。这些中立客观的现代建筑设施,供所有公民和社会成员穿梭其间,自由生存、理性交往和安全交易。如果说,传统社会为宗教或伦理所渗透和掌控的法律限制了社会文明向外的扩展,那么,到现代,全球社会的法律治理,或者,在全球普遍扩展和通行的法治体系则越来越成为可能。遵循客观中立路径,现代法治体系成就的是权利体系和政治文明,一如价值中立的格律成就诗的繁荣和声色文明。
三、诗、律与道的再衔接
格律与其说是偶然而任意的人为制造,不如说是对天地之道、造化之秘的发现,有着深厚的学理根基。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沈约就格律指出,“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这表现出格律形成的学理深度、历史高度和研究难度。古人论诗,未必都将其视作“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而是带着“道”的眼光。“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系辞》关于道的两句经典的话。从格律的具体规则看,这两句话贯穿于格律的生成过程。文字基于四声而分出平仄,是格律的起始基础,也是阴阳哲学的典型体现。格律看上去反复运用了阴阳哲学。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每句末字既非全部仄声,也非全部平声,而是仄平交错。具体而言,除第一句末字可平可仄外,其他每联上下两句末字都是仄起平收。其二,每句除韵脚外的其他字按两字分组,每组末字平仄,如马的前后蹄一样轮替。其三,每联相同位置的每组末字,如同阴阳背反一样相对。其四,对仗凸显阴阳对称。此外,孤平也可谓阴阳哲学的集中反映。一个句子,如果没有两个相连的平声,音声要么遭受憋堵,要么短促,由此容易导致气的中断。就此而言,孤平带着气促、气断、独眼、瞎眼之类的弊病,连平则有如诗句的龙睛凤目。格律中的孤平,就像现代交通规则中的闯红灯,是常识也是红线和铁律,看似受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阴阳哲学的指引下,格律使得诗句气韵流动而连贯,犹如马蹄前后接换,持续奔腾向前。
从道的角度审视,格律的形成蕴涵两个基本维度。一是虚无之道,二是客观规律。如同《中庸》所言“道不可须臾离”、《系辞》所言“百姓日用而不知”一样,这两个方面客观存在,只待人发现。沈约说,“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就此而言,格律与久远的乐理相通,透显出中国文化的体用原理。征诸史实,在格律形成的近千年间,这一体用原理看上去是明确的。这是佛学传入中土的时期,也是儒、道不断成长的时期。在此时期,虽然也有各种议论,但总体上,儒释道被认为是同源的,三家在体用原理上达成一致,孔子与老子、佛陀都同样作为觉悟道体的圣人看待。这构成格律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从个人层面看,永明文人集团大多涉足佛道,其时文学与义学或玄学呈并举态势;而对格律形成起重要影响作用的诸如“周沈”“徐庾”“沈宋”等人,对佛道都有相当研究。纵观历史,萧梁、隋、唐,在文人集团、图书收藏、格律探索、尊崇佛道乃至国家律典上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佛学东传,特别是其中的音声念诵,也被认为直接影响了格律的形成。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指出,“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这些都显现出诗律与道的相通。
尽管格律看上去与道有很深的渊源,也促进了诗的文明,但如同现代文明与远古之道之间看似日渐淡薄的联系那样,诗的文明形成后,诗人通常沉浸在诗的境界里,很少再将诗与道联系起来,去思考诗或探究道。在诗走向文明兴盛后,诗人大多流连于诗境的情愫光影,以此因应人世忧喜苦乐,但似乎终究缺少道的透脱。格律融道入诗是开端,但因诗入道看上去并不是结局。在与道德的关系上,现代法律与格律看似有相同处境。以道看格律诗,可见三重结构,一是诗,二是格律,三是道或本体。由于现代人大多不了解格律知识,对道或本体更是不知,格律诗在现代通常处于被作为文字或文章读的境地。进入格律诗,人只需掌握格律小知识。格律在现代仍然可学,而且人一定可以学会。掌握格律后,人即可自如写作格律诗,也能像打开窗户、透进光亮一样,更能充分欣赏领会格律诗。而对于道或本体,人纵有志愿和勤奋,穷其一生也未必能知,但这终究是一个方向。以道看现代法,同样可见三重结构,一是实在法,二是自然法,三是道或本体(拙著《亚洲世纪:法理的文化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前言、第二章)。其中,实在法就是国家通过文字发布的法令,有形可见,而自然法和道德本体,则无形不可见。所以,到英国法理学家奥斯丁那里,自然法因为不可见而被剔出法理学。如同不懂格律的现代人只看格律诗的文字,而看不见其中隐含的格律和道那样,现代法理学也只把实在法作为研究对象。奥斯丁所划的现代法理学范围,不包括自然法,更不见道德本体。然而,从历史看,自然法和道德本体或哲学本体虽然不可触摸,却是自古以来几千年一直被思考和探讨的对象。
在现代,格律更像文化遗产,实际沦落失语境地。道德本体乃至自然法更是鲜为人知,从现代知识和学术体系滑落乃至被驱逐出去。现代因此未再出现格律诗的文明,也面临着重启道体、在现代体系与道德本体之间重新达成衔接融合的基本问题。从法理看,承接中国文化的体用论,在现代实现诗、格律与道的衔接,将自然权利、形式法体系与自然法、道德本体重新融为一体,是既具可能也显必要的发展方向。《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是关于法律的简单观念,也无妨作为现代法的质朴取向。在脱离宗教教义和伦理说教、形式上平之如水的法治体系下,任由格律,也任由自然法、道德律、道德本体在现代社会经个体自主选择而重焕生机,这许是值得期待的现代文明景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