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作为人类社会的隐喻由来已久,从伊索寓言里的勤劳个体象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公民,到赫胥黎的未来人类社会形态比拟,再到当代科幻电影中的超级有机体文明……蚂蚁的形象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因循着历史、文化、政治和技术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寓意,但无论语境如何变化,蚂蚁都像一面奇特镜子——人们总能从中观照出极为贴合自身的影像,仿佛不是“蚂蚁像人”而是“人就是蚂蚁”。
《蚂蚁社会》一书通过对蚂蚁文化史、认识史的梳理,结合大量蚂蚁主题文本与影视作品的分析批评,揭示“蚁群—人类社会”这一绝对隐喻的成因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启示。因而在这部指涉甚广、意涵复杂的作品里,仍能看见两条清晰的叙事脉络:一是蚂蚁作为文化符号的社会史;二是蚂蚁所代表的昆虫学—社会学发展史。
书中对各类蚂蚁文本与影视作品的解读非常精彩,作者丹尼斯·韦贝尔将寓言故事、文本、电影、动漫等视作蚂蚁文化传播的载体——即传播的媒介手段,藉着研究以上媒介对蚂蚁描述与定位背后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及技术支持,显影蚂蚁文化形象生成的内在逻辑与流变历程,体现了一种媒介技术决定论的新文化史学观。在近代型塑蚂蚁文化的诸多媒介技术中,社会生物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此学科的发展史亦贯穿书中所有的书影评,尽管韦贝尔称之为昆虫学—社会学,但其理论仍建立在社会生物学的框架内。
社会生物学由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于1975年创建。威尔逊也是韦贝尔重点评论的科幻作品《蚁丘》的作者。威尔逊将社会生物学定义为“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系统研究”,将群体生物学、动物行为学和进化论等学科结合起来,解释社会性动物的行为与社会结构。人也是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如蚂蚁等有着相似的行为和结构,例如:利他主义、劳动分工、族群选择、交换经济、公共设施建设等等,社会生物学从进化论与基因遗传学说出发系统地阐释了这些行为的生发机制和原理,为“蚁群—人类社会”这一隐喻提供了客观有力的科学支持。
随着科学界对蚂蚁认识的加深,人类越发从中获得对自身的启迪与反思:蚂蚁的交哺行为与人类的交换经济相似;蚁群的分工与分配机制对市场经济、社会资源调配乃至计算机算法的建模有借鉴意义;蚂蚁的团体协作能从进化和博弈论的层面阐明——“合作具有进化优势,没有合作就不会存在生命的复杂性与建设性”……蚂蚁带来的种种启示都指向了群体意识(智慧)的重要性,它们的群体意识高度统一并行动起来时所展示的“1+1>2”的“超有机体”形态,人类很容易就从中照见“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自我描述形象。蚂蚁对人类社会的隐喻就演变为两者都是“超级合作者”,“谁理解了从蚂蚁到超有机体的进化,谁就能够理解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重要性以及一个社会如何可持续地运转”。威尔逊的《蚁丘》正是从此出发,将科学与文学,虚构与现实的话语进行拼接、互文、延拓,“把对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描绘与对蚂蚁作为社会性昆虫的观察联系到了一起。这两种情况都假定社会系统在一个生态位中发展。环境中外在与自身产生的变化使得系统面对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挑战”。
韦贝尔浓墨重彩地解读《蚁丘》,不仅因威尔逊是蚂蚁专家和社会生物学之父,也在于他一直致力追求“知识的大一统”,即以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来认识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本质,而这点同样是韦贝尔书写的主旨内核。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妨参照威尔逊的另一部著作《知识大融通》,书中阐述了生物学与社会学、文哲、美学、宗教与道德的互涵关系,借助各学科间的连接点寻找知识底层的同一性;而韦贝尔则是逆向从政治、文哲、电影艺术等范畴来描述以蚂蚁为隐喻的社会生物学,目的同样是为了映摄各学科间的联动关系,欲构建一种以生命科学为统摄的多学科和研究方法融合的认识论和世界观。由此看来,韦贝尔的《蚂蚁社会》犹如是威尔逊《蚁丘》和《知识大融通》的一篇精彩互文,并且《蚂蚁社会》的名字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否在向威尔逊与霍尔多布勒合著的《蚂蚁的社会》致敬?
不过,亦如威尔逊当年引发的巨大争议一样,韦贝尔过分强调科技、效率与进化的作用,力图通过生物学来解释人性包括伦理道德与法律,按昆虫社会模型来设计人类社会的秩序,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迷恋目光将蚂蚁社会推至“国家完美模型”的地位。在这种唯技术与生存至上的功能主义视野下,他的言论时常表达出:崇拜群体、贬低个体,迷信工具、轻视心灵,注重同一而否定多样性的偏狭态度。而偏狭必然导致误解,譬如他赞美蚂蚁社会的诸多优点,却没有回答:为何此“完美模型”在如此漫长时间内也没有诞生出文明? 人类为何要学习一个没有文明的社会?
而且,过度迷信蚂蚁式的高度一致性难免会滑向极权思想,就像他在解读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时说:“《美丽新世界》当然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对于每个读者都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从接下来的论述中,可看出他本人就希冀着这样的乌托邦社会存在并沉迷当中的生物极权政治情景。此外,韦贝尔也大段引用施米特与埃舍里希的社会构想来论证自己的昆虫社会优越性,而后两者都是德国纳粹学者,主张种族主义与反人道主义。这当中流露出的价值观倾向在现代文明和民主社会语境下难免令人感觉不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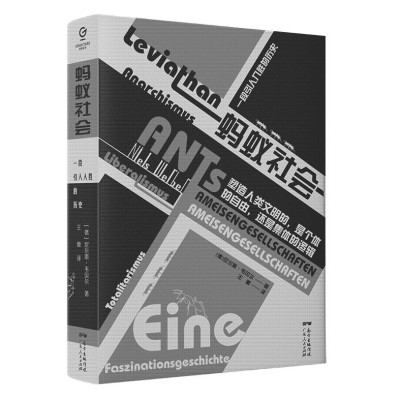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