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舒晋瑜
他好像一直在路上。
几次联系采访,要么是在会议的间隙,要么在去机场的途中,张培忠的身影总是匆忙,即使周末也无例外。
这让我想起他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永远在路上》。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感人肺腑,读之潸然泪流。对父亲的深情是触发他创作的冲动,贯穿了全文的情感基调。父亲对他的品格影响则奠定了他全部创作的底色。“在路上”,既是他的创作状态,也是他带领广东文学队伍奋力前行的状态。每天都要应对繁忙的公务,但他更善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于创作,《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获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海权战略》《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百万字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总撰稿……一部部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厚重之作,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为了完成《文妖与先知》,张培忠十年间没休过周末,五年没歇过春节。在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他实地考察张竞生当年活动的遗迹,以评论家的理性睿智、精微辨析,辅以小说家的细腻文笔,从忠实于历史的立场出发,不仅成就了个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奇”,也树立了广东传记文学的又一优秀范本。
之后关于郑成功与张九龄的传记创作,也体现了张培忠善于敏锐地选择传主的智慧和勇于探索被遮蔽的学术富矿的魄力。他的“业余爱好”颇有成就,同时也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文学粤军”。2021年8月,张培忠带队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作为中国作家馆的主宾省,广东主宾省活动展出广东作家创作的精品图书123部,其中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图书103部,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出版的图书56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评价,文学粤军作为中国文学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坚韧、执着、对文学充满激情,这是张培忠给我的印象。他总善于敏锐地发现独特的题材,并以定力在这独特中挖出一口深井;他在不断重写历史,在重写中总有新的发现,又于发现中展开超拔的丰富想象。笔触所及,折射着他背后潮汕大地“海纳百川”“爱拼才会赢”“永不服输”的精神底色以及对那一方热土的文化底蕴的长期研究和积淀,折射着广东作协带头人身上朴素而勇于开拓的坚定意志。
2021年11月,中华读书报专访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之路比较顺畅? 创作的各种体裁不但发表,且都能获得奖项,能否总结一下经验?
张培忠:经验谈不上。刚刚起步时,老师的鼓励颇重要。初中时语文老师推荐我读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为我早期的作文打上了散文诗的底色。在家乡读师范时,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小说创作;1987年在《汕头日报》发表处女作《春天的思索》《告别》,还和几个喜欢写作的同学创办了星光文学社,主编《绿茵》杂志。在大学中文系本科读书时,有意识地进行多方面的训练和多文体的尝试,参加了中国作协鲁院小说高级班的创作函授,报告文学《畲族凤凰出深山》获学院举办的1988年暑假社会调查征文竞赛第一名,三万多字的论文《雷铎小说论》获中文系优秀科研成果奖并在一所大学学报的头条发表,文学评论《怪才写怪事》在当时蒋子龙老师担任主编的《天津文学》发表,中篇小说《高考补习生》被《作品》杂志留用。
大学毕业后我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工作,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秦牧先生,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去拜访他,他亲切地称我们是“先后同事”。他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家,也是厌弃空谈的实践家,对我们刊物举办的活动几乎有求必应。他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他曾经对我说,自己的一生做过两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是当教师,一是当编辑。这两项工作都马虎不得,不懂装懂或似懂非懂都无法混过去。当教师,讲错了课就下不来台;当编辑,白纸黑色,一出差错,第二天准会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来指责。正因为这样,我养成了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受益终生。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在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也一直没有中断创作。对于您来说,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张培忠:写作的确是艰辛又寂寞的过程,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时间和空间极其有限,都是挤时间创作,长年累月,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既锻炼文字,也是积累素材,截至目前已有五百多万字的日记。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散文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经世致用,而把吟诗作文视为可有可无,似乎为文者足戒。但是,环境再困难,我也不愿放弃,可见创作于我是精神的、心灵的需要。不为稻粱谋,不存功利心,或许可以成为创作的一种境界;而面对纷繁的世界,重申一种新的写作态度,或许并非完全没有必要。首先,要有超越的眼光;其次,要有坚守的品格;再次,要有现实的关怀。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了人物传记和理论批评的方向?
张培忠:我在读大学时对小说最感兴趣,有很大的热情创作。后来编杂志,主要从事非虚构创作。我有位评论家朋友周政保先生,曾专门写信给我,激励我下功夫搞文学评论。他说要么写小说,要么写报告文学,要么写评论,把一件事搞透就能有所成就,不能贪多求快。放弃虚构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较真,事情不做则已,做就要尽量做到最好。写张竞生传记从确定题目、收集资料到创作,做下来二三十年,四十万字的文学传记,又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8套播出,并整理编辑十卷本《张竞生集》在三联书店出版。如此穷尽可能,别人再做这个项目的研究,可能都要从我所做的基础材料入手。
中华读书报:您曾说过计划写人物传记“三部曲”,现在进展如何?
张培忠:我的业余写作计划是人物传记“三部曲”或者叫创作“英雄三传”:文人、武人、官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时任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和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的支持和帮助。陈春声教授非常重视张竞生这个课题,将我的张竞生研究纳入其主持的“潮州文化的特质与内涵”合作项目,两次亲自到中大图书馆特藏室为我办理阅览证,到台湾讲学时也不忘复印资料带给我,他对于我用学术跟文学相结合的方式处理这样的题材很认同,认为只要我依样处理郑成功题材,这个人物一定能立起来。陈教授说,郑成功不仅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海权史上的重要人物,本身的故事相当精彩,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7岁从日本返回中国泉州,之后掀开了中国海洋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我首先找来郑成功的家谱,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看来了兴趣:郑成功的曾祖母谭氏是潮州澄海人。这说明郑成功有潮汕人的血统。我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又萌发了“挖掘史实烛照现实”的愿望。这部作品还在进展中。张九龄的创作则还在计划中。这三个人都跟广东有关。我认为挖掘本土资源,还是要立足根据地,熟悉笔下的人物才能有感情,才能出彩。
中华读书报:创作张竞生的传记,纠正了读者对张竞生的哪些认识?
张培忠:长期以来,学界对张竞生的偏见和误解是很严重的。我曾经用六个定论来概括张竞生:出色的哲学家、重要的美学家、启蒙的性学家、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最后总括为有情怀的革命者、学问家、实践家。他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是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社会实践家,这才是张竞生的本来面目,历史应该还他本来公道,性学只是他的十个手指头中的一个小指头,不能以偏概全。
在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哪怕是亲临,仍感受到许多的遗憾和缺憾。如一些老报纸虽有存世,但由于保存不善,无法翻阅。中山大学珍藏馆的《群声报》,就仅能翻看一小部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上海夜报》由于损毁严重无法查阅。尤让人痛惜的是潮汕地区的老报纸、老杂志,百不存一,其中的《大光报》有关张竞生作品连载部分也残缺不全。张竞生因《性史》一书备受争议,其著作被禁毁现象十分严重,也为资料的搜集带来了障碍。
中华读书报:选择张竞生是必然?张培忠:张竞生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景,串起一部不一样的现代史,他是中国现代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题材,却多年来无人挖掘,无人触碰。写张竞生,不仅是写史和事,也写学和理,更是写人和心,为读者呈现一个有血有肉是先知但也有缺陷的立体的人。所以,将张竞生称为“先知”,的确是因为他有一系列超前的理念。我之所以要写张竞生,就是因为他不仅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更重要的还有现实价值。
中华读书报:您选择的传主,都有现实意义。您在选材上是怎么考虑的?
张培忠:为一个人物立传,不是为写而写,不是搜罗奇闻异事满足人猎奇逐艳的兴趣。写历史,往往是为现实服务。历史人物非常多,作家怎么选择,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所选择的题材一定要跟现实构成强大张力,对现实能起到深刻的启示意义,同时写作对象本身要蕴藏非常丰富的时代内容,这样的题材才会进入我的视野。这三位传主都有潜在价值。我的原则是,不为历史而历史,选题要和现实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我不动笔。
张竞生提出以美的理念来治理社会,提倡美治主义,奉行美治精神,实施美治政策。在美学上,王国维、蔡元培是先驱,但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建构上,张竞生不仅提出一套理论,他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从实践的层面思考美育问题并身体力行。他在美学专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从衣食住行到婚姻家庭爱情方方面面都用美的理念来设计,并通过实践来体现、提升美的人生。他是一个启蒙的哲学家,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比马寅初整整提前了37年。关系到人的解放、人的觉醒之种种言论和实践,开历史先河,不但在当时显得惊世骇俗,引起轩然大波,放到现在,爱情、婚姻、家庭也是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他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张竞生在广东饶平,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创新举措,对于我们今天推行乡村振兴国策,以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很有现实借鉴意义。
我研究郑成功这个人物,首先是他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比如他的忠君爱国,敢于亮剑,比如他的“通洋裕国”的思想,实质上是最早的对外贸易与对外开放。郑成功的海商集团纵横东西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最鼎盛的时代。由海商转型为英雄,这里面有很大的表现空间供我辗转腾挪。近几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周边海域暗流汹涌危机四伏;我通过写郑成功,通过深入剖析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衰过程,借微观个案来反映宏观战略,这样视野更开阔,也更有现实意义,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弘扬郑成功精神”。
张九龄是江南第一宰相,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诗坛领袖,李白、杜甫都曾得到他的帮助;王维、孟浩然也得到过他的提携。一些名句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流传。这样德才兼备、识见卓越的千古名相太值得研究了。我同样是出于为现实服务之目的计划写张九龄,他识人、用人、选人的许多见解直到现在仍然很有借鉴意义。比如他在吏部当官,主持选官时,提出了“德才兼备,德望为先”的标准,跟我们现在的标准如出一辙。当然写张九龄的传记更困难,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资料更少,但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做着收集史料的工作。因为公务太繁忙,谋划和服务全省的创作才是我的主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预计这三部曲,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创作完成。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认为,您在张竞生及其相关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这其实也是写人物传记的共同特点吧?既让传主回到真实的人生经历,同时又要讲好“故事”,您在人物传记的创作中,如何把握非虚构的分寸?
张培忠:我严格按照史实,收集素材时一定要进行事实考证。我研究张竞生,会调查他在北京住哪条巷;为了写好郑成功,我专程到台湾的台南考察,两次到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户踏勘,对郑成功在广东、福建、浙江活动的地方,都利用节假日,前往现场做田野调查,获得真实感受;并从全球范围搜集郑成功的史料,托朋友从美国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大学查找郑成功史料,自费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研究生从日文中翻译郑成功史料,在史实收集方面下足了功夫。小的历史细节考证清楚才具有可信度。历史事实搞清楚后进行文学创作,我就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细节合理想象,使作品在事实可靠的前提下具有文学的可读性。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认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融合了文学性传记的生动性和学术性传记的严谨性,作者写了许多好看的故事,然而却又是言必有据,无一字无来历的”。李先生的评价当有褒扬和鼓励的成分,但他提到的“文学”与“史实”并重,“兼具文学的厚重、思想的深邃与艺术的美感”,则是我始终不渝努力追求的目标。
中华读书报:写人物传记,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张培忠:一定要写出传主的特质,要为文学画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我既不会一味赞美,更不会全盘否定,而是尽可能靠近他、感知他,还原他的真实面目。学术性与文学性高度融合是我处理此类题材总的思想。所谓“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受到很多限制,但在这种限制下我希望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独一无二的人物,以独特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的深刻性打动读者。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传记三部曲”还是《奋斗与辉煌》等方面,您的创作和主持的工作都是有系统有规模的,这种大格局的特点来自什么?
张培忠:我们本身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心怀“国之大者”,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力以赴做伟大时代的记录者、人民心声的表达者、文化强国的建设者,始终是我谋划广东创作和推进个人创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无论是创作“传记三部曲”,还是广东省作协的工作,一定不能辜负这个伟大时代。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这些都是重大的国家战略,蕴藏丰富的创作资源,敢于涉足这些大主题,敢于正面挑战这些大创作,触动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大作品、产生大共鸣。这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创作的需要。
当然创作难度很大,要求作家必须深刻把握、洞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和人心的复杂,要能把握住核心的东西。我特别赞赏苏轼的“犯其至难,图其至远”,也特别服膺雷巴科夫所说的,文学的义务就是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大时代需要我们的作家迎难而上,需要我们的作家有定力、有雄心、有能力去回答时代的难题、书写民族的辉煌。
中华读书报:作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您如何评价广东的作家队伍?
张培忠:广东的作家队伍势头很好,数量庞大,老中青相结合,特别是青年作家表现突出。我们提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服务三支队伍一起抓,锲而不舍打造“文学粤军”。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广东文学,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必能创作出更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精品力作,广东作家有这样的雄心和抱负。当然目前短板也很明显,名家和领军作家少,有影响的作品不多,二十多年没得茅盾文学奖了。
中华读书报:在组织广东作家创作方面,广东作协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下一步有何规划?
张培忠:广东作协重视顶层设计,全面谋划和积极推进全省的文学创作。一是组织重点作家到特区、乡村、企业挂职蹲点,通过重大资金扶持鼓励作家深扎创作。目前陆续有一些作品出版,我们对每位作家召开作品审读会,请名家给他们把脉,希望他们的创作有大的提高。二是组织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重点突破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召开乡村题材创作会,举办了两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还专门召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省选择了百名重点青年作家,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著名报刊主编当导师,以一带二的方式重点指导。其中十名重点青年作家每人给予十万元资金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整体提高作家创作水平。三是组织重点主题创作,比如《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我担任总撰稿。这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记录小康工程的鸿篇巨作、首部全面讲述广东小康建设辉煌成就的大型纪实文学。2020年广东作协组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创作扶持工作,实施“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造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代表作。建党百年,我们浓墨重彩地推出反映现实主义、红色题材和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希望重点作家能得到提高、青年作家得到磨炼。
文学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版块。几十年来我们广东没有自己的评论杂志,去年创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最近召开创刊一周年座谈会,多管齐下把杂志打造成为文学评论高地。接下来要花较大力气抓好我省的文学评论队伍建设,继续组织第二批签约评论家,安排一百万元资金,在全省征集并出版首批十部青年批评家丛书,继续出版“粤派批评”丛书,整合资源,壮大广东的评论家队伍力量,在全国发出广东评论家、粤港澳大湾区评论家的声音。
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广东文学事业发展,从政策出台、资金保障到工作指导,给予全方位的支持。除了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听党话、跟党走,组织打造精品力作,还在加快推进广东文学院改革、文学馆建设,以及影响基层作协“最后一公里”建设问题,全面推进广东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广东文学从高原到高峰,推动建设文学强省。目前是广东文学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促成伟大作品的诞生,也许当下还未能产生这样的作品,但是我们的一砖一瓦、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在起着铺路石的作用。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将来有那么一天,广东的作家,一定会创作出真正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对此,我深信不疑。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张培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第2版,定价:68.00元
《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张培忠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8月,定价:36.00元
《张竞生集》,张竞生著,张培忠、肖玉华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定价:980.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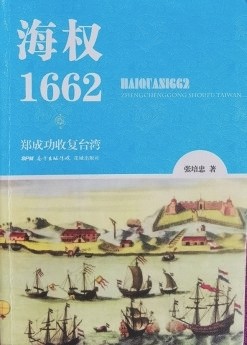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