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散文应该让人战栗、泪眼婆娑和重新发现,李琬的这册《山川面目》接近如此。她所引用的“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这句徐霞客的名言,我也是初次读到后就在心底默默记下。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我告诫自己不要去写散文,我也谨记十七世纪剧作家莫里哀《贵人迷》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汝尔丹跟哲学大师讨论后,发现自己这四十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中用散文说话”。
就像说诗就是分行一样,说散文就是“说话”,也是有道理的吗?布罗茨基说,伟大的散文必须被写成以其他方式存在的诗歌。一般人经常把精神的松弛状态等同于散文。诗歌与散文相对,就像艺术与生活相对。人们会说,在散文中,我们把若有若无的情绪表达出来,无异于那些伙夫、赶驴人、猪倌、店主的日常对话(可不就是莫里哀吗)。但这种“松弛”的散文,是每一个诗人从开始写作起就在清理的痼疾。不过,李琬的《山川面目》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我想是一种成长中的当代散文。它综合了诗人的语言敏感、人类学的细密观察和批评家的文体自觉。
散文对一个人的心理余裕有莫大的要求,古往今来的散文大家往往是不惮于把内面剖露在世人面前的人。新文学短短一百年出现过的一些优秀散文家,也多是性情冲淡平和、修为颇深的人物。在李琬引述的艾芜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习作”作家中,我想她也发现了这种特殊的描述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山川面目》中,第一辑“无穷的远方”,第二辑“无限的人们”,第三辑“文本中的世界”,都是被生活吸引、情动于衷而行之于文的作品。
就像在开卷《埃里温之瞬息》中,作者描绘在庭院中看到苹果树的段落,让人想起萨迪的《蔷薇园》。她写道:“曾经种满了花的院子里,长着两棵苹果树,树上结满苹果,枝条下垂,树下也落满苹果,来不及被人吃便掉落在地上,反射出带着灰土的紫红色暗淡光彩,在不太晴朗的黄昏空气里益发恬静。一个老人坐在店铺门口,抽着烟,店铺里空空荡荡,似乎没什么工作要做,但是他坚持每天都出来坐着。他向我们伸出手来,一双被生活、历史和遗忘折磨过的手,和这世界千千万万个小镇上的居民一样,是我们的叔叔伯伯。”这个开篇,传递了很多信息,也被后面的几篇所证实,那就是对中国内亚边地生存实态的书写、整理和经验的发掘,它以葱岭为中心,扩展到中亚,比如在亚美尼亚的旅行。在这些旅行中,作者一方面辨识着被“图经志籍”/个人“偏见”所蒙蔽的现实,一方面被自己的见闻感染,同时演化着自己的意识。
在李琬的这些文字中,必然与偶然的事物,超越性的与世俗的事物之间的次序发生了颠倒,权重发生了转移,偶然的东西是现实中那些最必然的。这里也有对待劳作的态度,我想是她走出学校之后接触“劳作”的实际感觉,对普通人工作中与汗水相称的“诚恳”有了新的体认。
她最好的作品通过到达普通人生活的实感而发现了生活的“幻觉”成分,最终抵达了非宗教领域的神圣。比如,“我们渐渐可以看见硕大密集的星群,每一颗竟然有无花果那么大。它们的光芒丝毫不亚于最明亮的钨丝,缓慢旋转,在冰冷的山风里欢愉地微颤。”(《寂静的夜晚,为何听不见》)这比喻,把“无花果”这个来自策兰诗歌的宗教性词汇放置在星群和钨丝之间,让人想到《第七封印》中骑士跟约瑟夫一家吃草莓的瞬间。在同一篇的结尾,作者把出神的时刻保持在某种密集情绪的笼罩下:“微弱的光在弹跳和扩大,从刚刚掐灭一支烟的卑微手指,到窗外浩瀚的银河尖峰。我醒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县城中心,永恒的阳光将要照耀塔什库尔干。新娘已经在路上,蒙着她年轻的面容。群山向我涌来,一阵战栗终于在内心停住。”这是深沉、令人难忘的抒情,从容、宁静,智识,不丢失任何感性,也不丧失教化带来的判断。旅程既是诗人的成长,也是对纷繁世界的采集。她就像原始时代的女性采集者。
在第二辑中,作者把自己的笔触收束到更加切近的人和事上,比如《夜幕》中经常光顾的电影院,《枣糕、灯光和烤鹌鹑蛋》中的北京小吃和与友人的郊游,《小劫六朝灰》《譬如朝露》中读、写、居、留的普通生活,《过城门》中的汉口——也是作者家乡的风物变迁史,《家宅》《晨昏·草木·大院岁月》则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留下丰富记忆的特殊场所——家。在第三辑,作为文学批评和读书随笔,李琬的文风稍微收敛庄重下来,不再有前两辑使人微醉的迷魅、摇曳,更多的是较为清晰的论述。其中,科辛斯基、乔丽·格雷厄姆、丹尼斯·莱维托夫的译介工作,她都参与其中。无论是科辛斯基的幽邃黑暗,格雷厄姆的广阔渺远,还是莱维托夫的微妙神秘,都与她所关注的“平行世界”的普通生活密切相关。
总之,在她的爱中,我发现了其散文的依据,某种“生活流”的细密画使我们接近永恒。读毕《山川面目》,我意识到某种错失,她在生活中发现的许多事物,我发现自己正好遗漏了。这种遗漏,不止针对我个人,因为她的发现,也不止针对某一个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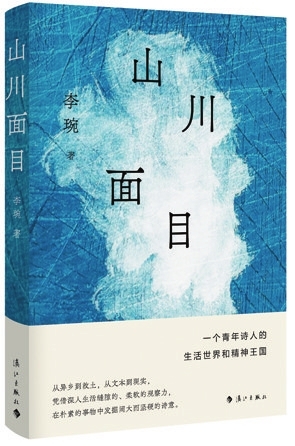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