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令人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因此,在我们策划“帝国时代”系列的时候,决定最先推出《大秦帝国》和《大汉帝国》。
关于这两段历史,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正史、野史、戏说、趣谈……都能说出个精彩纷呈来。然而,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讲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
历史到底想叫我们明白什么?或者说历史能让我们明白什么?
正史多想叫人晓古今而知兴废,野史则多想叫人明权谋而知进退。
《大秦帝国》《大汉帝国》洋洋洒洒百十万字,想叫我们明白的,无非是“人”和“人性”。说“明白”其实还不够贴切,应该说想叫我们“看到”,所有文字只在呈现而已。然而,这种“呈现”自有其妙处。某种程度上它如《史记》,笔触贴近人物。不同的是,“太史公曰”已将个人观点贴于古人显著之处。而我们这两本书则多采用“曲笔”,“含蓄多情”,对于人物,不置臧否,一如《红楼梦》。
在《俏丫鬟抱屈夭风流》一回,晴雯的毁谤致死,袭人最有嫌疑;甚至黛玉之死也与袭人有关。少时初读《红楼梦》,总疑惑作者为何始终不说清楚这些情节,甚至想借宝玉之口奚落袭人一句,都话到口边又咽下。是作者对笔下的黛玉爱得不够深?是告密者另有其人?都不是。待时移世易,自己经历得多了,才懂得作者的胸怀。人间事,是非善恶不难判断,难的是知其“恶”,也念其“善”,乃不能不理解、不能不感怀,乃不能不爱,故而不忍说破。作者爱晴雯,爱黛玉,但是也爱袭人。这爱,不是两性间的吸引,是生而为人,彼此之间应有的惺惺相惜。在《大秦帝国》《大汉帝国》中,鲜见断然结论,而更多的是这样婉曲的笔调,它不极力说明什么,也不极力批判什么,只是再现帝国崛起中的形形色色。
当帝国的车轮滚滚而来,操纵者并不能完全操控,被裹挟者则身不由己,被碾压者只能听天由命。个体生命在其中皆如蝼蚁。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平民,也包括帝国的开创者和设计者,包括帝王将相风云诸侯。当我们放下宏大的命题,诸如“帝国”,诸如“兴亡”,我们也许就能看到这一个个“小我”的脸上生动的表情,这才是帝国最本真的表情。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而明白的前提是理解。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的一去不返而显得弥足珍贵。
钱穆先生说,我们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是两部充满了温情和敬意的作品,这份温情与敬意不仅仅给予我们以往或辉煌或暗淡的历史,更给予我们历史中的每一个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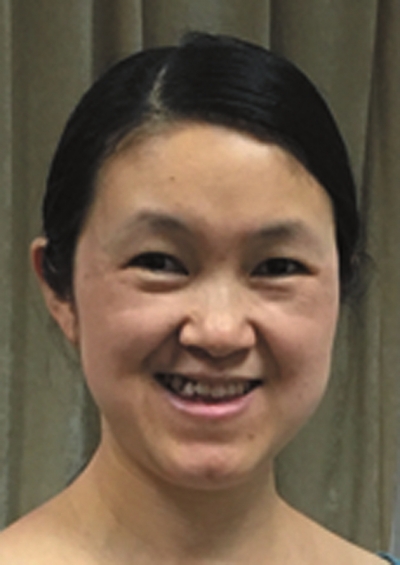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