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有一著名的论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源自于古希腊的一则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C·赖特·米尔斯(1916-1962)应该就是伯林意义上的“狐狸”,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与知识分子,他不拘小节,对于社会学挥洒自如,影响力远远溢出了社会学界,尽管已经去世五十多年,但他所倡导的社会议题与学术路径依然有其价值。
1997年,有人组织过一次对各国社会学家的调查,试图了解哪些著作对20世纪的社会学家影响最大,《社会学的想象力》位列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
《社会学的想象力》基于所论述的议题,更是有长久的魅力,社会学界对之颇为推崇。作为贯穿此书若隐若现的引线,“知识分子”的参与感与博雅诉求可以为读者理解此书提供潜在的思想背景。
米尔斯认为,优秀的思想家对于日常生活有丰富的感知能力,他们的研究工作并非与日常漠不相关,而是息息相关,进而使得两者相得益彰。他要求自己的后辈能够“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并且在你可能从事的每一项学术成果中纳入你的个人体验”。
具体而微,他主张建立完整的学术档案,用于缓解重复工作的乏味,使得研究者免受劳心费神之苦,更重要的是,说不定还可以激发研究者去捕捉边缘思想
针对当时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他试图嵌入历史学的视角,以便深入理解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对于社会心态做更加生动的追踪。个中洋溢着浓厚的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色彩,为其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提出做了细密的铺垫。
米尔斯对人类的潜质抱有很高的期待,同时又担心“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自甘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愉悦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人性的广度与深度恰恰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限度,这其中风景无限。
为此,他觉得注意力与思考力远远不够,学者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既可以促进理性思考,更能使得他们洞察世事,进而对周围的全貌有清晰的了解,这种品质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学者,对于记者、艺术家与其他专业人士也会很有助益。
早年米尔斯以为,“那些有能力和脑子洞悉机构缺陷的人,那些很敏感不能屈就错误命令的人,那些适应后就能屈能伸的人,那些有想像和智慧去形成自己准则的人,那些有勇气和毅力不顾社会压力和孤独过自己生活的人”,才是社会的瑰宝,才算知识界的中坚。无疑,他所欣赏的是知识分子的品格,这与能贡献出色当行的研究密不可分。
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偶遇的故事。某一天,艾森豪威尔慕名而来,不动声色地坐到米尔斯讲课的教室最后一排,米尔斯马上更换题目,开始说怎么用阶级斗争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越说越起劲,总统越来越不安,最后面红耳赤地匆匆离去。
刻意与权势保持距离,其实也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他呼吁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深信这给人文社会科学的启发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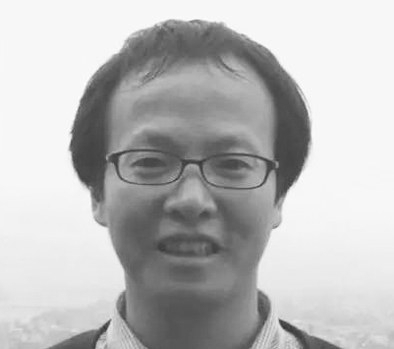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