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实实在在地踏在土地上而作出的沉思录,也是一个青年学者在参与社会实践后提交的一份优秀答卷。
《去北川》是作者刘大先去北川挂职工作一年多后写就的一本书。书中明显留下他的挂职履痕,也勾勒出北川山水的清新样貌。但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记录挂职的经历和见闻,而是作者对与基层亲密接触后的思考。而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在思考时所采取的角度。
一
刘大先的思考角度是从决定去挂职起就确定的。但他设定的第一目标不只是熟悉社会、了解现实,而是要“将自己投入进去,改换一下角色,融入其中,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补充,完全没有置身事外”。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书中,他用了“涵化”“同化”“融合”“混融”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也使他大有收获,成为“一次提升与塑造”,并强调自己“只是想沉潜进北川生活中涵泳,体味苦乐参半和悲欣交集”。刘大先真正把自己当作了一名北川人。工作时,他是北川的副县长,勤勉认真、兢兢业业;下班后,他又像一名普通的北川人,穿行在县城的街巷里,感受浓浓的烟火气。他很自得,所以在书中说:“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以北川人自居了,想到那一片土地的厚重与轻盈、艰辛与欢欣,我的心情也会不由得随之起伏。”
将自己作为一名北川人,才能真正融入北川的生活,懂得北川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真正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书中记录着他的成长提升和思想变化,比如,刘大先刚到这里时,就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提出:北川有一些地方地理环境差,不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不帮助这些居民迁移到适宜居住的地方去?后来他了解到,这种人口迁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能仅靠拍脑袋就提出建议,他为自己幼稚的提问感到惭愧。他还在书里真实地记述了如何逐渐融入北川的生活,并对北川人的性格、处事、为人有了更为准确的认知。北川人的可爱和可敬,体现在他们历劫重生的勇气和日新不已的奋进上,因此他这样描述北川人,“不会沉溺在苦情之中,而是将哀恸转化为新生的动力,回馈给人间大爱的是蓬勃向上的活泼容颜”“无论时代如何加速,世事如何纷扰,他们都能因应时势改变,总有那些亘古存在的事物在背后给予他们笃定的精神和气定神闲的姿态”。这一刻的理解和共情,是只有一名真正的北川人才能生发的。
二
但刘大先并没有止步于做一名北川人,他始终没有放弃一名学者的职责。书中的一个细节很有趣——有一天,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问他:“你觉得做学问这个事情的价值在哪儿?”刘大先反问:“那你目前做的工作意义在哪里?”副县长回答:“我搞项目,切切实实地改变了本地人的生活啊!”刘大先就说:“我生产知识和理念,可能没有你那么直接,但是从长期来说,也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尽管刘大先是这样回答的,但他也从这次对话中发现了自己的弱点——这位副县长可能因为其工作成就更有踏实感,而自己有时候不免陷入空虚。可以说,他下决心做一个北川人,其目的就是要克服学者的这一弱点。我认为他做到了,这本书就是他的沉思录,这些沉思都与现实和大地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研究文学的学者,刘大先的沉思主要集中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上。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现实担当上的一种自觉意识,但如何讲述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刘大先以北川的转折变化为切入点,围绕讲好中国故事展开叙述。在他的描述里,北川过去是封闭的,与外界的连接有许多阻隔,但这一切在新北川荡然无存,“关隘被打通,隙缝被弥合,隔阂在消除,新北川同世界贯通为一”,“北川的封闭性在新时代全然洞开,以开放的姿态显示出新生的样貌”。作者通过对比,着重描述了新北川的故事。
至于怎样讲述中国故事,他用了一个词:在路上。他由北川的修路,思考到关于速度、目的地和归宿等问题,并得出结论:当代人在路上奔忙,“在路上”本身就构成了全部的意义。“在路上”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叙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中,它着眼于现在,过去则体现为活在当下的传统。北川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刘大先用了很多篇幅谈羌族的历史和传统,强调了羌族是如何立足于现实而留下记忆材料,并如何用那些挑选的遗产来塑造今日的形象。作者认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稍纵即逝,没有定型的模式,总是处在不断的动态过程中,这让文化拥有了活力。这就是作者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本书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创新性:这是一本沉思录,是一种思想随笔;但也是挂职笔记,有社会调查、有工作实践,是一种记叙文。作者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夹叙夹议,并将抒情性的散文镶嵌其中,形成了一种既稳健又灵活的新颖文体。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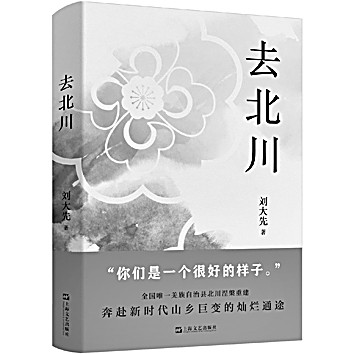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