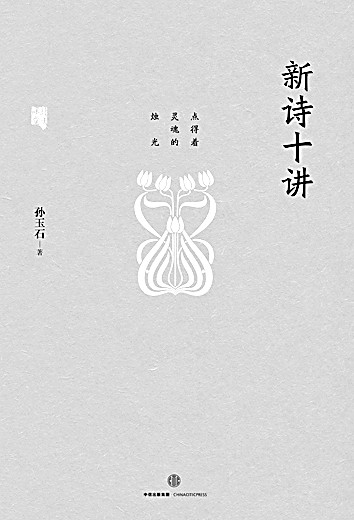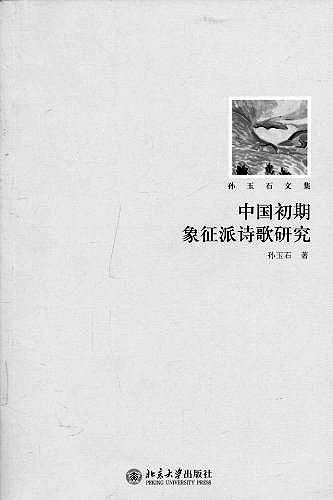学人小传
孙玉石,1935年出生,2024年去世,辽宁海城人。文学史家。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癸卯年腊月初三(2024年1月13日),孙玉石先生在北京仙逝。转瞬之间,半年多过去了。每每想到先生,我都黯然神伤,久久不能释怀。
孙先生人如其名,温润如玉,道德学问兼美。十年前,我尚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任职,孙先生修订《林庚诗集》时,与我鸿雁(当今实是电话、电邮)往复。此情此景,记忆犹新,宛在昨日。在辑校林庚先生诗作的过程中,孙先生一丝不苟,投入了许多情感,付出了巨大精力,不仅反映了其一贯严谨的治学风格、勇于自我批评的律己精神,也体现了其尊师重教的君子之风。今日回望此事,我方意识到,孙先生修订《林庚诗集》的过程,不仅攸关该书的版本,也是一段值得记录的学林佳话。因此,本无资格写孙先生的我,甘冒附骥之嫌,将这段过往诉诸笔墨,庶几使孙先生这些闪烁着人性之美的文字不至于沉没,也算是后学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吧。
缘起
孙玉石先生是声名远扬的北大中文系55级的一员,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任教,是中文系的一代名师。199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费振刚先生门下读博士。那年9月9日,在中文系研究生迎新会上,孙先生作为教师代表之一,给我们讲了一番话。他谈到中文系与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差距,勉励同学们要有危机感,发愤学习,为这所古老的学府争光,言语中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
孙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在现当代文学,尤以鲁迅研究蜚声学林;而我所学是古代文学先秦两汉一段,与之相去甚远,在校期间,我并不曾向先生讨教过。巧合的是,孙先生与费振刚先生及师母冯月华老师,都是鞍山一中的同学,自初中起就同在一个年级,中学毕业后,又一起到北京读书(孙先生、费先生在北大,冯老师在北师大)。孙老师的大名,是费、冯二老口中的高频词。因有这层关系,我对孙先生自然也多了一份亲近感。更幸运的是,在离开校园以后,由于编辑林庚先生诗文集的机缘,我得以走近孙先生,感受其为人为学的风范,多少弥补了在校时不曾求教的缺憾。
2001年8月,我作别燕园,到毗邻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当年10月,我策划为林庚先生出版诗文集,很快得到林先生的首肯。按林先生预设的时间,经过近四年的艰苦努力,2005年4月,林先生95岁华诞庆祝会前夕(林先生生日是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九,庆祝会特意安排在春暖花开之时),九卷本《林庚诗文集》如期出版。《林庚诗文集》是林庚先生平生创作的诗、文的总结集,计收著作、诗文集17种。其中,第一卷收录林先生早期的四种诗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第二卷收《问路集》和《空间的驰想》两个诗集。此外,林先生尚有一些诗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经辑录,作为《集外集》收入第九卷中。
《林庚诗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袁行霈、彭庆生等几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彭庆生先生,对大部分稿子进行了精心校对,对诗集也作了认真审订,并辑佚了部分作品。但由于文集全系重新录入,字数有近300万之多,加之我刚入行不久,编辑业务尚在起步阶段,又要赶时间,仅凭一己之力,确实力有不逮。书出版后,我发现校对方面留下一些遗憾。这令我如芒在背,深感有负林先生信任,也愧对读者。进入2006年,我便决定将林先生著作单行出版,既可对文字再加校对,提高编校质量,也便于读者选择。
较之《林庚诗文集》,单行本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每种书中增加了一篇《导读》,以帮助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林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同时,经袁行霈先生应允,单行本将其《燕园南62号——记恩师林庚》一文作为《总序》。承担《导读》撰写工作的,有孙玉石、彭庆生、林东海、钟元凯、陈平原、徐志啸、张鸣诸教授,他们都曾亲炙林庚先生,又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十分理解林先生著作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导读》之事,我才有了向包括孙玉石老师在内的诸位先生请益的机会。
辑佚
2006年4月10日晚,我拨通了孙先生家中的电话,简要汇报林庚诗文集的出版情况,表达想请其为林先生诗集撰写《导读》的愿望。孙先生欣然接受,并表示:愿为林先生诗集写点东西,一来自己研究这个领域,二来经常听林先生谈诗。孙先生同时告诉我,林先生尚有诗未收入《诗文集》中,还应做进一步搜集。想来在此之前,孙先生就有意收集林先生的佚诗了。
在北大中文系,孙玉石先生属于现代文学教研室,他从1979年开始在北大开设新诗导读课程,影响了几代北大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孙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讲求实证,注重史料,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做到言必有据,树立了一种研究范式。有学者评价:孙先生为建立现代史料学所倾注的心血,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无疑,孙先生把收集林先生的佚诗作为他史料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尽其所能搜集林先生的佚诗,而且逐一进行辨伪、校勘、系年、注释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林庚先生其他各种著作,都是在《林庚诗文集》基础上单行出版的,做起来相对简单,撰写《导言》的各位先生相继完稿,图书随之陆续出版。只有《林庚诗集》要做较大改动,尤其是《集外集》部分,要重新辑校,工作量很大,因此交稿时间不断延迟,直至林庚先生2006年10月离世,此书也未能出版。2007年1月20日,孙先生在为《林庚集外佚诗九首》所撰《附言》中说:“林庚先生著作其他《导读》的几本书,在先生离世前,都早已出版了,而这本收有许多佚诗的《林庚诗集》的导读,却由于我的疏懒而拖延,至今未出,这是我深深感到遗憾的。现在将这些佚诗,送与林庚先生的在天之灵和热爱林庚先生诗的读者的面前,也算是一点纪念和补偿吧。”重订林先生诗集及撰写《导言》等工作,本就是我有些不知轻重给孙先生增加的额外“负担”,他却因此而自责、道歉。感动之余,我没有勇气再主动追问书稿的进展,听凭孙先生自己安排。
孙先生虽然很忙,但一直没有停下辑校林先生佚诗的工作,不仅利用网络资料,还亲往图书馆,查阅旧报纸、杂志,以求作品出处、文字等准确无误。2014年2月3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四,孙先生给我发邮件问候新年,并说:年前赶完一些拖欠的急活后,便转为校对《林庚诗集》已排的清样,并编辑《诗集》集外内容。一个月后,孙先生给我发来了《集外集》“定稿”。虽曰“定稿”,但他的校订工作并没有停止。紧接着,他又通读了一遍《集外集》的电子稿,做了些改动,有必须删削去的,均用红色标出,要我酌情处理,并附带告诉我:“发现林先生在为厦大学生铁声合唱团写的团歌,歌词只见主歌四句,很有林先生风格,可惜副歌尚未查到。已录入文本。待查到后,再告之。”
1957年,林庚先生的《红楼》一诗在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第1期发表,在全国大学校园广为流传。这首诗创作于何时?孙先生根据《红楼》出版的时间,将其系于1957年。通过搜读网上资讯,他得知,林庚先生曾说过《红楼》一诗写于1956年12月13日。他又查到马嘶先生(原名马守仪,北大中文系1953级学生,《红楼》杂志编者之一,撰有《林庚评传》一书)的文章《林庚先生的诗化人生》,其中有林先生自引《红楼》诗,并答复马嘶问询此诗之信。孙先生由此确认,此诗的写作时间应以马嘶文章所述为准。孙先生对史料的孜孜以求,于此可见一斑。
对林庚先生的诗,孙先生极为熟悉,似乎凭直觉便能分辨真伪。2014年3月16日,他来信告知,下午再读清华《文学月刊》复印件,在第2卷第2期上林庚先生论诗的散文《烟》中,读到一首四行诗,是论诗的诗,林先生托为“一个失名的诗人”所作,但实际上应该是林先生自己所作,“诗意尚有价值,也符合先生一贯的新诗创作美学思想主张,遂录下,按时序置于《集外集》文本中第19页”。当然,如孙先生这样严谨的学者,秉持的态度自然是审慎的,“请一阅,暂供参考。倘经斟酌商定,不予收入,便可去掉”。
2014年6月,《林庚诗集》正式出版。当月10日,我到蓝旗营孙先生家中,送上几册样书。看到样书,孙先生自然很高兴,但紧接着就告诉我,不久前,他读到吴晓东教授的文章《异乡客的视角》,吓了一跳。原来,此文评论的是林先生的《异乡》一诗,孙先生感觉诗题陌生,以为《林庚诗集》漏收此诗,核查后才发现,此诗就是收在《春野与窗》中的《风雨》,收入《问路集》和《林庚诗选》时改题为《异乡》,且有详细说明,这才放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孙先生坚定地走上了史料研究的道路,此后的学术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史料展开的。辑校林庚先生的佚诗,孙先生可谓不遗余力,竭泽而渔,是其学术上实证精神的一种自然反映。
真诚
在修订《林庚诗集》的过程中,孙先生不时给我发邮件,只要发现任何一处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就会迅即告诉我,或发邮件,或打电话。今日稍加统计发现,仅2014年3月,孙先生给我的邮件就有20余封(不排除有我未及时保存下来的),有时一日两三封,其追求完美的精神,彰显无遗。孙先生心细如发,不放过一字一词,这份执着,体现的是其治学风格。同时,其字里行间也折射出一种严以律己的自省精神。
孙先生的自省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学问的敬畏和知错必改的勇气上。只要有一丝疑问,或是发现一处错误,他总是第一时间通知我。对于林庚先生散文《烟》中的那首无题的四行诗该不该收入《集外集》,他心里一直打鼓:凭着推断将此诗收入《集外集》,是否妥当?有几天,即便是夜里,他仍难以安心,琢磨着如何处理此诗。直到有一天深夜,孙先生终于有了答案,给我发邮件:“晚上我又为搜寻别的,阅中,得暇读到商伟赏析林先生《路》一诗文字,发现收于《集外集》第77页的四行诗《无题》,原是《路》一诗中的最后一节。这四行诗收入时,读起来总觉得面熟,匆忙中也翻过《问路集》等,由于看得不仔细,暂定收入,结果还是出了这个硬伤性错误!请将这四行《无题》,从目录和文本中删去,并为此再深致歉意!”
诗集出版之后,孙先生还不时有所发现和订正,并撰写了《〈林庚诗集〉之〈集外集〉编后零札》一文加以总结,检讨辑校过程中的失当之处。
2014年6月24日,孙先生来信告诉我,前段时间因家人生病,未能认真翻阅出版后的《林庚诗集》,“近日,因思考林庚先生在厦门大学十年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索问题,重读《集外集》的部分诗作,忽然发现这里面所收袁良骏发现之香港《红豆》上所载《寒夜》一诗(《林庚诗集》第415页),乃与此书收入《北平情歌》之《寒夜》一诗(《林庚诗集》第203页),从标题到文字,完全重复了。此为《集外集》的误收,也是整个《林庚诗集》的一个错误……书既已出,这一错误,已无法挽回。只能待此书有可能重印时,将后者删去,作为一种弥补了。谨此说明,并深刻检讨,向你及出版社深表歉意!”我回信表示,把关不严,责任在我,但孙先生又于27日作复云:“《寒夜》一诗,我过分依据袁良骏的发现文章和林庚先生的复信,就没像其他佚诗那样,去与前面集内诗作,进行仔细检核。如你所说,林先生因‘误记’而所写的那段文字很有意思,甚至可说很珍贵,可谓一个‘美丽的误记’,留在这里也好,等于必要的重收。将来再印时,也不一定删去,仍可作为‘特例’重收,只需在注释里多加几句说明。”
《寒夜》一诗的重收,令孙先生“耿耿于怀”,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责道:“袁良骏兄误将已收集的《寒夜》视为集外‘佚诗’,之后已有陈国球先生的文章指出其误处。而我编的《林庚诗集》之《集外集》已是陈国球先生大作出版九年后了,这笔误将林庚先生已刊作品当佚诗收入的‘责任’,就更使自己为学识之谫陋而惭愧不已,为编辑的疏忽而应承担无法推诿的责任了。”从编辑角度看,如此疏忽,责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孙先生无一言加我,将责任全盘揽下,非恕道在心之宽厚君子,何能如此?
温儒敏教授曾如此概括孙先生的治学风格:“孙玉石几十年投身学术与教学,对学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真诚,容不得半点掺假或差错。他写文章,一个论点,一条史料,甚至一个注解,都要反复斟酌,毫不马虎。”(《王瑶先生的大弟子孙玉石》)在与孙先生的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在学术上这种“容不得半点掺假或差错”的宗教般的真诚。
孙先生的自省精神,还体现在他能时时剖析自己,追求完美。在给我的信中,孙先生不止一次说道:“给你们添麻烦了,望谅!”“因我的仓促马虎,带来的诸多麻烦,恳望谅解。一切为将先生的诗全编一书出好,宁漏勿错,特别不出硬伤和错讹!”对书稿迟迟不能完工,孙先生自责道:“此林先生的诗全编《集外集》事,因我而拖延已久,心甚惭愧,祈望谅解!”“我主要为我的拖拉给本书带来出版的延宕,深感歉疚……出林先生《诗全集》,包括《集外集》,应是难得的喜事,这事的拖延,我应负主要责任。为弥补此过,总想竭力将《集外集》做得好些、全些,尽量少留一点遗憾。看来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可能,也可说肯定还会留下遗憾的,只能以后再弥补吧。”作为后学晚辈,先生的这些话,读来不啻千钧之重,如金玉良言,时时提醒着我如何谦虚做人,严谨为学。
屈指算来,孙先生2014年时已是年满八十虚岁的老者,而且他的夫人张菊玲教授正患重病,需要照顾。其时,先生可谓身心俱疲。他曾提及自己的状况:“一直因过敏性鼻炎,类感冒,喷嚏联翩,不断流泪,天天挣扎着在做最后交稿前之校阅,已近四个月了。如此拖拉,心颇惴惴。”今日重温先生的这些自白,心痛之余,更多的是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
尊师
孙玉石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倾尽全力辑校林庚先生的诗作,最大的动力,无疑是出于对学术的虔诚,同时,其中也饱含着他对林先生的尊敬与热爱。林庚先生1952年自清华移教北大,是中文系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孙先生自上大学起,便钦慕林先生,大二时,就模仿林庚先生,写作了十首现代诗,并以《露珠集》为题发表于北大校园刊物《红楼》。毕业留校后,孙先生一直未离开过北大,与林先生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颇得过从之乐。
在辑校林先生诗作过程中,孙先生时常说到“应该”二字:“这是为林先生的事,也为新诗,我应该做的。”“自厦门《新诗形式的研究》一文录出的诗,尚须慎重考虑,可更严些,集外诗部分,应更坚持宁缺佚而勿误收的原则。我可能意在广搜少漏,却忽略了发生硬伤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了。望谅!在学术上,为林先生,为工作,你对我都不必客气。”
孙先生对林庚先生的崇敬之情,时时洋溢于其文字中间。在2014年3月26日深夜所写邮件中,孙先生不无感慨道:“整理阅读过程中,我对于林先生谈论新诗的诸多文字,对于先生探索新诗艺术发展的思考,产生了一种新的浓厚的兴味。它们在新诗理论与创作发展史上,有独特的理论思考价值与未来性意义。”
孙先生对自己的老师林庚先生诗歌的那份热爱,是由衷的;对老师的深情,也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在《林庚诗集·写在前面的话》中言及孙先生对此书的贡献:“这个全新的版本凝聚着孙玉石教授的心血,也承载了他对林庚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对此,孙先生的回复是:“你太客气了,过誉之言,实不敢承受。”我深知,为林庚先生的诗,为新诗的研究,为学术事业,孙玉石先生从来不曾掺杂一丝功利目的。
在林庚先生过95岁生日时,孙先生撰文《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以为纪念,正题为《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美文,“相见匪遥,乐何如之”一语,出自林庚先生1996年元月3日致孙玉石先生夫妇的一封信。那时孙先生在日本,经历了1995年1月的神户大地震。经孙先生同意,我将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用作《林庚诗集》的《导读》,这也许能“相得益彰”吧!
围绕《林庚诗集》,我和孙先生来往8年有余,“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林庚先生有诗云:“人生的提纯,诗人因此也是一场修行。”那段编书的日子,对孙先生和我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修行。谨以此文纪念孙玉石先生。
(作者:马庆洲,系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南国学术》〔澳门大学学报〕副主编)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