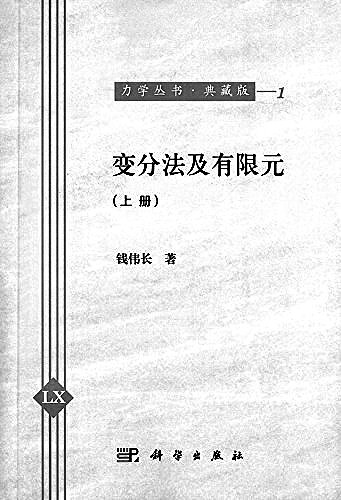学人小传
钱伟长(1912—2010),祖籍浙江杭州,生于江苏无锡。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1994年后改为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著有《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弹性力学》《变分法及有限元》《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等。
钱伟长青年时代“弃文从理”的故事广为流传:1931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国文成绩优异,数学、物理、化学成绩糟糕,原本打算读文史专业,但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他毅然投身物理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实际上,虽然在读大学时选择了物理专业,但钱伟长一生从没有放弃过文史。晚年,他仍对文史保持着极大兴趣,并且进行过一些文史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教育家,在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期间,钱伟长一直秉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把人文艺术课程作为理工科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
家学渊源
1912年10月,钱伟长生于江苏无锡洪声里七房桥。他的祖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靠在私塾教书为生,家境清贫,中年就离世了。钱伟长的父亲钱挚和四叔钱穆继承了钱承沛的衣钵,以教书为业,生活也不富裕。钱伟长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曾祖父鞠如公是前清举人,但一生没有做官。祖父承沛公为秀才……家虽清寒,但父辈昆仲皆好学之士……家父钱挚国学基础好,对《资治通鉴》研究有素,以工整的小楷作了密密层层的圈点批注。四叔钱穆(字宾四)对圈点本视为珍品,爱不释手。”(倪平《钱伟长谈四叔钱穆》)
1919年秋,钱穆就任后宅小学校长,把钱伟长带在身边。叔侄二人都住在学校,钱穆钻研学问时,钱伟长常常伴陪在侧,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有时温习功课,有时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还似懂非懂地看了一些西方名著。钱伟长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四叔和父亲共同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四叔“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钱伟长有时会听四叔讲文学,从《诗经》《史记》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派、晚清小说,脉络清楚,有典故有比喻,妙语连珠,扣人心弦。钱伟长说,他对文史方面的兴趣主要得益于四叔的熏陶和影响。他还回忆,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每年夏天都会有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自己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钱伟长的六叔钱艺、八叔钱文也都擅长文学。他在《八十自述》提到,自己幼年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他就在琴棋书画的环境中受到传统文化的陶冶。他的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刊出以“别手”为笔名的文章。八叔只比钱伟长年长七岁,他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他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演义小说,继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八叔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在幼年时,八叔也是他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钱伟长每两天写一篇作文,交给八叔批改。这一训练非常有用,在进入学校读书后,钱伟长的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除了家庭环境的熏陶,钱伟长中学时还得到唐文治、吕叔湘、杨人楩等文史学者的培养。在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面对《梦游清华园记》这个作文题,钱伟长写了一篇450字的赋。晚年,他不无自豪地回忆,他写的这篇赋,当时命题教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说:“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
钱伟长不仅写旧体赋,也写新诗。《清华暑期周刊》曾发表过他的新诗《荷叶上的露水》,此诗青涩细腻,充满灵动。在一次演讲中,钱伟长曾提到大学时代的文学生活:“对于周刊方面分为对内对外两种,对外是文艺性的,当时的编辑者有曹禺、曹葆华(现在解放区)、李健吾、卞之琳等,对内是副刊,写同学生活情形。”(《战前清华学生生活——记钱伟长先生演讲》,1947年3月23日《清华周刊》)可见,上大学后钱伟长仍然关注文学。
人文情怀
深厚的人文素养与敏捷的科学思维,在钱伟长身上相得益彰。钱伟长的学生黄黔这样回忆自己的老师:“文学使他思路清晰,讲课写文章都明明白白;文学使他文笔流畅,几十万字的讲义两个月就写出来了;文学使他富有想象力,灵感来得既多又快。”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伟长常常感慨西方摆脱中世纪的桎槛,一方面吸取古希腊文化,作为精神武器,搞文艺复兴;另一方面,从阿拉伯人手中学会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作为物质武器。1951年1月,钱伟长撰写的文章《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在《中国青年》杂志刊出。这篇文章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发明创造,如种植水稻、修建水利、九章算术、祖冲之圆周率、天文历法、木牛流马、石油燃料、造纸技术等进行了梳理。他总结说:“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经常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只是在近一百多年间才落于欧洲人之后’,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不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残酷的压迫,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无知和助纣为虐。今天,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了解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们骄傲地继承着这笔光辉的遗产,我们热爱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无休止地劳动,不断地创造,来丰富我们光明的前途。”1953年,《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这篇文章扩展成为专著《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出版。这本书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满怀自信建设新中国。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是钱伟长一生奉行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如何输入电脑的问题困扰着中国人,当时甚至有人公开宣扬“汉字无用论”。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研究解决电脑汉字输入的难题,他发明的汉字输入法“钱码”促进了中文信息化处理和汉字的现代化。钱伟长在《在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字是紧紧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改成拼音文字,那么老实说,诗、词、对联、书法家都不存在了……我们的诗词无论如何可以远远超过各国的诗词,一个词的妙用可以把一首诗写活……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国际文字,我们应该保护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到了晚年,钱伟长对历史文化仍旧有着浓厚兴趣。他的研究不仅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贡献,对年轻人也有指引作用。1996年7月,钱伟长在上海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说:“前几天我还在学夏朝商朝的历史,很有意思,好多历史我过去都不晓得,现在我对很多事有很大的理解,很重要的理解,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他晚年还写过《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契丹族起源与流变》《华夏的由来》等历史领域的文章。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钱伟长的教育理想,也是他的教育理念。钱伟长1983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又任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校长。在多年办校过程中,他非常关心文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认为理工科学生必须懂人文科学,因为文科可以起到文化熏陶和培养通才的作用。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钱伟长“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把培养理想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放在首位。他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学生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特别是加强道德教育,目前显得尤为紧迫。”钱伟长对当时一些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阐述了德智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他对上海工业大学的新生说:“你们到学校来受高等教育,什么叫高等教育?是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要转变你们的人生观,使你们生活有目的……第二,你们要获得建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是给你们武器,一个是坚定你们的方向。”这里所谓“给你们武器”,指的是智育,是学生获取的知识和技能;所谓“坚定你们的方向”,谈的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
钱伟长的人文教育理念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钱伟长人文教育的核心和终极目的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钱伟长看来,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他把是否具有爱国精神看作教育成败的标志。他强调:“作为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祖国有责任感。”“要理解一条:没有祖国就没有任何个人的出路。”他又说:“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负。”他指出,我们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某一专门的课程教学分开,不能只是把爱国教育看作现阶段的政治任务。对于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钱伟长提出要从中国历史中发掘爱国主义思想资源。他认为:“历史和地理课程,不能仅仅作为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而忽视这些课程在国民教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应该通过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青年学生的思想之中,并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内在力量。”
钱伟长还提倡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资源。1987年,他在一次教学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钱伟长认为,教材的编写应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有人认为理工科教材与爱国主义教育很难搭边,钱伟长不这样想。他以物理教材为例,中国古人在物理学上有许多发明和发现,例如在力学方面,《墨子·经说》中关于权衡的学说,涉及杠杆原理;《武经总要》记载,宋太祖开宝二年冯义升、岳义方发明了原始火箭;在电磁学方面,早在战国时便已发现磁石及其吸铁性,并已经懂得利用磁石指南,还发明了“司南”。钱伟长认为,像这样的材料完全可以编入教材来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钻会一门纯科学,就会整个地推动科学事业前进,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然而,积40年之经验表明,纯科学要搞,不搞就不是一个科学家,可是仅仅埋头于纯科学,其社会效果不一定好。要达到充分的社会效果,你就必须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在钱伟长看来,没有人文素养、人文情怀的支撑,技术有时候就会沦为危险的工具,需要通过人文教育来培育学生的理想情怀。他说:“大学的人文教育应该重视文学教育。通过文学教育引导学生接近人文理想。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激情、美好的人性光辉。我相信,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使学生获得心灵的丰富,懂得人世间美好事物的价值,使自己的精神、道德趋于完善和美好,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
在主政上海大学期间,钱伟长经常和人文学科的教师座谈,讲自己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上好人文课。钱伟长十分重视建设中国文化史课程。2003年春,91岁的钱伟长约请中文系教师,商谈编写《中国文化读本》,并委托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董乃斌教授主持此事。书成付梓之际,钱伟长欣然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思惟世界大势及祖国未来,深知发展现代先进科技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乃中华腾飞之双翼。先进科技必须认真引进,传统文化亦绝不可弃。我中华古国有五千年绵亘悠远之文明,文化宝藏之富厚贵重堪称举世无双。历代先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伦理、育人修身、处世智慧诸方面的种种创造,不仅光耀史册,而且沾溉万世;不仅有助于塑造崇高纯洁之人格,而且确能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之推动力。对于这份丰厚遗产,我们应当妥善继承,发扬光大,绝不可轻视冷落,而贻无知不肖之讥。我上海大学师生,文科者自需负起加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之责,即使理工科师生,也应以一定时间涵泳学习,俾能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品位高尚、发展全面之社会栋梁。”中国文化史课程不仅成了上海大学文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并且还向理工科专业学生开放选修。
在与年轻学生的交往中,钱伟长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知识面相对狭窄,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对科学史不甚了了,对于自己所从事专业的发展史一知半解。钱伟长对这种现象非常重视。在上海工业大学学生政工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讲道:“我们是一个工程学院,从某种意义上看,工程学院出去是当工程师的,专门搞技术的。我认为他首先是社会的人,要适应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还有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要有一定的素养。”在他看来,理工科学生也必须懂人文科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质。忽视人文、艺术等领域的教育,会导致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和实用性,社会整体变得浮躁,缺乏对长远发展和深层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社会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也会受到削弱。钱伟长主张把科学、人文、社会教育相融合:“我们不能躲在学校里,要把围墙冲开,不要泡在教科书里。文学院、法学院、经济类学院各方面都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科研的起点。”
1985年,钱伟长发表《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高声疾呼:“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理工分家,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的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建设四化人才的培养质量,现在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如今,上海大学的课程设置实践了钱伟长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办学思想,这种办学理念和实践有助于理工科学生学习人文科学。在文理渗透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大学建设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公共课程,取得了良好效果。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精神和内涵”,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教育仍有重要启发。
(作者:李飞跃,系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