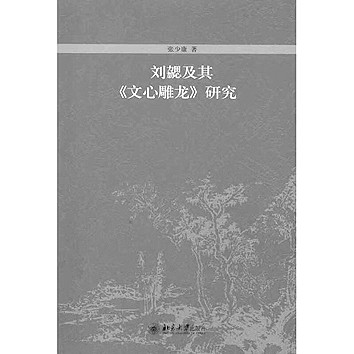张少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长期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推动了龙学研究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同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古代文论学科方向的建基人,在长达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的研究从先秦贯通清末,在汉魏到唐末这一段尤有建树。从《文赋集释》《文心雕龙新探》(后拓展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文心与书画乐论》《诗品》《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等文论专著研究,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中国古典美学论稿》《文心与书画乐论》等宏观的纵向文艺史论研究,最新出版的《张少康文集》(下文简称“文集”),包含了中国文论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和理论问题,而在古代文艺创作论方面钻研最深,创获最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1978年我进北大中文系回炉班时,是张先生为我们开设文艺理论专题课,补上了六十年代本科时期的缺门。后来在读研究生并留校以后,因张先生和陈贻焮先生来往较多,我也在旁听他们的学术讨论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的专业领域是汉魏到隋唐五代诗,研究对象和时段与张先生的主攻方向一致,所以近几十年来用心学习过张先生赐我的全部著作,所受教益极多。作为一个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我主要侧重于创作史,常常苦于理论修养不足,所以我学习古代文论主要是从本专业的研究需要出发的,我也没有能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全面评价张先生的成就,只是在拜读张先生著作的时候,往往会参考对照其他同类著作,慢慢地对张先生的研究成就和特色也有了一些体会。现在主要谈谈以下三点较深的印象:
一、张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以古代文学史为坚实基础,从不停留于一般的理论阐释,而是立足于大量作品分析,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展紧密贴合,深入考察古文论概念的理论内涵,所以他的研究成果能更及时更切合地解决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能一直走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前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已经分别形成两门学科,当时出现了好几种文学批评史。我遇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时,总是会去翻查最有代表性的几家著作,比较他们的说法,最后往往会选择张先生的解释。比如,“意境”是八十年代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很多论者对这个概念的形成有相当全面而深透的研究,但是我在做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这个专题时,总觉得很多解释都胶着于情和景的关系,不能非常贴切地说明王孟诗的意境特征,而意境这个概念本来应该是在王孟诗里体现得最典型的。后来我看到张先生1983年在《论意境的美学特征》一文中的解释,觉得特别能贴合我的理解,他举出很多诗例,指出意境绝不能和情景交融混同,并将古代文艺批评家的分析概括起来,认为意境应该有几方面的特征:境生象外;是实境和幻境结合的产物;而且应该超绝言象。他把这些特征和盛唐公认为意境优美的诗例相印证,最后对意境特征作这样的概括: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景表现虚境,使有形描写和无形描写相结合,使有限的具体想象和想象中无限丰富的形象相统一,使再现真实实景与它所暗示、象征的虚境融为一体,从而造成强烈的空间美、动态美、传神美,给人以最大的真实感和自然感。我认为,这是最符合诗歌创作实际的一种解释,所以后来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教学,只要涉及意境的内涵解释,我都会引用张先生的这段话。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界和文论研究界有很多共同的讨论话题,张先生总能提出有突破意义的观点。比如,《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一文,和当时文学史界研究儒家诗教论的热点问题也有呼应,这关系到对白居易诗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张先生认为,白居易的诗论是直接从民本思想中引发出来的,他是要用诗歌为民请命,并不是一般地讲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是民本思想积极方面产生的结果。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有它的局限性,比较典型的就是《毛诗序》过分强调要为教化服务,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表现出简单化、绝对化和忽视艺术特点的倾向,白居易的“六义说”同样存在这种局限性。陈贻焮先生在论中唐两大诗派的长文中曾经指出过白居易诗论的局限性,所以他很赞成张先生的观点,认为洞察更深。可见,张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非常敏感,很善于从中捕捉重大问题,并努力追根溯源,把它们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来认识。
二、张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非常注意吸收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并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考据传统与当代的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他不同于当代很多文论研究家的独特理路和风格。
古代作者生平思想的考订、文献版本的整理研究,原来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看家功夫,虽然现在仍然有不少理论研究者也都在做,但张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把这些工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比如,他对刘勰的生平和思想,就下了很多功夫。王运熙先生在张先生《文心雕龙新探》一书序言中肯定张先生对刘勰的身世作出了新的探索。后来,张先生又在《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对《新探》一书加以拓展,以更翔实的考证,对刘勰的家世、刘勰之父刘尚的仕历和卒年、刘勰的生卒年,以及入定林寺的时间和原因、刘勰入梁以后的仕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辨析。此外,如《皎然版本新议》梳理了《诗式》以及皎然的其他著作的版本情况,《关于〈吟窗杂录〉及其版本问题》一文考辨《吟窗杂录》的编撰者,对几种善本进行比较,并做了极为详细的校记,这些文献整理工作在八九十年代的文论界是较为少见的。
又比如,张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渊源的追溯,也下了很大的文献功夫。《文心雕龙新探》一书把刘勰的文论分成十四个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思想的溯源。这可以说是张先生的研究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王运熙先生在序言里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本书对刘勰理论历史渊源的探讨,尤为重视。他在这方面搜集了许多资料,除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论外,广泛涉及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各个方面,并与刘勰的理论联系起来,细致剖析其源流关系。”并指出这方面的研究以前虽然也有涉及,但比较简单粗略,而张先生“做了较多的发掘和开拓,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因此显得特别富有新意和特色”。比如,张先生提出刘勰对道的认识,一方面是继承了荀子,另一方面是发展了《易传》,就很有创见,后者在《文心雕龙》中各处都有体现,分析难度最大又特别精彩的可见于他对隐秀论来源的阐发。
对《文心雕龙》里一些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张先生也善于运用材料的比较作出全面的辨析,方法独特而科学。比如,“风骨”的问题,是汉唐文学史的一个重点。但刘勰所说的“风骨”是什么意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争论非常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把风和骨分开来理解,认为风指文情或文意的特点,骨指文辞的特点,这种说法最为流行,影响也很大;另一种认为风骨是一个概念,有时分开讲也是指统一的风骨的意思,因为骈文是互文见义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某些区别。这方面研究最有说服力的是张少康先生。他的做法是把《文心雕龙》全书中所有关于“风”和“骨”的论述全部摘引出来,分析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他发现,全书论及风骨的地方,除了《风骨》篇以外共有十四处,经过逐一分析,可以确认“骨”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所显示出来的义理充足、正气凛然的力量。“风”在全书中太多,有些与风骨无关,他挑出了八处和《风骨》所论的“风”接近的论述,发现“风”都是指具有儒家纯正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的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气度风貌特征。总的说来,风骨连用,指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风貌美。“风”侧重于作家主观的感情气质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骨”侧重于作品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不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说的风骨又随着他本人的思想而有所差别。这种解释基于对刘勰本人使用“风骨”一词的全部材料,确实比较符合刘勰的原意,也和当时人物论、画论中的风骨协调一致,更重要的是与盛唐诗人所说的“建安风骨”的内涵完全切合。所以,我认为在各种对《风骨》篇的解释中,张先生的这一解释是最为妥帖的。
三、张先生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学术有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孜孜矻矻,从不懈怠;学风极其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且对已有成果从不满足。从他直到今年初摔伤以前还在做《文心雕龙注订语译》这项艰巨的工作就可以看出,他对《文心雕龙》这部理论巨著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他上半年在微信里还多次对我说:“摔跤前刚做完文集清样校勘,《文心雕龙》部分本来想再修订一下。”“《文心雕龙》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又说文集中“粗疏讹误之处还有不少”。总之,张先生在这十大卷文集出版之时,想到的只是不足和遗憾之处。
与张先生的奉献精神和严谨学风密切相关的,还有张先生为人的刚正耿直和行事的低调谦逊,这是尤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翻看文集,我特别注意到他在几部书的后记以及一些给师友、学生写的集序中都表达过对当时学风的忧虑。比如,1998年在《夕秀集》的后记中,他说:“学术研究是要有决心,有勇气,有毅力的。要安于清贫的生活,要有为学术奉献一切的精神,要有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而不为名利追求轰动效应。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学界和广大读者自有公论,如果要借助媒体的炒作,实在是很可悲的。”在《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的后记中,他说:“我看到不少人视学术为仕途和名利的敲门砖,在那里学术早就贬值,学术界也快成江湖了。”所以,张先生从不请人为自己写书评,也从来不见他在任何场合自媒自炫,这种古风在当下的学界几乎已经绝迹了。
张先生视野开阔,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在古代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我这个半外行可以置喙的。以上只是我平时在学习张先生著作时的一些粗浅感想,谨以此表达我对张先生的敬仰之意,并借此机会敬祝张先生耄耋重新,寿超期颐!
(作者:葛晓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