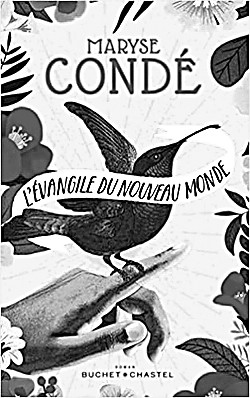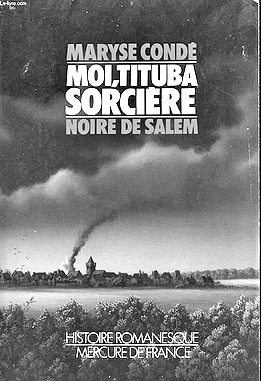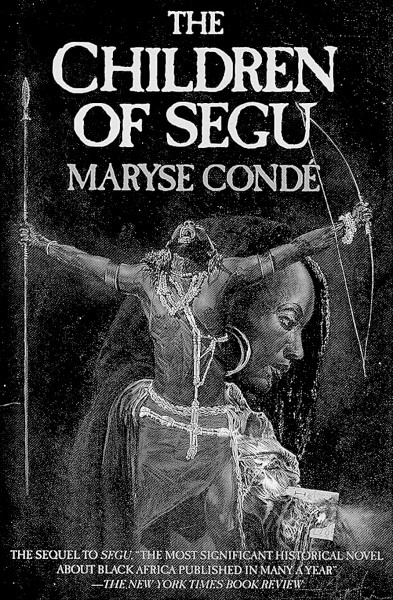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马朗、塞泽尔、法农、葛里桑、孔戴、夏穆瓦佐等加勒比地区作家成了世界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从血缘和人种关系来看,所有这些作家都是黑奴的后裔。在他们的笔下,原始宗教、神话故事、巫术和祭典仪式常常把我们带往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考量,其中,“黑人特质”“安的列斯人特质”“克里奥尔化”“群岛观”等成为最常见的文学主题。“黑人特质”旨在唤起黑人同胞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安的列斯人特质”强调去非洲寻根并不现实,安的列斯才是家园;“克里奥尔化”则强调文化多元,主张西方文化和当地文化融合。
2024年4月1日,加勒比地区法属瓜德罗普岛女作家玛丽斯·孔戴去世,享年90岁。1992年,她的小说《塞古:破碎的山河》(又译《塞古:大地碎裂》)被译成汉语。2023年,她的另一部作品《黑人女巫蒂图巴》(又译《薄如晨曦》)也与中文读者见面。孔戴的小说《埃雷马喀农》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反映了加勒比地区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及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Ⅰ 聚焦殖民创伤
孔戴是一位多产女作家,丰富的学术生涯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作品中,她探讨种族、性别和文化问题,尤其关注非洲人和海外黑人,特别是加勒比海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她先后创作了《德西拉达》《塞古:破碎的山河》《越过红树林》《亲爱的海地》《黑人女巫蒂图巴》《卑劣人生》《里哈塔的季节》《生命之树》等30多部作品。小说不同于游记或史书,为了让一切更加明晰,史学家通常抹去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小说家则相反,孔戴揭开了禁欲主义的面纱,让历史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那些丑陋的东西仍然影响着个人命运和集体意识。孔戴小说中令读者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心灵之旅,也就是主体对自己灵魂的探寻。她希望通过写作来激励人们在当今人种混杂、传统迷失的社会中立足于自我,找回“本真”。
1976年,孔戴发表小说处女作《埃雷马喀农》,讲述一位加勒比妇女在非洲的心路历程。书名在西非马林克语中的意思是“等待幸福”。小说的主人公维罗妮卡·梅西耶以女教授的身份到海外工作,9个月之后,抵达西非国家几内亚。然而,非洲不再是一个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游子的母亲,相反,非洲大陆有了另外一种性别,“慈母”变成了“严父”。因而,重返非洲对于加勒比人来说成了一个再也无法实现的梦。加勒比人对白人说不,而非洲人对加勒比人也说不。孔戴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起初,加勒比人还天真地以为可以回到故土,到非洲找寻精神慰藉。但是,三个世纪的跨度以及跨越大西洋的空间,使这些黑奴的后裔与非洲大陆不可逆转地分开了。
1984年,《塞古:破碎的山河》问世后,孔戴在文坛脱颖而出。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的西非历史,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白人闯入塞古古城的故事。随着白人的到来,古老而神秘的帝国世代相传的旧观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邦巴拉民族的生存遭遇了空前的危机。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君臣们不知所措,陷入迷惘。故事的时间横跨两个世纪:从18世纪的黑奴时代一直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的到来。孔戴巧妙地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一个虚构的家族兴衰融合在一起,同时还掺杂了18世纪非洲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涉及欧洲、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形势。1986年,她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黑人女巫蒂图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蒂图巴是一个混血女奴,因具有与无形之物对话的能力成为家喻户晓的“女巫”。1692年她因行巫被捕,刑满释放后,她回到巴巴多斯行医并执着地追求爱与自由,并最终认清自身的价值。
《会哭会笑的心:童年的真实故事》是一部集写实、消遣与教育为一体的作品。孔戴的记忆是碎片式的,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作品的每一个章节中。她曾毫不犹豫地问身边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殴打黑人?但是,没有人回答她。这样的沉默让她觉得必须靠自己找寻答案。孔戴在一个相对宽裕的环境里长大,她的父母是被法国教育同化了的一代——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并由衷地崇敬法国本土的一切。但是,孔戴看到的则是殖民主义给加勒比黑人同胞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这部作品中,孔戴揭露了法国在前殖民地瓜德罗普(1946年成了“海外省”)撒下的谎言。
Ⅱ “白面具”背后的社会意义
孔戴的小说让读者感兴趣的,是其内心旅程,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寻。这位女作家希望通过写作来激励黑人女性在人种混杂、传统迷失的社会中立足于自我,追求“本真”。小说《埃雷马喀农》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故事发生在塞古·杜尔执政的几内亚,女主人公维罗妮卡试图在西非广袤的土地上找寻过去,搜集与祖先有关的信息。但是,她看到的则是贫穷落后、专制腐败的资本主义。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感情,更对自己来到非洲这一决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与《黑皮肤·白面具》作者的观点不同,孔戴更加关注黑色面具而非白色面具。在《埃雷马喀农》这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与法农笔下相悖的另一种加勒比女人的形象。维罗妮卡出生在一个“黑人资产阶级”的大家庭,她试图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实现父亲对她的期待。她勤奋好学,想方设法得到父亲的认可,以满足黑人资产阶级家庭对她的要求。后来,她对自己的自豪感产生了怀疑。这种内心的躁动来自她对黑色面具的偏执,来自青春期对白色皮肤的抗拒。父亲把她打发到法国,不允许她重返瓜德罗普。为了平息内心的矛盾,维罗妮卡选择逃离,去了非洲。她错误地认为,这趟非洲之行可以彻底解决黑白身份的互换问题。实际上,维罗妮卡成了黑人道德准则的受害者。
如果说维罗妮卡的父亲代表的是加勒比黑人,那么,维罗妮卡试图寻求摆脱的正是父亲的影响。她寄希望于非洲,寄希望于殖民之前的那个过去,寄希望于一个从未受到奴隶制影响的黑人种族。维罗妮卡很快意识到,非洲并不是她想象中祖先所生活的地方,也不是她想象中殖民时代之前的那个过去,而是无法告别的后殖民时代。
Ⅲ 别具一格的叙事技巧
在“黑人特质”文化运动出现之前,加勒比法语文学处在一种真空状态。但是,随着这场运动以及后来的“克里奥尔特性”“安的列斯性”运动的发展,孔戴的文学创作遇到了诸多挑战。首先,她必须要冲破“黑人特质”思想的范式。在一次访谈中,她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开始创作时,她感到并不自由,她用了很多年摆脱塞泽尔的“黑人特质”思想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她还要与黑人激进主义、非洲中心主义做斗争。从《埃雷马喀农》开始,孔戴就冒着巨大的风险,不遗余力地揭开重返非洲的神秘面纱。
孔戴的作品拒绝单一性,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感:她拒绝加入任何文学流派,不断探寻新的叙事形式来揭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被忽视的问题。孔戴认为,她的作品要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要让读者开动脑筋,摆脱作者的束缚并由他们自己做出判断。在孔戴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她总是借助于虚构的人物或历史名人来探讨身份问题。
孔戴从黑人聚居区的文化中获得了灵感,并在作品中融入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语言及风俗。同时,她还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手法:用身兼巫师、乐师及诗人的非洲黑人的口吻讲述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个体与民族相互交融。她的语言清新明晰,而且总是令读者眼睛一亮,她把克里奥尔语、非洲方言和西班牙语词汇巧妙地点缀在法语作品中,总是能够让读者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里尽情地神游,在阅读过后进行深入的反思。
Ⅳ 从边缘走向中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博尔达斯出版社曾推出一部题为《1945年以来在法国的文学》的教材,里面设立“法语地区文学”单元,用以介绍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法语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法语作家被纳入法国作家之列,但是仍然被排除在“法国文学”之外,被刻意安排在所谓“法语地区”栏目。1921年,《巴图阿拉》摘得法国龚古尔奖桂冠,但是,马朗并没有被看成法国作家。1977年,在《文化引领——法语文明与文学》一书中,马朗仍然被安排在法国的安的列斯和圭亚那作家之列。马朗是个黑人,但是,他早就加入了法国籍。正是由于法国公民的身份,他才在法国殖民当局中谋取了一个管理岗位。显然,马朗被排除在法国文学之外跟种族主义脱离不了干系。在《定义与标签之间:南方文学的分类问题》中,克泽维尔·卡尼艾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黑人文学、边缘文学、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新兴文学甚至民族文学,所有这些分类或标签都代表一定的偏见。
在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黑人就是“他者”,处于欧洲白人的对立面。但是,在以孔戴为代表的加勒比法语作家心目中,加勒比地区混杂了非洲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土著人以及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族群,那里的文化将不同源头的族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混杂型或融合型的文化景观。克里奥尔人就是这种混杂文化景观最为集中的体现,而“克里奥尔化”则是加勒比地区语言和文学的最显著的标识。一百多年来,加勒比地区法语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尤其是黑人的民俗和民间传说。每一个主题和意向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都指向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构建。如今,跟马朗、塞泽尔、法农、葛里桑、夏穆瓦佐等人一样,孔戴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热门作家,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担当。历史在变迁,时代在进步,加勒比地区法语作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用“黑人特质”“安的列斯人特质”“克里奥尔化”“群岛观”等思想消解了西方中心的荒谬论调,为纷繁复杂的后殖民时代提供了一盏明灯。加勒比地区文学犹如一座富矿,具有开采不完的价值。这一特殊类别的文学堪称世界文学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作者:刘成富,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