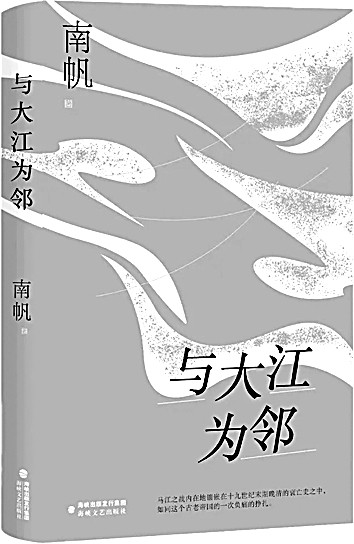【当代文学现场脉动观察】
文学评论与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们各自从不同维度,对存在世界进行深度阐释或呈现。文学评论家惯以“理论判断”来审视、洞悉文学创作的奥秘,作家擅长以细部修辞、奇崛的叙事与想象来建构文本世界。在学者或文学评论家看来,他们是在学理层面探掘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努力发现作家本人也可能未意识到的意蕴,给予创作重要启发。写作与评论,仿佛两根并行但不即不离的铁轨,承载着文学的列车一路向前。
近些年来,渐渐形成一股不小的“文学评论家从事创作”的潮流,如於可训、吴亮、王尧、杨剑龙、张柠、李云雷、房伟、霍俊明等。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之余,在文学创作上仍能独具匠心地运笔,凭借强烈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学理底蕴,亲自“下场”进行文学创作。这种评论与写作的“双向奔赴”,构成一种独特的景观。
实际上,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作家与文学评论家都是“双重身份”的存在,并没有严格的身份界定。应该说,文学评论家从事文学创作,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感悟到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新的可能性,因为优秀作品的背后,必然需要更坚实的人文传统。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是否对之前的文学叙事惯性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冲击力?是否可以与新文学的前辈作家进行叙事美学方面的承接?又如何对中国文学审美视域形成精神性延展?此外,文学评论家写作是否印证了文学创作都是“思想、语言、结构”等元素的完美融合?其形象思维、叙事能力、个性化语言,能否为叙事文学提供一个更有特性的面向?
不少文学前辈兼具双重身份,一面“理性”思索,一面“感性”抒情
“文学评论家创作”之所以能够引起关注,或许首先缘于它冲击了人们固有的“分科”观念。长期以来,人们觉得评论与创作属不同“工种”,应该“各司其职”。通常认为,这两种思维亦很难融合在同一写作主体身上。在这种境况下,就更能凸显出“文学评论家创作”对此偏见的挑战意义。可以说,他们的切实行动不仅是一种反思,也是文学审美视域的拓展。而重新审视两者的有机联系,更是对百年新文学伟大传统的回望。
实际上,我们不难从前辈的写作,来诠释评论与创作“携手”的重要意义。回顾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文学前辈往往都是兼具文学评论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没有“精确”的分科意识,而是一面“理性”思索,一面“感性”抒情,从容地展现着对世界的多样形态的描摹或表述。
鲁迅在写现代小说前,最先在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等方面已卓有建树,且在对国内外文学评述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他融合尼采、叔本华的思想,提出“立人”主张,主张文学应当以发掘人的个性为重要目的。他还以“摩罗诗人”为圭臬,倡导作家应成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的战士”。其实,正是这些文学评论的观念,也“反哺”着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形成“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的审美个性,更给予青年作家、同代人重要示范。
茅盾虽然以写小说知名,却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开创者之一。他最初以文学评论家的姿态,指出新文学初期题材狭小、表现肤浅等问题,而呼吁“文学的目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与失意时的消遣,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这种理念,自是贯穿在他的小说之中,使他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容”,严肃地展现“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自1927年开始小说写作后,他同时也在文学评论、研究方面笔耕不辍。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论,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作出即时性评述,有着准确的把握和评价,与他的创作形成“互文”关系。
这种评论与写作之间的互渗,在当时显然是比较普遍的存在。如闻一多所提出的“理性节制情感”,不仅是其诗歌的理念,更起到了对早期新诗过于散漫自由、不严肃等现象的“纠偏”。被称为“印象文学评论家”的李健吾,虽然主要从事文学评论,也尝试写作“意识流小说”,把对作品的印象置换成对生活、人性的印象叙事。而以《围城》为更多读者熟知的钱锺书,在创作前一直在从事中外文学、文化研究。他饱读诗书、学贯中西及熟谙人性的特质,这种学者修养和气度,在其各类文体的文学创作中体现无遗。
所以,从新文学史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最先从事评论、研究的学者,都是以作家的身份为公众熟知。他们从学术理念中汲取养料,又在创作中思考文学的多种路径,使其作品更具有睿智的品格与个性化的审美风貌,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文学经验。
在学科分工的背景下,依然践行着评论与写作的“双肩挑”
自20世纪末开始,社会分工急剧加速,各学科开始倾向于“互不越界”,甚至同一学科也开始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创作与评论之间愈发割裂。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偏见竟逐渐地被不自觉地广泛认同。所以在这时,谁能用具体的文学作品质疑偏见,谁能思考如何回归评论与写作的血肉联系,就成为文学界所关注的问题。
面对“盛行”的偏见,有许多学者、文学评论家仍践行着评论与写作的“双肩挑”,努力让割裂的两者加以弥合,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周国平、刘小枫、赵园、乐黛云、谢冕、洪子诚、雷达、陈平原、孙郁、南帆、王彬彬等。他们将写作的“形象思维”与研究的“抽象思维”融合,一方面从事评论、研究,另一方面跨越学科的设限,以自由之心书写着对宇宙人生的深切感悟。他们将学术的识见与对世界的关切,深度地融入文字中,既有个性的展现,亦有“有情”的说理。
比如,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平原,以宽厚、中和的笔触,在散文随笔中对当下学术、文化热点问题不乏锐利目光与犀利的剖析,与其学术理念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位学者的“人间情怀”。还有南帆的散文,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身份,更能诠释何为评论对创作的“反哺”。南帆在文学评论、研究中就重视对历史与人性“盲点”、边缘处的洞察,不被固化、僵化的成见所束缚,以睿智的思考,在不易察觉之处发掘出人性与历史的褶皱。而他在散文叙述中,也能以非定论式的理路,深入地体察、探寻世界的“关系与结构”,与他的批评理念形成共鸣。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不仅甘愿坐学术研究的“冷板凳”,更用实际创作去检验和践行自己的学术理念,此中坚守显得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亦鼓舞了更多后继的评论家从事文学写作,以更独特、多变的视角来观摩人间百态。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文化界更为关注这种现象,从而有利于研究者与写作者以更深度的剖析,发掘出文学创作的更多路径与可能。
“两线作战”,促成批评观与创作观相互整合、融合
从近年来“文学评论家创作”的现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写作及其文体、审美形态渐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之前的学者写作,多集中在散文、随笔方面,文体较为单一。但近年来文学评论家的创作,则延展到小说、诗歌、戏剧等多个领域,且明显有批评观与创作观相互整合、融合的倾向。
长期从事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於可训,生动形容“他们这些教文学的教员,是自己不会炒鸡蛋,还要教人家鸡蛋怎么炒”。于是,他就决定“把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暂时放一放,也来试试炒鸡蛋”。他将这个决定称之为“衰年变法”。结合着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所阅读的文学、史学资料,於可训立足本土、回望传统,其笔触指向“乡村教师”群体再延展到“乡村异人”,这些人物丰富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於可训的“转行”并不是个案,还有更多学者试图突破“学院派”的审美思维结构,拥抱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如早期从事散文研究,后在文学史、小说史研究方面卓有学术贡献的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他的批评观与散文史的训练,使其在后来的散文写作中游刃有余,富于才情的叙述引人入胜。王尧书写出知识分子在大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对价值观的选择,其文胆与诗心、人文精神在俗世中的意义,都被作者朴实、细腻、深入地发掘出来。王尧还倡导新“小说革命”,主张重建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主张突破“我自己”的故事,欲与广阔的世界重新连结。理解这种倡议,就不难理解他的小说《民谣》中的“自叙传”式的讲述,这正是对其批评观的一次文学化阐释。
同在苏州大学的房伟教授,也在评论与创作方面进行“两线作战”。他确信“这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对立,必须跳出大学体制培养造成的‘专业幻觉’与‘思维惯性’”。他用扎实的研究,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以丰富的想象力写作小说,又使其文学评论有了独特的剖析维度。他觉得作为一个学者,要杜绝理论训练后所养成的“居高临下”目光,将文学作品变成研究的工具,从而丧失对作品感同身受的审美力。或许,同时从事评论、多文体写作,正是房伟对思维惰性的警惕。此外,还有很多文学评论家也将其评论中所渗透的文学理想,寄托在个人的文学作品中,抒发着对世界的独特关怀,且不乏佳作,丰富了当下中国文坛创作。
“文学评论家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有不少的遗憾存在。比如,很多“学者型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匠气”多而“地气”略显稀薄,亟待将学理与情理进行适度的整合。一些文学评论家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受理论化思维干扰,缺乏现实感而显概念化。其深厚的学理根基没有成为作品潜在的艺术指引,而是显性地支配了文学叙事。
当然,这是“学者型作家”在尝试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是对鲁迅、茅盾等前辈的回望与赓续,是对评论与创作割裂现象的努力弥合,即让两者回归彼此一体、互动、相融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文学评论家的创作是一种“重新开始”,学术界也需要进一步关注这种现象,给予他们鼓励、建议,切实地推进评论与创作的双向互动,进而让中国当代文坛更为多姿多彩。
从另一个角度看,近年出现的关于文学如何“出圈”“破圈”等话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回应、诠释了文学评论家“兼职”“转行”的现象。这个话题,虽然与“文学评论家创作”现象有着不同的指向,但两者始终有着这样的“共鸣”:写作者需要提升作品的内在品质,从语言、结构到内容,都要不断打破常规经验的封锁与桎梏,努力以全新思考世界的方式,来展现人性的深邃与斑斓。毕竟,这是文学审美永恒不变的特质与追求。
(作者:张博实,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