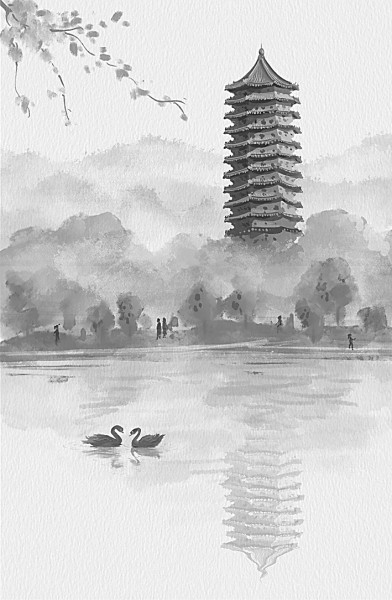今年5月4日,北大校庆日,我回了趟学校。按规定从东南门进,也借此机会搞明白了北大究竟有多少个门。南边西边不算(北边没有门),光说东边吧,就有东北小门、东北门、东门、东南门四道,一门之差,别有洞天,你不小心看错一字,就要走好多冤枉路。
进了东南门,左侧是邱德拔体育馆的北广场,为多家院系的接待站,巨幅标牌印的是:“家·年华 欢迎校友回家。”我在总接待站取了一册《北大人》,季羡林先生题的字,封面印着“巍巍上庠,国运所系,永担使命,与时俱进”,大开本,胶版纸,沉甸甸的,分量感十足。我没带挎包,外衣口袋也装不下,只能拿在手里,但是既要拍照,又要记笔记,碍事。情急智生,我把它贴胸插进衬衣里,束紧,仿佛多了一副上阵的铠甲——不,是多了一面护心宝镜,一块举世皆无的巨型芯片。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行为艺术”。
转身,径直奔向五四运动场。当初是泥巴地,现在铺上了塑胶,我在跳高场地旁找了块海绵垫,一屁股落座,而后顺势躺下,双手作枕,仰观天上的浮云。
60年前,入学不久的一天傍晚,我来这儿练长跑。400米的跑道,一圈下来,尚能摆臂迈腿,从容不迫;两圈下来,转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三圈下来,则头重脚轻,眼冒金星,胸膛像挨刀扎,双腿灌满了铅……心想,自己不是长跑的料,这项目太耗力,太累人,算了,干脆退出。但前有本班男生,后有邻班女生,光天化日,我不能认孬。再说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点困难算什么?于是咬紧牙关,豁出小命,拼出如今所说的“洪荒之力”,坚持,坚持,再坚持……跑完四圈,嗯,腿还长在我的身上,步子居然不再踉跄;跑完五圈,噫,呼吸忽然畅通无阻,腿脚如有神助般异常放松,整个人像要飞了起来。
若问五年半的大学生活有哪些重要的收获,耄耋之年回首,那次长跑度过“极点”后的体验,让我终生受用。
“卞兄,你还记得我吗?”
扭头,是一位年纪与我相仿的老先生。
迅速起身:“你是……”老实说,我认不出。
“提醒你一件事,1966年冬天,去井冈山,攀登黄洋界,我在半腰崴了脚,是你把我背到山顶。”
“哦,记得。可我并没告诉你我是谁,我也没问你是谁。”那年头,做好事讲究不留姓名。
“你胸前戴着北大校徽。我没戴,我也是北大的,中文系。五六年前,看到你一篇回忆登黄洋界的散文,时间和细节,触发我的联想,上网查了资料,确认背我到山顶的正是你。刚才就注意到你,又上网查了你最近的照片。”
“越说越有故事,像一篇小说。”
“说故事也是故事,说缘分也是缘分。同为北大人,今天回了家,不是碰到你,就是碰到他,总有一道闪电会照亮你我他共同的记忆。”
漫步在当年的学生生活区,恍若隔了世。经过上世纪末的改建扩建,昔日的四层灰色砖楼,一律改成了高大敞亮的六层板楼,位置也作了调整。我曾经住的四十斋,前移了数十米。庭院里的几棵大树,槐梓相杂,粗逾水桶,高超六楼,不会是后植的,应该是原住民,与老楼同期落户。如今,老楼完成使命,寿终正寝,而它们依然葱茏蓊郁,坚守故土。
若要打卡,这是最具纵深的地标。
那些建筑面目全非,唯有这几棵老树,是昨日的见证,也是今朝的慰藉。一阵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我抬头仰望树梢,傍午的日头正透过那簇长相最旺的枝叶俯视着我。树嘛,自然在不断生长,它们向天空发展,向地底延伸,向内心蓄力——镌刻年轮,那是它们的年谱,也是过往岁月的天文志、地理注。在树的眼里我也是一棵树,十趾沾地却又不懂得向下扎根的树,终生奔跑操劳却总也高不过层楼的树,甚至越长越矮。今天,我这棵老树倒很想和那些老树谈谈,譬如春华秋实,譬如夏长冬藏,譬如立地顶天,譬如千秋万代。
燕南园是北大园中之园,里边住的俱是“重磅人物”,整个学生时代我都没能进去瞭一眼。
第一次得窥“庐山真面目”,是在毕业26年后,拜访陈岱孙先生。那一阵子,北大的公众人物,是陈岱孙、季羡林。我与季先生相熟,便请他介绍——就是向陈岱孙先生问个好,和他拍个照。哪知找到55号,敲门,无人应。问邻居,说身体不好,住院了。
好赖见识了燕南园,感受了其磁场。
过了若干年,采访侯仁之先生。侯先生住61号,当时虚岁已值百龄,获睹他的丰采,聆听他的嘉言,幸何如之。
去年岁尾,写作《先生之风》,涉及57号前后两任户主江隆基、冯友兰,又来一探究竟。57号已辟为“冯友兰故居”,适逢闭馆,遂隔着围墙瞻仰了那名享士林的三株老松。
今日再来,依旧铁将军把门。
人去楼未空,“三松堂”储满斑驳明灭的光与影,锁犹未锁,有心人往门前一站,自有浓郁的书卷气、博雅气袭面而来。
我是有心人,免不了对围墙内的三株老松又低回了一番,然后迈开大步离去。拐了个弯,正襟危坐的陈岱老,恰在55号院旁等我——那是他的铜像。合影如仪,还有比这更令人满足的吗?
一路走走停停,见到华发苍颜的老者,别有一番故交故知的亲切,他们的目光会主动迎过来,我也会热切地望过去,对上了眼,有人径直问:
“哪一级的?”
“64级。”
“学什么的?”
“日本语。”
“认识吕学德吗?”
“认识,教阿拉伯语的老师。”
又有人搭上话:
“我学过陈信德的科技日语。”
“是吗,陈先生教过我一年。”
“我认识刘振瀛。”
“哦,刘先生教高年级翻译。”
北大很大,北大也很小。
一处交叉路口,西南角竖着一块告示牌:“世上本来有路,停的车多了也就没了路。”我拿笔抄下,觉得这标语新颖,借着鲁迅的名言反过来说,让人见了愣一愣,想一想,这一愣、一想,就多了一番明心见性的顿悟。
未名湖南岸,靠背长椅,右首是我,左首是她。
我读我的《北大人》。
她是游客,江南口音,用手机絮絮叨叨地向家人汇报燕园见闻。
渐渐感到左侧热辣辣的目光,扭头,四目交集。她问:“您这本《北大人》在哪儿买的?”
“校友会赠送,非卖品。”
“太遗憾了,我看到很多人手里拿着这本,以为我也可以买到。”
“你想要?”
“想呀,我儿子今年读高一,他打算考北大。”
“那……你等等。”我掏出笔记本,把刚才读过的两段将来或许用得上的材料,刷刷地抄下。然后,把刊物送给她。
她十分好奇,想知道我抄的是什么。
我翻开《北大人》,在那两段文字下画了波浪线:
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周培源陪同。他提到自己曾经是杨振宁的老师,现在则要向杨振宁学习。毛泽东笑问:“你现在落后了吗?”他欣然回答:“是很落后,后来者居上。”(摘自《缅怀科学巨擘周培源》)
杨辛考察泰山,作《泰山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摘自《缅怀哲学美学大家杨辛》)
但愿她的孩子读到上述钻石般的文字,也会与我一样,心潮逐浪高。
(作者:卞毓方)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