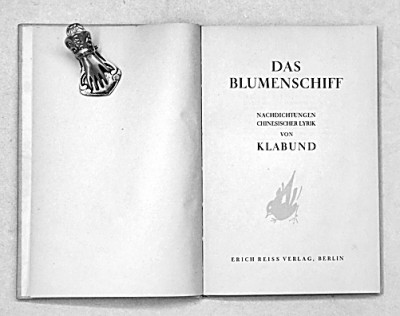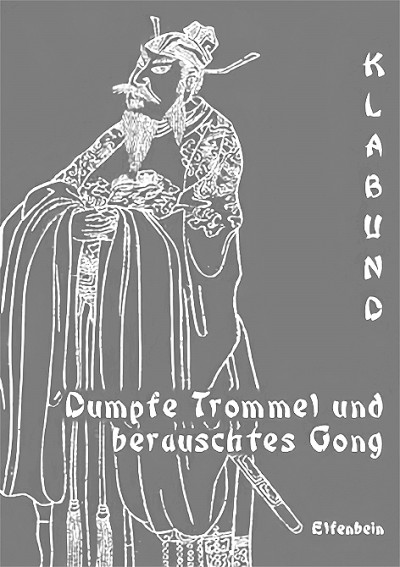扬名于20世纪初的德国作家克拉邦德与中国有着独特的情缘。一方面他是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他又依照个人的理解和艺术趣味改写了大量中国唐诗。表现主义关注内在世界,在心灵同客观的碰撞中聆听回响,追求一种越过表象逼近本质的情感和精神。这微妙地契合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对“意”的侧重。克拉邦德正是以意象和意境为核心,使得中国古代诗歌向西方世界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因为不懂中文,克拉邦德只能选用当时已经通行的德文版或法文版唐诗译本作参照,但克拉邦德对中国文化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还是让他抓到了唐诗表意的精髓,他笔下洋溢出来的表现主义风格又激发出唐诗非语言层面的神秘魅力。
Ⅰ.诗歌意象的“跨国之旅”
克拉邦德的唐诗改写主要汇集在三部诗集当中,分别是以战争诗为主的《紧锣密鼓》,以饮酒诗为主的《李太白》和以抒情诗为主的《花船》。而贯穿这三部诗集的又首先是中国唐诗意象的“跨国之旅”。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强调围绕意象特别是意与象的张力关联来组织作品。在克拉邦德的改写中,相同的意象却在不同的语境中催生了不同的审美意境,也间接实现了不同的主题寄托。
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李白的名篇《清平调(一)》和《静夜思》的改写。
李白的《清平调(一)》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克拉邦德将其改为《即兴诗》:
云朵和衣裳,还有她的脸庞。
芬芳飘散,
这可爱的春天。
如果她站在山上,我便不敢去攀登,
如果她投身月亮,我又会远离,
可爱的春天。
李白诗中的前两句将“云”与“花”全部进行人格化,借物喻人,从而表达美。但克拉邦德却在改写中取消了这种人格化,选用一种意象铺陈的手法,原诗中独立的审美意境,在这里被拆解成了意象群。后两句在克拉邦德的笔下又被直接抒情化,“她”是一个具体的追求对象,前面的意象群都成为对“她”的烘托。
综合整首诗的改写可知,克拉邦德是将李白单纯歌咏“美”的诗凝缩成了一首抒情诗,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把“云”与“花”,“山”与“月”进行表现主义式的简化,抽去其中自带的意味,使之全部面向“她”,以及“我”对“她”的思恋。李白写作中并没有直接指涉出“她”和“我”,因为李白有意构建一种“花”与“人”交融互摄的意境。而且这是一首应制诗,在诗歌传统和当时语境下,李白都不会表露出“她”和观看者“我”(这个“我”可能指皇帝,也可能指作者)的对应关系。中国古典诗歌浑融的语言特色能很好地弥补这种指向的含混,“意”隐藏于“象”之中,不必分别。而德国表现主义则倾向于“意”从“象”中抽离出来,以象铺陈,让意直显。于是我们看到了诗歌意象和指涉由隐到显的微妙变化。这当然是一种大幅度改写,李白原有的那种“花”与“人”交辉的美感在克拉邦德的改写中大大缩水,情味略显干瘪了。
《静夜思》的改写又更加特别,标题就已经被改成《游子从客栈中醒来》,李白的千古名句在克拉邦德的笔下变为:
与往日不同,
我从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光线刺眼。
是霜吗?
一夜之间把地面染白。
抬头,看向闪亮的月光。
低头,想起旅途的终点。
其中最重要的改写是原诗中的明月意象几乎不再有存在感,有的只是一个在观看和思考的“我”。这首诗中没有意象铺陈,而是遵循表现主义的情感本位,将“象”中的“意”全部凝结成一个生活的瞬间,意味被具体化为一个游子的真情实感。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改写则是把“故乡”改成了“旅途目的地”(或者译为“漫游的目的地”)。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就是让文本缺失了一个情绪落点,原本单纯的思乡之情变成了一种不知去往何处的空虚、落寞。
Ⅱ.诗仙李白之“醉”
克拉邦德对李白的推崇已经无须再多加强调。除了直接以《李太白》为名编纂诗集,即使是在以战争诗为主体的《紧锣密鼓》中,30首诗也收录了李白的12首。而克拉邦德对李白的改写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表现主义的风格转换中将李白的恣意洒脱同酒神精神联系到了一起。而“诗仙”在异域的叙说当中也变成了“永远圣洁的流浪者”。可以说“诗仙”与“流浪者”的身份转换意味着中西方对于人格与命运的不同侧重。
李白的《悲歌行》写道:“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一个独立且孤傲、狂放且富于悲剧气息的人格跃然纸上。克拉邦德延续了诗中悲的基调,但个体郁郁不得志的悲上升到了集体命运的悲。他改写后的《忧愁之歌》同德国传统中的悲剧精神相呼应。
李白原诗写道:“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这几句诗在克拉邦德笔下完全变换了样貌:
天,从来不朽。又将一半的永恒赠予大地。
而我们,又能享受多少金钱和美酒?
一百年的时间啊,很少。一百年的时间啊,很多。
生死,才是人的唯一目标。
一种抛金洒银的豪放恣肆变成了追问,而为李白所淡忘的生死却又在克拉邦德的笔下化作深深的慨叹。和李白的原诗相比,克拉邦德要收敛很多。从主旨上看,《忧愁之歌》将“醉”的叙说从人格抬升到命运。李白将“悲”化在洒脱轻狂之中,改写之作却让这种悲逐层显露。天空与大地是命运的背景,时间的流逝是命运的必然。追问生死将人生意义转化为选择的问题,而狄俄尼索斯精神或者说酒神精神,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自古希腊伊始逐渐积淀而来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其本质是“从本性中升起的那种迷人陶醉”。李白的饮酒诗与酒神精神的呼应正在于对“醉”的沉迷,以一种迷狂之际的大欣喜来实现个体意志的跃进。李白在《悲歌行》的结尾还是认为“还需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书生”,这是一种现世的自我超越,最后落脚于现实功业的建立。中国诗人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感,他们所关注的人生价值多指向现实生活,即使李白也不例外,在“醉”的迷狂背后,始终隐藏着一双现实之眼。而西方酒神精神却经由身体和意志通往悲剧,通往大喜与大悲的交汇。我们可以说,李白的“醉”始终以现实社会为舞台,而克拉邦德的改写则将现实关怀完全化为个体精神的独舞。
克拉邦德对李白的改写俨然是将李白诗歌中与酒神精神相默契的那部分抽取了出来,将李白直接具体的人生追问抽象化,也将李白作为“谪仙人”的身份悲剧化为“流浪者”。这是表现主义对本质的执着,即任何具体的人生呼吁背后都同有一个内核,李白的具体性是仙与酒,李白背后的内核则被解读为酒神的悲剧之音,是生和死,是沉重的命运。
Ⅲ.面向世界的中国慰藉
20世纪初期的德国,受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一战战败的影响,物质主义盛行,虚无主义也十分突出。文化领域亟须一种来自异域的文化给养实现面向社会的精神慰藉。克拉邦德运用表现主义的方式改写中国唐诗正是要实现这样的慰藉,他所致力的是在改写当中凸显中国精神的内在,使西方社会得以直观。其典型的体现有两点:
其一是家国-人性观。克拉邦德本人也曾受德意志旧有的民族主义传统影响,讴歌战争和民族革命,他甚至报名从军参与一战,只是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而后来受到中国诗歌影响的他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好战青年”逐渐变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在他的诗歌改写中,家国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比如对杜甫《石壕吏》的改写,原诗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诗中有无奈,也流露出对战争本身的愤恨。克拉邦德却将这一句改写为:“如果您要我牺牲自己,我愿意牺牲,愿意为士兵做饭,愿意为指挥员服务。”杜甫诗中的“老妪”因无奈主动提出从军,而克拉邦德则突出了“您”的意志,这个“您”的呈现,将写作重心从老妇的无奈转向权力对个体的强制、胁迫,这深刻地展现了战争背后的家国与个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其二是生命-自然观。克拉邦德对中国精神最核心的把握是源自道家的自然观,倦怠于当时欧洲社会的物欲横流,他在道家顺其自然的表达中意识到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统一。生命归于本性也就是归于自然。杜甫的名诗《曲江二首(一)》写道: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杜甫把俗尘的名利划归于“物理”也即自然界的变化万殊之中,将人世的流俗沉浸在春花荣萎的更替之中,以天地之大衬托浮生之小,以时空之漫长衬托羁绊之短暂。克拉邦德将这首诗改为《曲江之上》:
我从苍白的小舟四下望去,
向下看见水中的荒野,
芦苇和云雾之间,
涌起月亮的金影。
爱人啊,她在我的灵魂中
灿烂地闪烁。
白昼,日光让月光暗淡,
夜里,月光却分外耀眼。
克拉邦德的改写抓住了原诗的精神内核也足够曼妙动人,全诗都在讲述“物”的触动,都在叙说自然如何拨动人的心弦。区别在于,杜甫的诗歌有着较为深沉的历史沧桑感,而在克拉邦德的改写里这种历史沧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爱人”成了描写中心,诗歌强调个人的情与爱、得与失如何生于自然,又如何融于自然。
唐诗的异域改写释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这背后也是无数诗人真切的体验和积淀。克拉邦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生硬引介,而是尽可能地触碰诗人的体验和积淀,也把自己带入其中,因为共情,所以言情。
(作者:于萍,系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