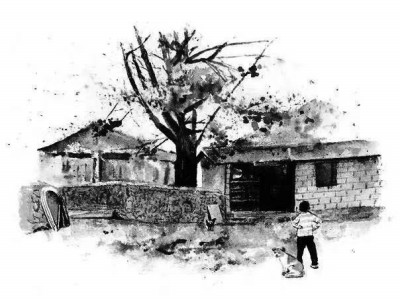【当代文学现场脉动观察】
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全面融入时代发展的壮阔进程,继承深厚而悠久的传统文脉,与世界文学优秀成果交流互鉴,是一个富有魅力和勃勃生机的场域,也是一个不断涌现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课题的场域。本版从今日起开辟《当代文学现场脉动观察》栏目,力求发掘文学现场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前沿性的热门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发展风貌。
在当下,关于当代文学写作“地方性叙事”的研讨一下子“火”了起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等成为这股潮流的标志。相关的概念界定、作家和文本划分,成为研讨会和杂志版面的焦点,热度居高不下。对此,一方面,我们为文学写作与研究新现象的出现,油然生发出参与建构的激情与冲动;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进入“冷”思考的层面,回溯、检视其中深层的学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地方性写作和研究走得更远、更扎实,从而更好地审视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浙派写作”之“新”究竟在哪里?是否有着新的叙事理念、审美思维和叙事新气象?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在文本中到底建立起什么样的文学精神?新“地方性叙事”各自有着什么样的“出世”路径和样貌?其概念界定的学理性何在,有无合法性?其总体热度缘何而起?它生发了什么,遮蔽了什么,接续的走向又该如何?以上一系列问题都亟待爬梳、辨析与审视。
当下地方性写作呈现新的面貌
近几年来,“新东北文学”或“新东北作家群”特别活跃。辽宁的班宇、双雪涛、郑执,稍晚出场的黑龙江的杨知寒,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至少近十几年东北文学创作相对沉寂、沉闷的状态。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为东北文坛乃至当代中国小说界带来新的活力。仔细探究,他们在叙事伦理层面,具有较新的文学理念和叙事的自觉性、执着性,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增添了新的元素,进而也成为“东北叙事”新的生长点。
在文学的意义上,“东北”作为文学书写的“地界”,并非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地方”概念。对于“新东北作家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更强调其“东北往事”叙事的独特视角,认为双雪涛和班宇们所讲述的“是一个迟到的故事”:以20世纪90年代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他们的后代来讲述。因此,这就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主要是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辈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新东北文学”有着更清晰的叙事伦理和切入生活的新角度。
相对于“新东北作家群”或“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和“新浙派”这两个概念,其所指和涵盖范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
“新南方写作”这个提法或概念,最早出现在广东的一些文学研讨会上和批评家们的文章中。“新南方写作”的叙事“地理”,被有些倡导者认定为海南、福建、广西、广东,还包括香港和澳门,并进一步辐射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曾被称为“南洋”的区域,尤其强调其主要特质是“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被“圈定”的“新南方写作”的作家主要有黄锦树、黎紫书、葛亮、林森、朱山坡、王威廉、陈崇正、陈春成、林棹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培浩认为:“新南方代表着崭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与人类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新南方写作”,尚有诸多“还没有来得及”考察和认定的因素,尚未树立起它的标志性作家和代表性文本,甚至还来不及梳理能够被普遍认可的“新南方写作”的基本特点和美学风貌。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似乎主要在于以“理论先行”来引领“新南方”区域作家的写作,提示他们更加关注地方性现实、历史和记忆,彰显地域写作的独特审美个性和精神内涵。因此,“新南方写作”并非一个总结性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生长性、提示性甚至催生性的整体写作期待。这种文学现象,颇像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小说”“新写实主义”,具有理论、概念先行的特点,目的在于有意识引导作家不断努力,积极生产出创新性文本。《青年文学》杂志主编张菁认为,“新南方写作”其实早已存在,只是以往未能很好地总结,这源于它自身“地域特色”和“整体性”并不是特别鲜明的缘故。实际上,在“南方以南”,始终有诸多的作家在耕耘,不断呈现出新的气象与生机,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韩少功、刘斯奋、林白、东西、凡一平等。其中部分作家是从其他省份迁居过来的,在他们身上我们所期望见到的新南方的“南方”性并不强健,且并未形成标识。也有部分作家积极汇入“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的洪流并成为主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文学写作中的视域,已超越一般的乡土意义,上升到民族性、人性、人类终极思考的境界,从而成为乡土中国乃至人类的镜像与符号。因此,我们说地域性或地方性写作,最终都是要越过叙事边界,通向民族性与世界性,呈现出具有个性品质、超越性精神内涵的文本面貌和美学维度。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不失贴近叙事地域的地气,而且拥有世界性格局和叙事气魄。
对于“新浙派”,《江南》杂志在2023年首次提出,主编在“邀语”中并未阐释其内涵,而是列出一长串从50后到90后的浙江小说家名单。青年评论家行超认为,当下提出“新浙派”这个概念,并不在于创造出一种浙江文学新风貌,而在于呼唤浙江出现大批颇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并在这个时期内形成互相砥砺、彼此促进的写作新生态。其实,“新浙派”同样是一种召唤或“聚集”,号召更多作家创作更多更好、区别于其他地域作家、充满异质性的作品,形成独有的“浙派”风格。由此可见,“新浙派”的提出,并不是对作家叙事风格和叙事伦理的统一,而是试图寻求建立几代浙江籍作家的精神“共同体”。
比较而言,相对于“新南方写作”“新浙派”,“新东北文学”或“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命名、创作实绩显得更为成熟。
一位作家审美维度的建立,无法离开他所处的地域、地理和文化环境
“新东北作家群”“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和“新浙派”这些较为难以界定的概念,其实还涉及南北文化的差异和风貌。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尤其关于“南学北学”“诗眼文心”等问题,在近现代就有许多学者有过充分的论述。如果从文学写作发生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更需要注重从文化、文学的传统渊源,人文地理的沿革方位,以及言与思的品质等诸多方面入手,沉潜到文学叙事的内部结构。其中最具个性的文学魅力在于,作家的写作中呈现出的语言气质、审美想象形态和与之相映的美学风范。这种气质和风范,也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在底色和基调,进而形成各自别具风貌的文学叙事。
或许,我们以往都是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或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命名泛地方化、地域化,过度强调“地方性”因素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作家主体写作的个性和自主性。
作家写作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常常体现在他们的地域性和地缘愿景,这是作家叙事的地理基点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它链接着叙事主体的写作气质和写作风格。地缘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写作者不同的审美选择,也就决定了他在审视存在世界时,如何发掘出隐藏于地理与时间背后的规则。就是说,一位作家审美维度的建立,的确无法离开他所处的地域、地理和文化环境。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显然,地域性对于作家的个性形成和塑造至关重要。对写作而言,地域性经验可能会构成叙事的源头性力量。任何一个人从他出生开始直到生命的终结,无不带有其出生地和成长地的印记。作家的人生“出发地”,往往就是他写作的“回返地”。对作家而言,地域性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概念,其中独特的地理风貌、世情习俗、历史、现实和文化积淀,已经融入他的生命肌理之中,成为滋养个体生命与写作生命的精神空间。而作家对这个精神空间的感悟,就是对世界、存在深度的体认,具有个性化的、深层的温度和气息。
地域性可能会给作家带来某些尴尬和制约
空间作为地域性的显现方式,在宿命般地馈赠给作家丰厚写作资源的同时,也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作家的个性优势和审美独特性。“地域性”或“地方性”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作家以自信,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写作的自由。这是一个两难的悖论性问题。
无论是“新东北文学”,还是“新南方写作”“新浙派”,既是作家独特的写作起点,也可能成为惯性叙述的囚笼,使作家沉溺于曾经的“乡土”。当然,也可能由地方性通达世界性,成为想象的“风之子”,这些都需要在对作家的具体创作和文本阐释中进行辨析,进行文学价值判断。
实际上,作家与地域关系的研究早已有之,但为什么现在“地方性写作”会如此之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当下文学界试图调节文学生产方式,推动地方文学的生产,期待召唤出更多优秀作家和杰出作品,并由此引发整个社会对文学更大的关注。这些有助于作家以中国经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有助于文学的“破圈”。同时,就文学研究而言,地方性叙事作为一种方法,为不断拓展研究视域增加了新维度。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讨论和研究,倘若没有严格的学理边界,这些论题能否沉淀为一个共识性的概念?是否会引发同质性写作的滥觞?甚或,能否真的构成新的叙事原则的崛起?总之,将文学叙事的“地方性”及其阅读、阐释,深植于当代生活和历史的聚合点,已经成为我们把握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要坐标。
(作者:张学昕,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