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对时间的敏感,像一个诗人,甚至超过一个诗人。他在论述《红楼梦》时,说《红楼梦》的魅力在于林黛玉永远是13岁。文学给了人物不老的时间,也给了读者永远年轻的林黛玉。1934年出生的王蒙,从物理时间来计算已经年近九旬,但他的小说创作丝毫没有老态,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爆发力,笔墨还是19岁写《青春万岁》时的热烈、奔放和激情。
时间的金线被王蒙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而时间的金线也将王蒙编织为一个童话老人。王蒙小说里的时间也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变幻着不同的意象。纵向来看,他的作品像镜子一样映射着时代的进程、历史的变迁,是一部辉煌的史诗。横向来看,他的小说的时间又像水流一样流淌着心灵的波澜,还有一些作品里的时间飘浮飞翔,云一样轻盈,云一样变幻莫测、聚散飘忽,形态如风,穿越时空和心灵。
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同步
王蒙对时间酷爱和敏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就是以时间来命名的。这部带有处女作性质的小说迟到了多年才出版,虽然沉睡多年,但丝毫没有被湮没光芒,直到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这是一部记录青年学生的长篇小说,写共和国成立之后热情似火的生活。这又是一部关于时间的青春文本。小说开头的序诗这样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青春”是时间,表示年轻;“万岁”是时间,表示古老。青春是美好的,也是稍纵即逝的,王蒙希望它永不消逝。青春是短暂的,但又是长久的,短暂在于人生易老天难老,长久在于青春永远生长,个人的青春如烟云一样飘过,但新的青春又再度生长,所以“青春万岁”。
不同的时间观,有时候就是不同的世界观,当然世界观也会因为时间而变化。时间的长度在物理上也许是一致的,但时间的质量不一样。有的时间因历史变化而变得厚重,有的时间则显得轻飘飘的。王蒙从创作《青春万岁》到现在为止,70年间创作的总字数超过2600万字。这样悠久的时间长度和庞大的体量,在当代作家中可谓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作家的生命是一种时间长度,这种长度能不能转换成创作长度也因人而异。王蒙70年的创作生涯,留下了共和国历史前行的足迹,通过时间塑造了历史的形象,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他的作品也成为共和国历史的镜像。
王蒙的小说具有广阔的时空,横跨三个世纪之远,空间从河北南皮乡村到北京四合院,从新疆到欧美大陆,再到中国东南部工业园,世界之开阔和小山坳之逼仄,他都有精致地描绘。在题材上,从革命岁月到改革开放的场景,从共和国第一代中学生的青春到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婚恋,从北京胡同里的旧式家庭生存状态到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态,从京郊农民的悲欢到球星、名医的奇遇等,都在王蒙不同时期的作品里得到体现。如此壮大、宏阔的历史舞台,王蒙以时间巨笔书写了人间万象。
物理时间在王蒙作品里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文本外部的时间历程,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青春万岁》《这边风景》《春之声》《蝴蝶》《相见时难》《青狐》《尴尬风流》《仉仉》《女神》《笑的风》《霞满天》等,如果把王蒙这些作品排列起来,会发现是一个编年史的结构。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的内部时间,这就是王蒙的写作依照着大自然的时间顺序,包括但不仅限于故事和情节发展的时间,小说人物的成长所需时间、人生经历时间等。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情节发展时间,上班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他预备了半天的提纲,和厂组织委员魏鹤鸣只谈了五分钟就用光了,这使他很窘。“第四天”“五分钟”都是典型的物理时间。《这边风景》《霞满天》都是由物理时间支撑起小说的基本骨架。
这种物理时间还表现在王蒙的写作时态上。他是一个回忆性作家,也是一个即时性写作的作家。他的一系列小说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现场直播”,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同步,他和小说拥有了相同的物理时间,小说和生活在时间上是重合的。
文学界曾经流行过审美距离说,认为作家对生活的反映最好不要近距离地去书写,因为缺少应有的距离,往往容易身在庐山中,不识真面貌。如果过一段时间,事情和人物尘埃落定了,这样写起来更客观和冷静。因而描写当下的生活、反映现实的题材常常成为一些作家的瓶颈,认为沉淀沉淀再写会更好。审美距离说有一定合理性,很多回忆性的小说容易打动人,不仅仅是怀旧的原因,也是由于时间过滤掉那些非文学元素,留下来的记忆带有天然的文学性,所以更容易打动人。即时性的书写一般不被看好,留下的好作品也不多,而王蒙反其道行之,几乎在他的70年创作中时时保持这种即时性书写的热情,青年时期如此,中年也是如此,到了晚年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了。一般说来,老年往往是作家回忆往昔、拒绝现实的阶段,而王蒙依然保持着拥抱当下的生活热情。这种写作的风险在于时过境迁,导致速朽。王蒙与生活同步的写作,不仅当时看了新鲜,过后没有速朽,留下一系列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时间造成的审美距离,对王蒙来说不是问题。
以音乐思维呈现心理时间
“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
这是《春之声》的开头第一句。《春之声》是施特劳斯的名曲,王蒙的小说选择名曲作为小说的题目,足见他对施特劳斯和音乐的热爱。《春之声》和他的《夜的眼》《风筝飘带》《海的梦》,一并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集束手榴弹”。
这篇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在于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或者说没有完整的叙事骨架,而是在音乐声中让文字和情感自由流淌。意识流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有着完整的体系,而王蒙并没有读过“意识流”代表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小说被称为“意识流”感到惊讶。
那么,《春之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这里要回到小说的题目,回到音乐对小说的内在影响。王蒙选择《春之声》作为题目时,决定了整个小说沉浸在音乐的河流之上。音乐靠音符和旋律来构成艺术空间,小说靠语词和叙述来建构世界。《春之声》打通语词和音符、旋律和叙述的界限,形成新的叙事。读这部作品,我们感到音符的跳动和旋律的奔涌,语词转化为音符,叙述成为旋律,而意识流本身的特点就在于记忆的片段化和叙述的情绪化,这与音乐的抽象和自然流动是同构的。
王蒙是一位音乐造诣很深的作家,发达的听觉活动为小说注入另一股真实的情感力量。他说:“声音是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解无存,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有。”王蒙的小说多次以“歌唱”方式来表达,音乐在《春之声》里转化为小说的结构、皮肤、血液、灵性,小说写声音和音乐到了至境,也就和“意识流”的“流”相通了。
其实,王蒙在所谓的意识流小说中使用的是音乐思维。音乐的思维方式是抽象而具体的。抽象在于它用音符叙事,具体在于每个音符又是具体可感的,有自己的音长、音高和音色。音乐通过时间的流动来构成节奏、旋律和腔调,这样的时间是物理性的,一首乐曲的长短可以用时间来计算,而音乐的时间心理性成分会比文学、雕塑、绘画大得多。文学的时间在阅读中产生,是通过视觉转化为想象,再转化为形象的。雕塑和绘画的时间是凝固的,视觉和画面的复合形成意象美学。音乐的非视觉化让听者通过心理想象来产生美的感受。音乐的叙述性借助音符流动和旋律生成特殊的心理时间。
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相互交织
如果说物理时间要尊重客观、显性的时间问题,那么心理时间则是隐形、主观的。心理时间随着人物情节的走向而延伸,或许大于物理时间,或许小于物理时间,总之无法和物理时间完全等同。物理时间遵循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心理时间更在意人的感觉。这种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交织在王蒙的小说中尤为明显,因而形成有别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第三时间,物理学称之为量子时间,而我习惯称之为云叙述。云叙述的特点在于打破叙述的时间和视角,打通人称的壁垒,由定点叙述转化为散点叙述,空间可以转化为时间,时间也可以转化为空间。
王蒙在一些小说中有意识地淡化时间的存在。比如在《杂色》中,他虽然写了具体的时间,精确到年月日,但读完《杂色》之后你会发现小说里的时间几乎是凝固的,时间对曹千里和那匹老马没有意义。《杂色》的叙述已经呈现出一种云叙述的状态。云叙述的特点就是叙述的起点和终点不明确,叙述的时间、空间也不明确。云的特点是移动的,变化多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种云叙述在《闷与狂》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部作品彻底弥合了时空的界限,叙述者也被叙述者的界限打破了。
在《闷与狂》中,作家已处于一种追逐时间的状态。他在追逐历史,历史也在追逐他;他在追逐现实,现实也在追逐他。“我常常陷入一种胡思乱想或者准梦境: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追逐一个影子。两个影子拼命地追赶我。或者是他们锲而不舍地追逐我,以为我是阴影。”这两个影子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历史是现实的影子,而影子又是昨天的现实。在《闷与狂》中,历史和现实纠结着,像两个影子,互相拥抱又互相离异,朝着同一个方向,又向着不同的方向。历史与现实的无穷纠结,在王蒙小说里尴尬而又潇洒地首尾交接,剪不断理还乱。王蒙曾经试图整理过这样的纠结,但发现旧的纠结尚未了结,新的纠结又源源不断地涌来。这种纠缠是时间的纠缠,也是空间的纠缠,最终形成量子时间的纠缠。
文学与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本质上是记忆的倒流、岁月的回放。如何倒流,如何回放,则是由作家的时间观所决定。时间的本质是“存在”,大到宇宙的存在,小到粒子的存在。而人的存在,语言的存在,声音的存在,感觉的存在都是文学孜孜以求的。时间给予王蒙可谓多矣,90年的岁月,70年的写作,让他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而我们穿越这些语词的迷障和叙述的曲径,发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心和不老的灵魂。这是文学的意义。
(作者:王干,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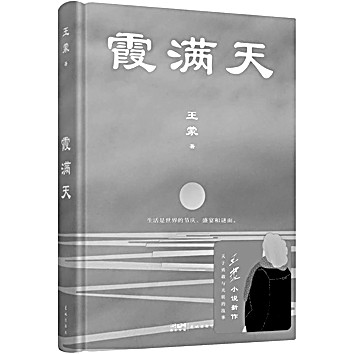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