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151年前,中国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历史走到今天,每年有超过70万人出国留学。2021年,留学归国就业学生第一次超过百万人。成千上万的留学生,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系的纽带,正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回头看一百多年前的留学史,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赴日留学时,在书店立读的一件往事。“立读”就是站在书店书架前浏览。那时我刚走上漫漫的留学日本之路,心态还没调整好。出国前,我在清华大学任讲师,一个月工资134元人民币,而日本书店里的一本小书通常也要几千日元,是我在中国两个月的工资。我觉得这些书太贵了,可又对最新的知识感兴趣,于是,不时到书店立读一两个小时就成了习惯。那一日,忽然看到一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这本摹画几代中国留日学生精神历程的著作,获得过大佛次郎奖,也获得了第四届亚洲太平洋奖。一位和自己同时代的中国人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能在日本出版,并且在日本得了奖,我着实觉得这位作者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那个时代,有一句话压在整个中国学界头顶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不仅是敦煌学,中国在很多重要研究领域都很落后。拿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领域来说,当时最权威的著作就是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那样的时代,严安生先生的著作能够出版并获奖,其影响不仅在学术方面。
我们这一代研究日本的人,都对严先生有一份钦敬之情。
拥抱偶然:
成了教书先生
严先生经常讲,他第一次与日本结缘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严安生1937年11月底出生在武汉。那正是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国民党很多机构迁到了武汉,日本的飞机轰炸也跟过来了,几乎每天都有。母亲怀着严安生挺着大肚子“跑轰炸”,恰好他出生那天日军没有来轰炸。没有空袭,没有警报,没跑防空洞,母亲安安稳稳生下了这个孩子,所以给他起名“安生”。青年时代的严安生曾经觉得“安生”这个名字很不革命,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名字,一直想改。后来听母亲讲了这个过程,就决定不改名字了。严安生,是一个在日军轰炸威胁之下平安出生的人。
严安生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不识字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哥哥回到老家江苏镇江。日子不好过,经济拮据,严安生没有钱读书。幸亏附近一所小学的校长有慈善心,看到这是个聪明孩子,就和严安生的外公约定,如果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在前三名,就可以让他免费读书。靠着好成绩,严安生读完了六年小学。
严安生读六年级那年,赶上解放。他一直都清楚记得,有一天早上一起来,打开门,看到解放军就在巷子里席地而睡,一点儿都没扰民。14岁,严安生考进了南京师大附中。同学们都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添一把柴,很多人都想学理工科。严安生的理想是为祖国建设寻找矿产,就准备报地质系。后来受数学老师影响,他也考虑过报天文专业。1955年前后,学校有一场演讲比赛,因为正好看了一本小说《外交家》,严安生灵机一动,就拿“将来当外交家”这个话题做了个演讲。他没想到,那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演讲。1956年外交学院来南京师大附中招生,校长就推荐说,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的理想是当外交家,口齿也挺好。就这样,严安生被保送到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是日内瓦会议后为培养外交人才而筹建的,到外交学院学外交也是为了国家需要。严先生因为没有英语基础,原本被安排到英语二班(慢班)学习。开学的前一天,住在临时宿舍的十个男孩子相约跑到电影院看一毛钱的学生场。一场电影看完,回来在大食堂围着一个桌子吃饭时,旁边几桌的同学都看他们。原来,那边演电影时,学院这边临时开了个动员会,学院新设立了一个日语班,十个因为看电影不在会场的男孩子,“自动”进了日语班。
我曾问过严先生,一下子进了日语这个小语种专业,心里很不满吧?严先生回答说,没有任何不满,那时的想法是国家需要就是他们的志愿,“所以我们老老实实学”。
那时的外交学院是5年制本科,不过运动很多,一停课就是两三个月甚至一个学期。严先生算了一下,真正在课堂上坐下来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月,所以连初级阶段的日语都没学完。
好在,严先生学习成绩好,1961年留校教书,1962年随日语专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严先生说,他后来的业务都是靠自己学,用的都是当时的政治文献,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选集》。那些文献的日文翻译是一些老日共或者日本战败投降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翻译的,文字非常好。他一条一条对照来学,分出主语、谓语、宾语、修饰语,或者按照中日的语序对照、句型对照、用词对照,“我按照自己的方法,逐渐把日语常用的句型、句法,包括常用的长修饰句、复句,都掌握了。有了这个本事,后来教书就不难了。”那时,学校开始要求用日语讲课,怎么讲呢?严先生的办法是,在每学期开学前把课本里的范文全背下来,只要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就容易前后关联,把课文讲活。再往后,严先生就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借阅日文小说。大量的文学阅读,让他渐渐对日文的世界有了更深领悟。
严先生说:“人生充满了偶然,我拥抱命运的偶然。”日语越来越流利,语言越教越好,他成了一个极好的日语教师。可慢慢地,伴随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他感到,只懂得语言不过是“口舌之徒”,要真正教好外语,需要追求语言之上的东西。
中年留学:
不满足的半条命
2021年,严先生84岁。他几次讲到自己84岁的人生可以从42岁劈成两半。42岁以前是一个人,一个单纯教日语的“口舌之徒”,42岁以后是另一个人,知道要做学问。
1979年,严先生通过考试,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去日本的留学生。当时,教育部选派了150多人去日本,理工科尤其工科的学生最多,学日语的只有十个人。
我曾好奇地问过严先生,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您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对于当时中日经济发展的差距,严先生用了“天地之间”这个词来形容。那时羽田机场已经落成,第一条跑道已经飞飞机了。出了机场一路看,首先高速公路、交通就刺激你,进入东京一片高楼大厦。一路震撼是很大的,心里会问“为什么”。日本的发达让严安生陷入沉思。从那时候开始,他一直仰视的鲁迅、郭沫若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成为自己的留学前辈,这些前辈当年从事文学活动的精神历程忽然被严先生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鲁迅、郭沫若等先辈也是在国家落后的时候出国留学,他们也曾经历过文明冲击带来的震撼、混乱,开始逐步思考。两代人的感受在这时结合起来了,但严先生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命运转换。
年过四十,有了留学的机会,严安生的想法是要把日语教得更好,所以想学语言学,也报了东京大学语言学专业。可惜东京大学本乡校区那边的语言学专业留学生招满额了,他很偶然地被转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从此和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这个专业方向结了缘。
在东京大学,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知识养分。当时,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主任佐伯彰一是留美的,其他骨干教师也大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深受比较文学领域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影响。其中芳贺彻等三四个学者想建立东亚的比较文学,设想至少在起点上有中国、韩国、日本学者共同对东方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这些学者在日本比较文学界形成了一种势力,特点既不是典籍的思想研究,也不是历史年表式的平行分析研究,而是注重对人的研究。他们专门研究留学问题,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日本人海外的留学生活,研究文化冲突、文明冲击,讨论文明落差给东亚地区的人们造成的影响,带来的精神变化,以及知识结构如何转变。还有一些学者发起文化摩擦研究会,专门探讨不同文化各方面的摩擦,包括观点、思想观念方面的摩擦,也包括生活小事上的摩擦。严先生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来自中国的这位中年教员,就坐在那里静静听着一群青年人切磋琢磨,思路有点跟不上,但很受刺激。他慢慢认识到,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可以具体而微的。
两年修业期满归国,严安生已经非复吴下阿蒙。他就像一块神奇的海绵吸满了知识之水——在驹场,他看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师生如何研究和分析明治时期日本留学生的海外经历,看到了他们如何通过文化摩擦的细节审视和分析人的精神变化。更重要的是那缕漂浮在智慧之水上的灵气——他从自己的留学生活中,体会到了曾在日本留学的先辈们的精神世界,和他们发生了深刻的精神共鸣。严安生研究留学日本的先辈们的精神史,一个巨大的动因就是来自现实生活触动而获得的这种共情,“我自己遇到的苦恼让我一下感受到了留学先辈的苦恼,一种力量推动我必须要追踪先辈们的精神世界”。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灵魂震撼、精神冲击和思想探索表达出来,是他从事留学生精神史研究的动力。一个单纯教日语的“口舌之徒”,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学问之路。
从1979年赴日留学起,严安生开始关注留日学生的精神世界。1981年归国后,他一边教书,一边不断深化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他跑遍了北京城内的图书馆寻找资料。柏林寺那边的北京图书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刊物堆在一个大房间里,读者可以直接进去看。雍和宫对面是国子监,那时是首都图书馆,两边的厢房里有不少他用得上的旧书。东厂胡同一号,原来是日本人搞的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也很丰富。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中央和地方的文史资料,汇集了不少辛亥老人的回忆,这些辛亥老人是历史当事人,他们写的辛亥前后的历史,材料丰富,鲜活生动。用了十年时间,严安生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于1989年获得了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后来的《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
时空坐标:
寻绎历史深处的逻辑
近代中国人的留学,原动力来自中国的衰败与落后,特别是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更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作为起点。《马关条约》的签订,无情地打碎了清朝天朝大国的美梦。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国人震惊,呼吁民族救亡和变法维新。变,成为时代最强音。要变,就需要变的目标和模板,明治维新后骤然强大的日本,就成了最好的鹄的。“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回绕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共同问题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为什么会突然强大起来?强大到能够战胜清王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日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这经验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大规模的留日运动由是发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现象。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统计,1898年留日人数为77人,1899年增加到143人,1901年留日学生266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到1905年,留日学生已经达到8000人之众。这个数字,超过当时中国赴世界其他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这些留学生,有兄弟留日的,有父子留日的,有夫妇留日的,有全家留日的,甚至有全族留日的。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记其1903年3月离别东京之际:“是行也,留两子、一妇、一女婿、三外孙于东京,远别能无黯然?然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渐渐进步……”
在这样大规模的留学运动中,留日学生们经历了怎样的精神过程?摹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这么多赴日留学者的精神世界,谈何容易。喜欢逻辑思维的严安生,采取了画时空坐标的做法。江苏留日学生在《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中讲到,留学生们“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怀抱强烈的爱国激情,把世界的发展介绍到中国,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为祖国尽一份心力,这可以说是20世纪初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也是严安生考察留学生们精神世界的原点和基点。确定了这个基点,他开始借用坐标线恢复历史的时空。留日运动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在那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中日两国的历史也不断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严先生参照两国的历史发展划出了坐标线,这是立体的往复线:
甲午战败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受此震惊,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的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我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
我曾经向严先生请教,您这一生的研究中对哪一部分最有心得?严先生回答说:从事留日精神史研究,体会最深的就是历史逻辑的重要性。
严安生认为,历史有历史的现场,现场就有现场的逻辑。他没有系统学习过历史学,一旦进入历史研究中,逻辑就成了他在历史深处探索最重要的方法。他重视逻辑,反对任何单纯罗列史实的叙事。比如,他认为留日运动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很重要,在分析大规模留学运动的起点时,他提出,这一运动的动力源从一开始就来自中国和日本两个方向。
对于留日运动,1898年意义绝大。那是中国激烈变革的年代,1897年年底,严译《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带进中国,冲击巨大。“适者生存”,不适者亡国灭种,这让当时中国的精英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般认为,为推动国人留日,张之洞于1898年3月发表了《劝学篇》,这是中国人留日运动最重要的开端。此后,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制定《游学日本章程》,上奏皇帝。6月1日,军机处奏上具体方案,由总理衙门复奏,派遣学生留日由是成为国策。前有张之洞等人舆论上的倡导,后有清朝政府政策上的积极推动,遂出现了大规模中国学人留日运动。但严安生通过研究比对,指出历史的另一条线索——在张之洞《劝学篇》发表之前,1898年1月,日本军部派宇都宫等三人到张之洞处游说,鼓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好处,并表达他们愿意尽力提供帮助的愿望,这正是促使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重要契机。而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人业已将俄国视为首要敌人,动作最迅速的日本军方已经开始尝试拉拢中国人共同对付俄国。来自日本的思想灌输和主动拉拢,是近代留日运动另一个重要原动力。
近代的东亚是一个风起云涌变化激烈的年代。几年之间,留日运动的核心目标发生转变,留日学生活动的历史逻辑也因之发生变动。同是留学生,鲁迅这一代是科举制度体制之下的最后一代,按日本学者的说法,他们属于末代科举教育下最后一代政治青年,有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在心里。而郭沫若、郁达夫这一代留学生出国前受过初步的新学教育,在中国,他们是第一代新知识青年。他们遭遇的大正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日本,也和明治日本有着根本不同。严安生就是这样依照历史的坐标系一步步还原中国近现代留学的历史,进入鲁迅、郭沫若等留学生思想产生的话语场景中的。在研究中,严安生特别重视文化摩擦,注重通过留学生经历的历史细节审视和分析人的精神变化。他将笔触伸进日俄战争、万国博览会上“人类馆事件”以及课堂、食堂、澡堂、宿舍等留学生的生活空间,通过现场找出历史的逻辑所在,成功再现了一部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精神生活的历史。
蓦然回首:
留学究竟是什么
从最早的公派留学算起,151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已经可以静下心来思考,留学究竟是什么?
从大的方面说,留学生是连接起中国与世界精神文化传输的纽带。然而到了一个个具体的留学生那里,留学又是一个人的漂泊,离开了呵护自己的亲人,告别了熟悉的父母之邦,孤身远行,走进完全不同的语言,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陌生的生活。留学生们要经历陌生人海中的孤独,夜深时的寂寞和凄惶,要承受来自不同族群他者挑剔的目光,同时也会遭遇各种异域的美,看到不同文化的风景,打开一扇扇能透进霓虹七彩的天窗。151年中国人留学的精神历程,有千种滋味,有万种风光。
直到今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依旧走在留学的道路上。151年后的留学,回首家园,是否依旧满怀故国情思,满是落寞惆怅?瞩望远方,是否依旧满怀豪情,将大风高唱?
回望20世纪的中国历史,活跃其间的许多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他们有的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中国政治的重要推动者,有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的骨干力量,有的领军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推动中国文化转型起到重要作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致力于科学与教育,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在陈述同一个事实,那就是留日学生是推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留日学生能在众多领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并非偶然。严先生在回忆他这一代人的留学生活时曾感慨,自己和鲁迅那一代人一样,都是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留学的。落后这一事实给留学生个人带来巨大的震动和冲击,激起他们奋起直追的勇气。
如果我们把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看成第一次浪潮,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大批留学日本比喻成留日的第二次浪潮,那么当第一次浪潮消散,尘埃落定后,我们看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标志性人物;经历岁月淘洗,今天,第二次浪潮也已趋于沉寂,我们同样看到一批优秀学者沉淀下来。凭借在留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严安生先生注定将成为第二代留日学人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作者:刘晓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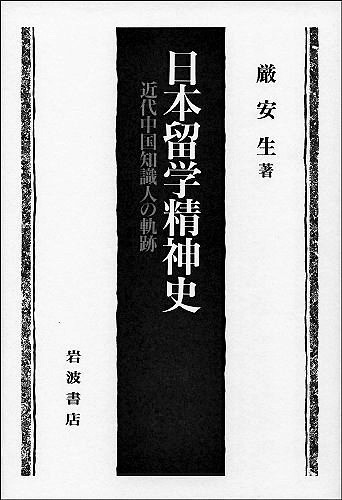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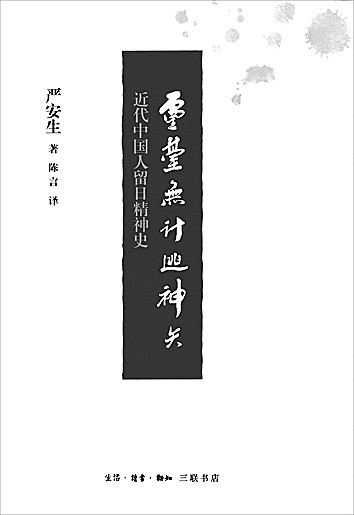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