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数来,2022年出版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已经是我的第68本书了。可以说,这算是我的专著中的重头货。以几十年的研究经历为根基,我深以为,书写思想史,最需要创新的思想。只有创新,才能提出新问题、新思路,与过去常规的问题和思路形成对撞,由读思想史激发新思想。而这一点,正是我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基本追求。
一
思想史植根于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脱离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的所谓思想史,只不过是概念的演绎,变成一堆空空洞洞的纸片。文明史可以使思想史底蕴深厚,生动活泼。我讲思想史,就因为它囊括了综合性的文明观照、先秦诸子发生学、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间的位移、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法论,展开了既有本体性、又有开放性的宏观视野,形成一种深入文明史的思想史。
了解什么是中国思想,然后才能跟踪思想运行的轨迹。在思想文化综论中,我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三原则:一是在原本比较重视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三是从文献的验证中,深入到文化意义的透视。其中有两条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另一曰追问重复。由此所重绘的文学地图,是一个现代东方大国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升级版的文化身份证。
为什么进而提出“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命题?这是为了使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觉”。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追问:第一,中华文化从何而来?第二,中华文化根本何在?第三,中华文化有何种基本内涵?第四,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千古不灭的生命力?第五,中华文化如何焕发与时俱进的现代原创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五问”,它将成为我们创造一代大国学术的逻辑起点。在这里,我们探讨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性、中华文化的原创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丰沛性和中华民族文化景观的丰美性,从而自觉地形成了文化的五纲目。
二
本根探索,是根本所在。在探讨先秦诸子文化本根的时候,既概括地展示了先秦诸子发生学,又重点考究了孔子赴洛阳问礼于老子的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以及考究了荀子与韩非、李斯师徒会的先秦诸子的闭幕式,对文化血脉进行返本还原,展示了春秋战国300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形态。然后考察了《论语》早期三加一次编纂(《齐论语》)之秘密,对齐子贡进行生命解读,对《孙子兵法》进行生命解读,对庄子思想的国族文化基因作出探赜索隐,最终落脚到诸子是怎么炼成的,从而真实深入地勾勒出中国文化的经学、子学脉络。经学、子学脉络,是中国文化精神发生学上的本原性脉络。
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因而,要进一步总览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就此,我着重探讨了司马迁的“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陶渊明的菊、松、酒的人生三维境界”“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以及“苏轼与士人文化范式”。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可以从中寻找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某些原型。比如:讲尊师,也许想到张良的圯桥拾履;讲重才,也许想到萧何追韩信;讲忍耐,可以想到韩信的胯下之辱;讲信义,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诺千金。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国。勾践的卧薪尝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范蠡的扁舟五湖,蕴含着何等的意志、决心、气节、豪情和潇洒。再如焚书坑儒、指鹿为马、项庄舞剑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包含着多少残酷的权术和悲哀的命运。人们寻找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多从经子典籍着眼,岂不知史书也以历史的残迹在编织国民精神的网络。所以,《史记》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影响,除了《论语》记录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部书,其影响不在老、庄、孟、荀之下。从整个民族来说,在铸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史记》所讲述的一系列“中国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远的作用。
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觉醒和个性自由的时代。文学觉醒和个性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陶渊明。文学自觉浪潮迭起,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张“文以气为主”。继之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新境界,当时有人说“谢诗如芙蓉出水”。再继之就是陶渊明诗文共140多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70次之多,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陶渊明以大思想家的姿态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还有一部《世说新语》彰显着魏晋风流,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行为,栖逸、任诞、简傲等性格,都有生动的描写。鲁迅称赞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是“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在这股潮流中,陶渊明几乎成了中国一个士人文化的品牌。凡是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他的《桃花源记》,知道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隐士、田园文学的奠基者。有人或许还能吟得出他的一两句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讲得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渊明诗的价值,植根于诗而超越了诗,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采菊东篱、安逸田园、清风明月的文化,并以此进入中国文明史。
《史记》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史脉,李白、杜甫则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诗脉。史和诗,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脉络所在。通过探讨“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从诗仙和诗圣的笔下,我发现了盛唐魄力与诗学新境界,他们以新的时代姿态,彰显的是《毛诗序》的诗学精神:“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苏轼在唐诗丰神之后创立宋诗格调,苏东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以文学上的旷世大才,代表着一种以才情浩荡,诗、文、词、书、画兼通,而又意趣旷达为标志的士人文化形态。苏诗真率大气,才情浩荡,洋溢着忧患和理趣;东坡词采取“以诗为词”的策略,借用一种处在文学正宗地位的优势文体,驾轻就熟地开发出当时还有“艳科末技”之讥的词体的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他用诗解放了词,从而使以往多用于应歌侑酒的歌伎唱词,在根本上转化为士大夫文人抒情言志的新诗体。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书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句话经典地总结了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元明清以降,思想文化向民间位移,小说戏曲中所蕴含的民间思想文化极其复杂丰富,道教信仰、“三国气”、“水浒气”,弥漫社会和江湖,因此有必要在新诠释学视角下剖析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尤其是《红楼梦》文化的“天书—人书”之精华。宋代勾栏瓦舍的说书四家,“说三分”衍化出《三国演义》,“说铁骑儿”衍化出《水浒传》,“说经”衍化出《西游记》,“说小说”衍化出《金瓶梅》。四大奇书实际上是反映中国民间精神文化的一种史诗性作品,宋元明800年其实是我们的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礼乐文明强烈碰撞的800年。某种程度上说,《三国演义》把民间的精神原型仪式化了。由于对民间精神原型作了仪式化的处理,《三国演义》的影响往往超过了我们的很多长篇小说。近世以来的戏曲里面留下的剧目,三国是最多的,像空城计、单刀会、失街亭、斩马谡、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等,都是从《三国演义》里面来的。《三国演义》以一种仪式化了的民间心理形态,深刻模塑了中国民间的价值观和生存智慧。另一种角度看,《三国演义》是一种智谋书。俗话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又有“事后诸葛亮”“诸葛亮的锦囊妙计”,都是把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来看待的。《水浒传》更称得上是一种民心、民气和民间文化的结晶。《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热情奔放、口若悬河地讲一个很古老又带有传奇色彩的梦。而《金瓶梅》却是以一种冷静、清醒,有时候带有几分轻蔑和嘲笑的眼光,由书斋里面看市井,看那个说书人的周围的世界。四大奇书,把我们中国宋元明这三代民族生存形态、民间文化心理、文人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思,写得非常深入。小说戏曲的思想文化史,揭示了不同于正统诗文而更加连通地气的思想文化潮流。
三
思想文化史除了思想文化下行到民间之外,还应该考察思想文化外行而拓展空间,由此就会出现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因而就牵连出“世界大文化背景下的《格萨尔》”“《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以及“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的崭新命题。
思想文化远行到黄河长江的源头,就遇上了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传》是一个文化奇观,长达100万行,而且还是一部依然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态史诗。《格萨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玛纳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史诗大国,这里面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神话的想象,对英雄的描绘,以及世俗生活的展示。中华文明有了它们,就成了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共构的一种复合文明。称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是江河源文明的典型,意味着什么?我以为,它意味着高山文明,有高山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和尚武精神;同时江河源地带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侧,是蒙、藏两个民族的结合部,是东亚、中亚、南亚文明的结合部。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公元前的那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的那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而公元后的第二个一千年,历史将会证明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它是至今还活在数以百计的歌手口中的活态的史诗。由于是活态的史诗,对于史诗的发生学、形态学、文化学、艺人学,包括艺人在演唱中能够演唱十几部、几十部的那种精神的迷幻状态的研究,都会提供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现实的材料,可以为世界史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蒙古族还有一部史诗性的《蒙古秘史》,它是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是他们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并记录着自己的精神历程。这部《蒙古秘史》12卷(或15卷),282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四
在历史潜流中,深刻地搅动明清两代思想文化,挑战千古延续的社会体制的,莫过于以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为标志的西学东渐。这是数百年间牵涉着思想文化方方面面的一个异数。2010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炼、捶打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400年。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形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全面复兴。400年后的中国,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西学东渐400年祭”的。400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另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间有一座碑,那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400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
利玛窦和鲁迅,是我们考察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命运的两极。鲁迅作为百年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文明的批判者,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对他的研究已经被中国人作为显学,谈论了近百年。“百年鲁迅”,是一个植根于文学,却又超越文学的宏观文化命题。现代大国的文化进程,要求我们对鲁迅的存在采取新的观察。比如应该观察,鲁迅小说为现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展示了哪些视境上和途径上的美学可能性;鲁迅略作白话诗,却长期写旧体诗,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格局提供了哪些启示;鲁迅论梅兰芳,论中医,为中国式的戏剧现代化和中医现代化,提供了哪些思想参数。诸如此类的命题,都需要以一个渊博的文化学者的世纪性高度,退出一定的时间距离,采取更为宏大的价值尺度,进行知识清理和思想分析。这些涉及现代中国文明形态重新认知的命题,都需要以一代学术去完成。在此有必要突出地强调,提高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解释能力,是新世纪中国学术能否形成大国风范的关键,也是鲁迅研究能否大成的关键。解决这种解释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进入现代人的心灵,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向导;二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与当代世界进行深度的文化对话,激活中国思想的文化魅力;三是对前贤的解释能够契合当代中国人文建设的需要,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健康、自由、生机勃勃的发展。
百年鲁迅研究,学界更注重思潮,现在是到了转变角度,将鲁迅的文学血脉深入进行清理的时候了。文化血脉,是鲁迅的根脉所系。失血脉,就失鲁迅。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权衡文化偏至的时候,主张去其偏颇,他讲了两句话,一是“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二是“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然后再讲第三句话:“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鲁迅文化战略思想或文化哲学的结构是“2+1”,具有郑重、深刻、稳健的特征。追逐思潮而不顾血脉,则可能丧失文化身份,失去文化主体性的独立创造之根基,连带着对外来思潮也只能挦扯皮毛,难以深入。保守血脉而疏离思潮,则可能丧失创造的动力,失去文化现代性与时俱进的视境,连带着对血脉也只能陈陈相因,不能激活。中国现代文化的革新和发展,需要采取既“取”又“复”的复合型的深度文化对话姿态。通过对话,既可深度把握外来思潮,又可激活本有的文化血脉,然后再生长出“别”。这个“别”就是根基牢靠、生意盎然,从而创造出别开生面的第三种充满根基与活力的文化形态。“别”的姿态是“立”,是站起来,迈出脚步去创造,而不是躺着做复古梦,也不是跪着做拾人牙慧的文化贩子,或文化奴隶。只有建立自主创新的现代性文化,才能“立人”,才能立“人国”。这是鲁迅早年就探明,而且坚持了终身的文化战略思想,一种复构动态而强调现代性的文化哲学。
五
在讨论思想史的最后,专门推出方法论问题,这是我煞费苦心之所在。方法论是贯通思想史的,这里讲到的方法论包括叙事学方法、文学地理学方法和治学五窍门。它们相互交叉,融合为用。在中国叙事学的方法论中,我强调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创造新学理。即“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八字箴言。建立中国叙事学现代体系,要了解西方叙事学主要研究哪些问题,与西方现代理论对话和互动,要坚持“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至于考察叙事“结构”,包括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然后是时间、视角、意象和有中国特色的评点家。“结构”一词词性从动词到名词的历史性变化,反映出中国叙事的结构是动态的过程,是人与天地之道的精神契约。时间问题是叙事学研究中关键的关键,中国人的统观性时间观,使中国叙事长于预叙,与西方分析性时间观长于倒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叙事作品中,使用什么角度去看世界,牵涉他与世界结合的方向、方式和介入的程度。这在叙事文学中是一只兴致勃勃、无所不窥的眼睛。检讨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有所谓古典小说的视角非全知全能,实际上中国叙事有着丰富的表达方式和智慧形态。有志怪小说的限知视角,还有说书人的流动视角。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站在虚构之外谈虚构,出现了元小说的视角;而《聊斋》游戏笔墨,反而出现了反元小说的视角。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一“气”、四“效应”、十命题。一“气”,就是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中国人最发达的思维方式一个是诗,一个是史。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的优势。经、史共构了文化的双源性。编年史的准确性和人文地理材料的丰富性,是中国对人类文化史可以称得上“双绝”的重要贡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敞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形成四大效应:区域文化领域,形成七巧板效应;文化层面剖析,形成剥洋葱头效应;族群分布,形成树的效应;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形成路的效应。从微观的文化学着眼,分析老舍的创作文化层面意识,颇有意味的是,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就像一块千层糕。”他又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笔下的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所,各色人物在那里尽情尽兴地表演自己的文化角色。
六
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以“边缘活力”的理念观察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无可怀疑的是“史诗的富国”。在文学地理学中,无论是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还是族群的区分和组合,只要它们中的一些成分一经流动,就会产生新的生命形态,从而产生文化、文学之间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合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原本位置和新居位置的关联变动中,锤炼出文学或文化的新品质和新性格。唐宋以后中原汉人南迁,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形成独特的客家民系。黄遵宪曾赋诗赞叹客家迁徙:“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客家民系的“九腔十八调”散发着山乡的情调和趣味,体现迁移人群的情思、意志、见识和能力。文学地理学在本质上是会通之学。它不仅要会通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四大领域,而且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对中华文明进行整体性思维,不能不注重研究黄河、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在这种“太极推移”过程中,形成了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和巴蜀文化两个太极眼,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以此考察李白和杜甫这两位盛唐最重要的诗人,可以说,李白诗具有胡地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基因,杜甫诗是中原黄河文明的产物。
至于治学五窍门,即“学海苍茫,敢问路在何方?——治学的五条路径”,是进一步扩充了1924年章太炎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只重“耳学”,就是指用耳朵去听讲的这路学问,而不重“眼学”,不读原始著作的思路。除了眼学、耳学之外,进而拓展了“手学”,要用手去找材料;有“脚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去做田野调查;还应该有“心学”,用心去体验、去辨析、去思考,实现学理上的开拓和创造。眼学是做学问的基础,就是要多读原始文献和经典,回到中国文化原点。眼学具体来说,又包括卷地毯式、打深井式、砌台阶式和设计园林式四种方法。具体而言,卷地毯的方法即是根据研究题目,按照阅读书目把作家著作和相关材料,逐一阅读,发现问题就进一步追踪线索。打深井式阅读,即是选一个比较小的难题或学术空白点,穷尽所有资料。三是砌台阶式阅读,将整体性的学术设想进行规划,分成若干台阶,分阶段完成。起步的研究应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础,逐层递进,有如“接力跑”,又如“三级跳”。把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其内在的有机联系,格局互补,共构成一个总体的大分量。第四种方式,就是设计园林式,错落有致,迂回曲折,着眼总体的布局。从台阶式到园林式,就是从时间维度转换为空间维度,蕴含着学术理念和方法论维度的本质性的更新。耳学就是听讲之学,听课有助于拓宽视野和交流思想。如果不参与思想交流,就很容易陷入闭门造车的孤陋状态。这就容易陷入《礼记·学记》所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困境。手学是一门古老的做学问的方法,就是要勤于动手找材料,勤于动手做笔记,不断地在一段时间内按照特定的目标,逐层深化地积累材料。材料是分散在各处的,靠你用一条、两条线索把它们贯串起来。经过贯串的材料,才是有联系的材料,联系就是材料意义的新发现。而脚学,指的是田野调查。古人做学问的一个传统,叫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清人龚自珍赠送给魏源的楹帖,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我主张文学研究也要做田野调查,迈开双腿走到历史曾经发生的现场,身临其境地领略文学文本产生的空间,作者生存的环境,体验其胸次豁然而得江山之助,心与境会的妙处。同时,可以获得地方文人编撰很多资料、书籍、图册,这是一般的书店、图书馆都没有的。包括在那里搜集到的族谱、碑文、建筑风格等,都会启发新鲜独到的思路,而且使这些思路连通“地气”。心学指的是要用心去感受、体验研究对象,思考和发现其内在的生命及意义,达到超越的学理上有所建树的效果。心学的另一个原则,是对文本材料获得第一感觉之后,强化感悟和思辨的互动互渗,寻找自己可能的创造空间,深度开发材料内蕴的生命表达和意义密码。治学“五路”的提出,旨趣在于充分调动和激发研究者主体的感觉思想能量,多渠道、多路径、多层面地打开研究对象的本源、特征及其皱褶、脉络。眼学的特点在于明,耳学的特点在于聪,手学的特点在于勤,脚学的特点在于实,心学的特点在于创。五学的综合效应,是实事求是,天道酬勤,聪明敏悟,达至原创。创造性,是一切研究之魂。如此探索思想文化史,把思想史纳入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的宏大空间之中,打破单一维度,使思想文化变得丰富而博大,浑厚而生动。
洋洋洒洒万言,便是《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的内涵,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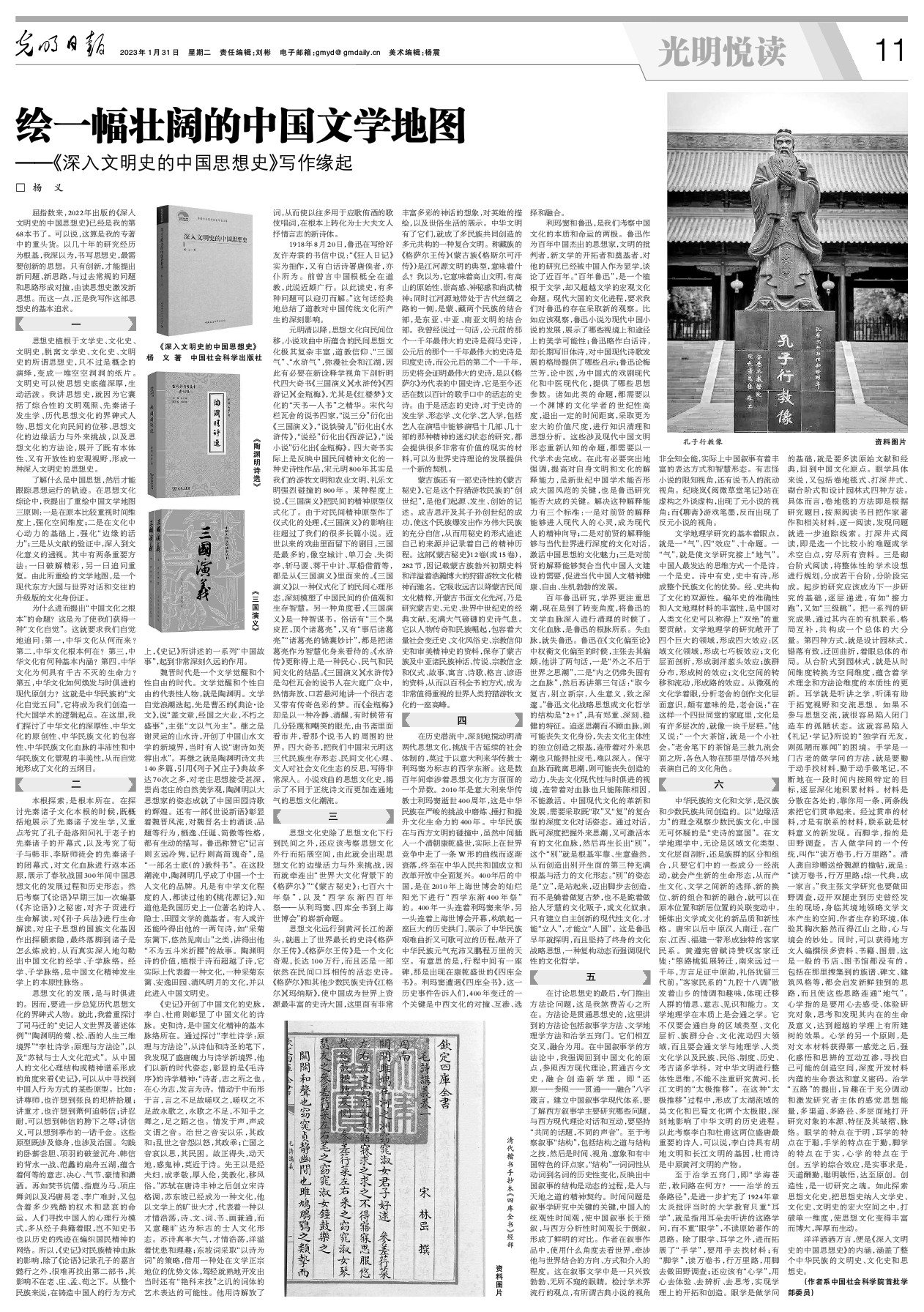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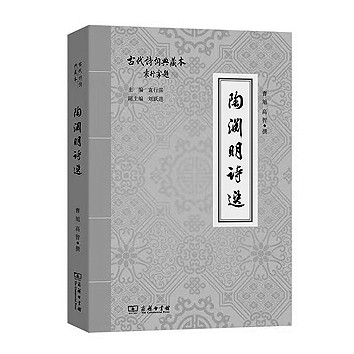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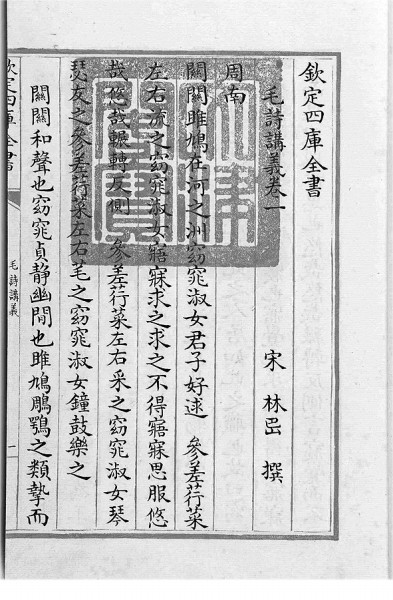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