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编者按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音乐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它穿过历史的浩荡激流,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而乐器,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有力见证。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一书,近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中,编著者们通过一件件乐器,将笛哨初现、钟磬喤喤、丝竹相合、锣鼓生辉的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今日,《光明悦读》约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撰文,为读者展开一段中国民族乐器的溯源之旅。
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展览以“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为题,展出了200余件(套)中国古代乐器。依托于国家博物馆丰富的藏品资源,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二十余家文博单位支持,展出的200余件(套)展品涉及乐器、乐俑、图像等多种形态,时代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各个阶段。2022年,国家博物馆择选其中的代表性展品,出版了名为《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的画册。
画册延续展览的立意,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乐器的文化特点。136件(套)艺术精品分为“鹤鸣九皋 声闻于天”“钟鼓喤喤 大音至乐”“丝竹相合 妙音飞花”“云间锣鼔 日月同辉”和“高山流水 松风清音”五个部分展现,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乐器的一次集中展示。
远古之音,旷如川泽,先人执笛,洞开乾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肇始,礼乐分明。钟声如天诏,磬声示神明,丝竹似流水,鼓声若雷鸣……在一组组精妙无比的图示与解说中,中华礼乐文明的生命力扑面而来。
先民之乐
在《天地同和》一书中,收录的第一件乐器,是1986年出土于舞阳贾湖遗址的七孔骨笛。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500~9000年。我们常说华夏文明五千年,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三千余年。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一认识被逐渐印证,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破。舞阳贾湖骨笛的陆续出土,证明了早在9000年前,生活于这片土地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制造和使用乐器的技术。
这一件骨笛突出的特点是,其正面,特别是开设指孔的位置,有着清晰的刻划痕迹,可见骨笛的制作过程经过了精心的测量与计算。在另外的骨笛上还可以看到,在一个音孔的旁边钻了调整音高的小孔。这些都说明,在那个久远的时期,贾湖人已经具有了相当明确的音准观念和制作骨笛的技术标准。回溯相关研究可知,198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武汉音乐学院组成的测试组,曾对M282∶20号骨笛进行了测音。测试结果显示,该骨笛音质较好、音阶结构为六声音阶或者七声下徵音阶,还存在着转调演奏的可能性。
贾湖骨笛在艺术与工艺层面所表现出的高度,以及遗址中的生产生活用具、契刻符号、农业畜业信息,都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溯到前所未及的阶段。类似的器物在不同的文化遗址或国家多有出现,对于这一类器物的性质,学界还存在不同认识。而贾湖骨笛的乐器身份之所以被普遍认同,关键原因是,在我国中原、新疆与西藏等地目前仍有相似材质或演奏方法的乐器被使用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属工具、文字、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脱离野蛮蒙昧、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些标志出现于各个古老文明的早期阶段,且都属于人类意识与观念的创造性实践。音乐艺术,同样可视作文明的标志物,是人类脱离了生存需求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其产生的过程今人有多种解释。无论是模仿、劳动、巫术、表现还是求偶,都意味着人类对声音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自发阶段,成为有目的的自觉行为。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应为人声。随着可发声器物的加入,音乐行为步入更加高级的阶段,乐器也从此成为音乐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物质形态的角度来看,乐器由粗简到精密,从单一材质到多种材料的结合使用,映衬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改写了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认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文明诞生标志物的认知。
黄钟大吕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中如是说。《礼记》,便是此书书名“天地同和”的由来。
《礼记》是记录先秦时期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对后世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礼仪制度的详尽论述,对华夏礼乐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奠基作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逐渐进入阶级社会。这一时期因为青铜礼器的大量使用而被称为青铜时代。周王室为了维护统治权力,推行了一整套等级鲜明的制度体系——礼乐制度,而青铜礼器便是此制度的物化形态。以编钟为代表的青铜乐器,因其具有发声功用而成为礼器中独特的一类,甚至成为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地同和》收录有青铜钟类器物二十余件(套),形制涉及铙、镈、甬钟、纽钟、钲、錞于、铎、句鑃多个类别,均为殷商至战国期间的典型器。虽然这些器物形态各异,应用范围不一,件数多寡不同,但均由青铜铸造而成,堪称人类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13件战国编纽钟,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套完整的楚钟。由于保存情况完好,音乐性能优良,其演奏的《东方红》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曲响彻中华大地,并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而进入太空。在录制《东方红》的过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在钟体侧上方找到了五正声之外的一个偏音,由此完成了全曲的演奏。正是这样一个发现,揭开了认识合瓦形编钟历史之谜的序幕。
合瓦形的称谓最早见于《梦溪笔谈》,意为钟体形似两个瓦片扣合,这一形制是华夏先民独有的智慧创造。在青铜被称为吉金的时代,同样的原材料既可以制作武器、货币、生产生活用具,也可以制造象征身份的礼器。持有青铜器数量的多少,往往代表着国力的强大与否。如何高效地利用“祀与戎”活动中必需的原材料,是礼乐器的制造者面临的问题。合瓦形编钟天然地具备一钟双音特性,即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发出两个独立的乐音,由此可以在相同的音列内减少编钟数量,达到节省材料的目的。
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黄翔鹏先生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直到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他的看法才被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曾侯乙编钟3700多字的铭文中,绝大部分记录的是各诸侯国的音高关系,其正侧鼓分别标注着以三度音为基础的乐律学体系。当近世外国学者以“中国音乐基本由五声音阶构成,处于七声没有齐备,更遑论十二律”为主流观念的时候,青铜编钟的陆续发现,揭示出中国的乐人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有了12个半音的音高观念,并成功付诸实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音乐常见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音乐,只是“以简御繁”理念的产物。
在《礼记·乐记》中,“礼辨异,乐统同”的观念被反复提及,强调了以礼乐器为代表的物质形式体现的是等级差异,而音乐的使用是为了强化统一的观念,通过文化的统一来实现政权归属的认同。因此,青铜乐器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其在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情感方面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夏正声
如果只能选取一种乐器,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代表的话,我个人认为,当属古琴。《天地同和》一书,为古琴独立一章,即体现了其独特的地位。
古琴,又称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焦尾”等,这一历史悠久的乐器直到上个世纪还被称为“琴”。只是之后因众多外来乐器被冠名为带有修饰词的琴,如扬琴、胡琴、小提琴、钢琴等,才更名为古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琴在传统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古琴的文献可上溯至周代,如《礼记》《世本·作篇》中都有伏羲制琴的记载。周代以后,儒家“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文人四艺之首。正是在文人的拨弄下,古琴艺术形成了华夏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寄托着文人不流于尘俗的情感追求。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生动地刻画了魏晋文人的风骨,其中古琴的形制已与现今的古琴完全相同,这在全世界的旋律乐器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唐代中期,古琴艺术发展到最为繁盛的阶段,记谱法与斫琴技艺的发展,为古琴艺术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挥洒空间。特别是减字谱的出现,对琴曲的广泛流传贡献卓著。与其他传统音乐多用工尺谱标记音高与节奏的方式不同,古琴谱记载的是弹奏时的定调、弦序、徽位,以及左右手指法、奏法。这样的记谱方式是无法视唱的,观者无法从中读出乐音。脱离古琴,以汉字偏旁为元素的减字谱就是贾宝玉所说的“天书”。为一种乐器创造一种记谱法,一种记谱法只适用于一种乐器,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样是罕见的。也正是因为这一份长达千年的坚守,才保证了古琴乐器形制和古琴艺术品格的持久稳定,成为华夏正声的代表。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九霄环佩琴,为唐代雷氏所斫,是现存同名四器之一。琴体保存完好,通发牛毛断纹,整体风格浑厚圆润、精致内敛。不同于日本正仓院的偶然性封存,国内的唐代古琴能够传承至今,且大多保有优异的声音品质,得益于千百年来不断地弹奏与修缮。历代琴人通过弹琴与“知音”,完成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不断地将人文精神和情感内涵赋予古琴,将每一处结构、每一份尺度、每一次抚弄,都视作自然与生命的浓缩。在传世名琴的琴腹、琴底等处,多见题款刻印,借以寄情喻志,也体现着文人对古琴所特有的、非一般乐器所能比拟的文化情感。
乐器承载着文明,印证着历史,蕴含着情感,伴随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骨笛、编钟与古琴,体现着中华民族于不同历史时期在音乐艺术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然中华音乐文化博大精深,远非这些典型艺术形式所能涵盖。通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可以感知,这些乐器精粹,来自丰厚文化积淀与丰富艺术形态的给养,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之浩如烟海,奔腾不息。
(作者:冯卓慧,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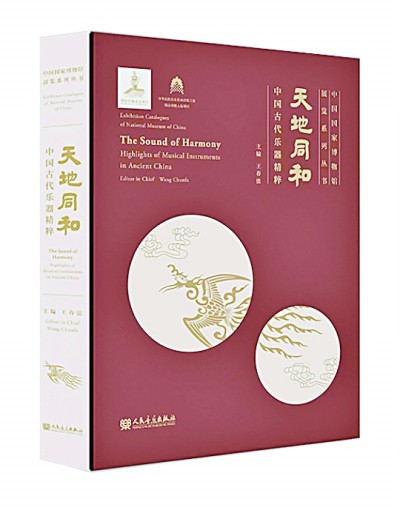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