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德国古典学家菲利克斯·雅各比为保利-维索瓦古典研究百科全书撰写了长达三百余页的《希罗多德》一文,全面而系统地讨论了希罗多德《历史》的写作风格、史料来源、结构内容、文本流传以及后世影响等。雅各比的这篇长文决定性影响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设定了基本的问题场域,而且还对诸多关键性议题提供了明确的讨论起点。回顾百余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学者们除了在一些经典的历史学议题方面有重要推进外,还广泛利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全球史等研究范式,阐发希罗多德著述文本的丰富内涵,本文现择要进行介绍。
自雅各比以来,西方学术界始终热议的一个话题便是希罗多德著述的真实性问题。希罗多德在古代就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名声,西塞罗在《法律篇》中将希罗多德形容为历史学之父,但又说他的作品中充斥着编造的故事。到19世纪末期,学界依然有一些质疑希罗多德著述真实性的声音。但雅各比的文章强调了希罗多德自己的探究工作,以及希罗多德对口述传统材料的鉴别和遴选能力,确立了希罗多德撰述内容基本真实可靠的观点。后来的学者大多接受了雅各比的观点,如20世纪著名的古代社会研究者、意大利古代史家莫米利亚诺就曾说过:“希罗多德之前并无希罗多德。”因为希罗多德是第一位运用口述传统撰写历史的人,并且通过探究来考察事件的因果以及当事方的动机。然而,对于希罗多德著述真实性的质疑并没有终结。德国学者菲林1971年出版了极具争议的《希罗多德和他的史料来源》一书,重启了对希罗多德著述真实性的怀疑。在菲林看来,希罗多德的撰述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他也不是“科学的”历史学家,只是给出看似真实的叙述。菲林的观点引发了众多批判与回应,英国古典学家福勒在其影响深远的《希罗多德及其同时代者》一文中就提出与菲林相对立的观点,力图证明希罗多德在撰述时有意识地进行史料批判工作,并自觉地作为历史学家在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希罗多德写作真实性的讨论也有新的研究方向,特别体现在对希罗多德叙事学的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希罗多德如何通过文本结构和撰述结构来展示自己的“探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历史学家德瓦尔德的系列研究,以及任教于美国北卡罗莱纳教会山分校的贝拉格瓦纳思的专著《希罗多德的动机与叙事》。后者特别指出,希罗多德往往并不会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提供一种权威解读,而是在撰述过程中提供多种原因和解释,所以希罗多德是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理解过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读者应该利用这些多重的材料,自己去探索结论。
关于希罗多德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议题是族群与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希罗多德如何评价雅典的问题。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仅记载了希波战争的原因与重要战役,而且在前四卷中记述了大量族群生活的地理环境、习俗法律等。传统解释往往聚焦于西方希腊与东方异族的习俗对立,东方异族被塑造为希腊人的“他者”,二者之间是自由与奴役、政治与专制的对立,而希罗多德也被视为是雅典的代言人。但是晚近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摆脱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再认为希罗多德对雅典持有毫无保留的赞美立场。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希罗多德对于吕底亚、埃及、斯基泰人以及东方其他族群的书写并不是要显示他们与希腊的不同或者和希波战争的关系,而是有着对这些地区和族群本身关切的内在价值。希罗多德对雅典以及更广大的希腊世界在希波战争中的表现是持赞颂立场的,但是对于雅典在战争后所表现出的帝国主义行动实际上是持批判态度的。
学界在上述两大议题研究的推进,实际上也离不开20世纪以来的史学思潮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如从对希罗多德笔下东方异族描述的新理解,可以看到爱德华·萨义德思想的影子。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使得学者们重新审视希罗多德撰写不同族群的初衷,不再带着希腊的眼睛将他们视作“蛮族”,而是如其所是地来看待非希腊人。另外,对希罗多德写作的理解很明显受到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像福柯、海登·怀特等思想家并不认为史家就是对过去事实的客观收集者,而是将史家首先作为作家来对待,在拣选材料和书写的同时,实际上就制造了一种对于过去理解的叙事。需要警惕的是,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史并重的分析视角,存在着把传统史学编纂的客观性价值过度贬抑的危险。除了20世纪的这些重要思潮外,对希罗多德的研究也越来越体现出多学科的影响。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希罗多德的镜子》,就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以及人类学的方法对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的叙述作出了经典研究;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则通过对口述传统的研究,重新激发了对希罗多德运用材料的理解,即如果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社会主要是口述社会,那么理解他的撰述方式则有赖于对口述社会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方式的深入把握。
进入新世纪之后,除了对传统议题的研究推进外,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这也与史学研究出现的新趋势有关。首先是接受史研究的兴起,希罗多德及其著述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并非新话题,但晚近国际古典学界的接受史研究成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在过去十年中,学界集中出现了多部专著和文集,讨论希罗多德对希腊化文化、罗马史学编纂以及拜占庭的影响,以及后世对希罗多德史学编纂方法的接受与改造。其次是比较历史研究,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与阿拉伯史学经典论著《历史绪论》的比较、与司马迁《史记》的比较研究等。这些比较研究并非简单的史学编纂方式或者叙述风格的比较,而是通过诸如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描述与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来确认对于游牧民族的共同描述等,还有比较不同帝国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等。当然,这个领域还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也与国际学界出现比较古典学的研究倡议遥相呼应。第三个动向则与全球史影响相关。如果我们不把希罗多德看作是雅典或者古希腊价值理念的代言人,那么他作为最早的全球史家所撰述的《历史》就可以有全新的定位和理解方式。2010年,三位德国学者主编的《希罗多德与波斯的世界帝国》一书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该文集中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希罗多德作为一个出生在希腊与波斯交界处的作家,所要书写的是一部世界历史。而这个世界不只有希腊的城邦世界,更多的是波斯所构建的“世界帝国”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的主线是波斯的兴衰,虽然大流士没有征服斯基泰,薛西斯没有征服希腊,但波斯仍然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唯一所知的帝国,统治着广袤的土地。
总之,从雅各比的奠基性文章以来,西方学术界总体以一种更为均衡的眼光来看待希罗多德笔下的丰富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力回到希罗多德的本意永远是学者们需要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对希罗多德的研究也必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以及人类事务本身。
(作者:张新刚,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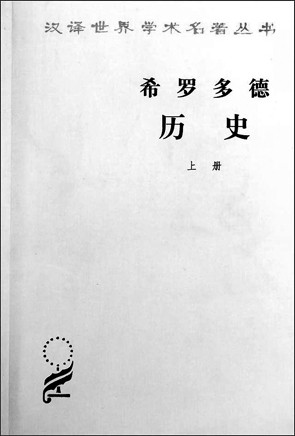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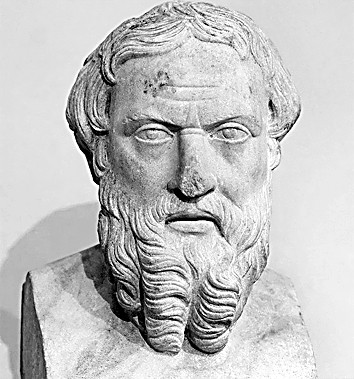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