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经典细读
审美和思想的生长点
光明悦读:在新书《思于他处》的32篇随笔中,您谈及了很多经典作家作品,如卡夫卡、鲁迅、汪曾祺、普希金等等,这些文章是文学研究者的阅读笔记和书评。人们常说经典是常读常新的,能否与读者分享一下您的阅读兴趣?
孙郁:其实这本书就是我这些年业余时间读书的一种体会,我有一个习惯,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书以后,会把感想写下来。我其实最早不是搞书评的,以前在报社编文学副刊,当时各种各样的好书出版后,我就写下一些心得。到90年代初,开始给《读书》杂志写一些书评,今年整整30年了,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和阅读兴趣展开的。《思于他处》这本书其实就是这些年来我读书的一点痕迹,但它是边角余料,不是学术论文和那些比较正襟危坐的书,我那样的书很少,就几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随笔,因为我喜欢这样写,觉得它比较随意。把阅读时自己那种最初始、最原生态的感受表达出来:一本书、一部作品为什么打动了我?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把我的感觉写出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在阅读一个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文本时,会使你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突然被召唤出来,那么就赶快把这个感觉留住,这种感觉如果和一些知识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可能会发酵,生成一种审美的观念的或者思想的概念,让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许多思想都是在细读文本时产生的,比如海德格尔的很多思想就是在阅读荷尔德林的诗、尼采的文字时产生的。所以通过读书,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会让我们在一种陌生化的感觉里,寻找到和世俗社会不一样的一种尺度,它会舒缓我们的种种压力,使我们从世俗的尺度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觉得对经典或者是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阅读,会使我们不断涌现出新的审美体验,这个体验可能是知识和思想的生长点。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与当时的学人细读经典、重新发现经典有关系,我就是受益于那一代学人,并受到他们的启发。
光明悦读:这样说来,阅读经典和细读文本不仅是个人的审美训练,还是一种激发思想的方式。您在书中提到,文艺的一个目的是“唤醒读者的灵思”,这就是对审美的重视吧?
孙郁:知识很重要,审美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高校里很多老师不太注意培养学生的这种审美能力,主要是讲授知识,但是审美这个东西也教不了,就只能用熏陶的方式。中国传统里,从孔夫子一直到鲁迅,都很注重感悟,注重诗性的培养。在东方,智性和诗性其实是在一起的,我们的汉语是有传达审美和思想的功能的。当代作家、小说家很多不太注重语言的这种体验,当代小说能让人们反复阅读的很少,但《红楼梦》是可以反复阅读的。我们现在让孩子们背古诗,看古代的作品,其实就是要培养语感,与文字共舞,呼应文字,发现它的好处,然后去思考一些问题。
汪曾祺的语言之风
光明悦读:您在《汪曾祺的语言之风》一文中说“在汪曾祺的眼里,语言是精神的存在之所,也为生命的血脉”。您多次谈及汪曾祺,似乎都是从语言这个方面去切入他的独特性。
孙郁:汪先生的语言是这样,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先锋派,受到域外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影响,那种表达是一种撕裂了的流行语的一种表达,很前卫,但后来他才发现其中有问题,这是一种小知识分子的语言,要表达大众生活的时候,他必须回到民间去,所以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编《说说唱唱》,收集整理了全国各地的民歌歌谣,这些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后来,汪曾祺又受到了明清戏曲的影响,觉得剧本的念白和韵文也很有意思,有世俗性、烟火气。汪先生开始注重“烟火气”,所以在他的语言里面,有六朝的语言,有宋明士大夫的语言,但同时又有民间的一些口语,他在张家口时学了很多地方土语,他还专门谈张家口一些俗字怎么念,后来他对北京市井的生活也很了解,再加上他家乡的高邮话,他把这些不同风格的语言汇在一起,混搭起来,像一个调色板一样,就调出了一个新的话语方法。
他曾跟我说,他的语言表面上看很平常,背后是藏着文言文的。汪先生这么做是觉得我们的文学和学术表达太单调了,他要把有意味的存在给勾连起来。应当说,鲁迅之后,汪曾祺对中国的语言和表达的贡献是最大的。
光明悦读:那么,方言、土语和日常语言中,有哪些潜在的未被我们重视的价值?
孙郁:方言土语里有一种鲜活性,它是植根在泥土里的。清末韩邦庆写《海上花列传》用的是吴语,金宇澄写《繁花》用的是上海话,周立波写《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前者是用东北话,后者用的是湖南的方言,这些语言是很有生命力的。
最近读季栋梁的《半坡典故》,就像到了宁夏的山里,看到了带着泥味的古路,画面感和声音感都出来了,小说里写到的西北农村的一些语言,都是《诗经》里的语言,比如“葫芦”称“瓠子”,与《诗经》的表达一致,岁月没有改其旧影。
光明悦读:这些方言俗语里有历史,而且仍是活着的。
孙郁:贾平凹的小说里有许多他的家乡话,保留了很多汉代的语言,所以会觉得有一种古风在里面。
光明悦读:您之前说过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全集除了《鲁迅全集》之外,《汪曾祺全集》是卖得最好的。您认为,为何现在的年轻人仍热衷阅读汪曾祺?
孙郁:汪曾祺对一些假道学的东西进行了解构,他又保持了儒家的那种温和暖意,所以读他的文章,首先他不装、很真。其次他有趣味,把生活艺术化,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存在里面,他都能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他以前去香港时会想:香港早晨怎么没有人遛鸟呢?在这么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为什么会没有提笼遛鸟的人?我们很多人不会想到这种问题,而他就有这样一种“闲心”。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他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但是,休闲、快乐就是他要寻找的一种东西,这些对于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另外,在他的小说里,他对丑陋批判得也很厉害,比如《陈小手》这些作品,就是用一种不动声色的语言,把世界上最本真的美和最丑陋的东西都写在了里面,这是汪曾祺不简单的地方。
把视野打开,把文体打开
光明悦读:在《“思”与“诗”的互渗何以成为可能》一文中,您提到学术论文写作深受翻译体影响,感慨“今天有弹性的辞章越发稀少”,向往程千帆所说那种“贵乎变通”,古今笔意悉入文中的境界。您所指的辞章的“弹性”是怎样一种状态?
孙郁:文体一旦形成一个模式以后,它就会按照一个逻辑、一个模块来展开,很有可能把鲜活的东西锁定到无趣的方向。所谓“弹性”,是说表达要有空间、有余地,当我们在表述一个观点的时候,要警惕自己的表述可能是有问题的。有弹性的语言会把一个问题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会以一种有温度的方法来处理一个没有温度的话题。
文体就像一个巢穴,是思想的寄寓之处,所以它应当是有温度的。我常举例鲁迅的语言为什么有弹性?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紧接着他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他在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要用另一个概念来修饰它,不然这个概念很可能走到反面去。真正的思想家的语言是有弹性的,他们会用一种多维的结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光明悦读:百余年间,我们的述学文体经历了哪些变化?
孙郁:最早一代学者像王国维、鲁迅等人,他们是用中国的辞章来表达学术的看法。他们虽然懂外语,但没有翻译腔,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都是用晚清读书人的语言来写作的,鲁迅是受六朝文字的影响,陈寅恪的文字带中古文人气,章太炎更早,他有时涉猎到周秦汉那套语言。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也是用很东方的语言来表达哲学的认识。述学文体其实也是一种修养的表现。
还有一种是翻译了外国哲学和文艺理论的书并受到其影响,比如朱光潜,他的文艺美学就受到了很多欧洲批评家的文体影响,但是他的语言写得比较美。后来,苏联文学批评理论过来以后,又有很多人模仿,于是学习西方和苏联这套话语的语体就出现了。学者用这种翻译体的语言来表达学术观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用非常艰涩的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学术论文就开始越来越涩,越来越迂回,越来越绕,如果说为了表达思想的绵密性这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也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于是陈平原就提出,应当用通俗的、轻松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的一种方法。我个人也觉得,我们应当用东方人充满性灵与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对于审美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真正好的思想家写文章,常常是深入浅出的,大家的思想也常常在谈话里面出来,比如胡适他们都主张“谈话风”。
光明悦读:前两年有一些高考作文被批评“翻译腔”,翻译腔是不好的文风吗?该如何理解鲁迅提倡的“硬译”?
孙郁:翻译其实是一次语言实验,要把外来的文字用母语表达出来,这其实要看母语的能力怎么样。为什么说鲁迅、穆旦、傅雷这些人的翻译好,因为他们的母语好。但是很多翻译家都是按照现成的语言来翻译,不敢用颠覆母语的方法来表达思想,不太去考虑向表达的极限挑战、超越,“翻译腔”就是一种偷懒的语言。鲁迅在翻译尼采时用的是列子的语言,他认为列子和庄子的语言才能和尼采的思想对应起来。
翻译会刺激语言的生长。比如普希金的俄文受法文影响很大,日本的夏目漱石英文很好,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很大,二叶亭四迷是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的。他们都是通过翻译刺激了母语的生长,这是很重要的。
钱锺书提出最高的翻译是化境,鲁迅则认为要“硬译”,他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书写习惯和认知习惯,因为中国的传统语言似是而非,是一种审美的,但缺乏逻辑,翻译就是不断使我们的母语陌生化。但“翻译腔”是在我们熟悉的语言里面重复,反复延宕,没有陌生化的效应。我最近看一个翻译家的作品,食之无味,因为他对母语没有感觉,但是像穆旦翻译的普希金、雪莱,翻译得太美了,因为穆旦本身就是诗人。
光明悦读:您的文章常有一种亲和力,有走出象牙塔与大众对话的意味,《思于他处》中说“文章之道就是生命之道”,这是您的写作追求的一个方向吗?
孙郁:写作是对话和交流的过程,是与自己的心灵、与历史对话,是与大家交流,与时代交流。这样想,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绑在一条狭窄的路上,就会把视野打开、把文体打开。
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那种感受和体验告诉学生,其实你也影响不了学生,鲁迅讲,不要给年轻人做导师,鲁迅说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我怎么能给你当导师呢?所以即便是学者也不要装,我觉得汪曾祺和鲁迅这一点是很可爱的。我希望把学术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的诗意的表达融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学问不应当只在象牙塔里,它就在日常生活里,日常生活里面到处都是学问。
(本报记者 陈雪)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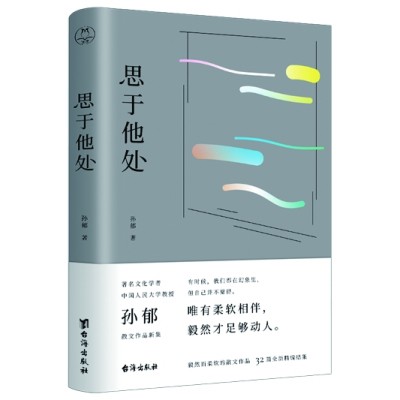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