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孙犁)。蝉的到来,给饱受苦夏折磨的孩子们带来无穷的快乐。
蝉是从蝉的卵子和幼虫变化而来。李广田说:“秋天以后,我们常看见树枝的嫩梢——尤其是桃树——有些是先已枯死了的,折开看时,则见死枝里面有一种卵子,白,小,状如虮,据说那便是蝉的卵子。据说直到明年春天,雷鸣惊蛰时,这卵子便被春雷震落,又深深地钻在土里了。所以蝉的幼虫,又名为‘雷震子’。春天来,是‘出树’的时候了,须掘地五六尺深,才能将树根掘出,把树身放倒。就在这掘树的深穴中,常常有一种幼虫可以被发现,颜色嫩而白,因为落地的久暂不一,形体的大小也不同,头尾蜷曲着,像一个小小的胎儿。那便是蝉的幼虫。”
到了夏天,蝉的幼虫有的就长成了。捕捉蝉的幼虫就成了北方农村小朋友最乐于做的一件事。孙犁在《昆虫的故事》中为我们讲述了其中的技巧:“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游,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钩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察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
蝉的幼虫可以吃。烤着吃,炸着吃,都鲜得很。美食家蔡澜还提到:“泰国菜中也常以蝉入菜,放进石臼中,加了指天椒、小茄子和鱼露,大舂特舂,做出紫颜色的酱,拿来蘸青瓜、生豆角和柳叶吃,味道鲜美得不得了,连最单调的生蔬菜都变成上等佳肴,吃个不停。”
蝉的幼虫,需要经历艰难的蜕皮过程才能变成蝉。法布尔在《昆虫记》中细致地描述了这一过程:“看起来很坚硬的外皮从背上裂开,露出里面淡绿色的蝉。蝉的头部首先露出来,接着是吸管和前腿,随后是后腿和翅膀。此时,除了身体最后的尖端,蝉的整个身体已经完全蜕出了。接下来,蝉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它的身体先挣脱出来,只有一小块还固着在旧皮上,然后翻转,直到头部倒悬、布满花纹的翼向外伸直并完全张开。随后,它又用一种几乎不可能看清的动作,尽力将身体翻上来,并且用前爪钩住空皮”,“它那柔软的身体在还没具有足够的力气和漂亮的颜色以前,必须在日光和空气中好好地沐浴。它会用前爪把身体悬挂在已脱下的壳上,在微风中摇摆。它的身体依然很脆弱,依然是绿色的。直到棕色的外壳出现,它才变得像平常的蝉一样。”
蝉的幼虫蜕皮成蝉时脱下来的壳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孙思邈的药书中说:“蝉壳,主小儿痫,女人生子不出,灰服之主久痢。”李广田回忆:“孩子们常常带了长竿,携了竹篮,到树林里面去拾‘神仙皮’。‘神仙’的皮原来也可以成为一种货物。夏天将近完结的时候,便有人担了很大的席篓,到各村里收买蝉壳。‘买神仙皮呀,买神仙皮呀’,这样地呼喊着。此外也有担了泥人、芦笛、刀竹,或针线火柴之类的东西来交换蝉壳的,这便更是小孩子们所喜欢做的交易了。他们也都知道,神仙皮被收买了去,是用来配制眼药或配制金颜料等等物事的。”
蝉喜欢叫,“一迭声地叫,这里,那里,连成一片,铺天盖地”(王安忆)。蝉声,在李广田看来,“初夏雨霁,当最先听到从绿荫深处鸣来的几句蝉声时,是常有一种清新愉悦之感的,觉得这便是‘夏的信息’了。”在郑振铎看来,“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地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歌,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音,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的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闭了目,静静地听了它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幽的乐阵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
蝉“嘶嗄的声音好像金属的簧断续地震动着。但是愈唱愈缓,腔子也愈拉愈长,然而仍固执地唱”(陆蠡)。施蛰存最初对蝉的叫声是反感的,“聒噪得那样的叫人心里为之烦乱”,但是他后来“用‘蝉噪林愈静’的会心去听它们歌唱,渐渐地我非但不再觉得它们烦乱,甚至竟听出一点意思来了”。法布尔说:“幼年的蝉如何在地下生活,至今还是一个未知的秘密。……通常,他在地下生活的时间是四年,而在日光中的歌唱则不到五个星期”,“我们不应厌恶它歌声中的烦吵浮夸,因为那种声音是那么高亢,足以歌颂它的快乐,既如此难得,又如此短暂。”
蝉白天叫,晚上也叫吗?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有个叫陈少白的读者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回信说:“《背影》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不过,后来朱自清坦言:“那时我自己却已又有两回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我没有记录时间和地点等等,可是这两回的经验是确实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叫。汪曾祺在《花园——茱萸小集二》中提到:“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决不偏斜转弯。”
蝉不但会叫,还会飞。不过,有时候,蝉也是动弹不得,“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许地山)。
蝉可谓识尽夏味,而不知春秋,慢慢地,“吵人的蝉声被秋风吹散了,代替它的是晚间阶下石板缝里蟋蟀的悲鸣”(巴金)。
(作者:宫 立,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资助”阶段性成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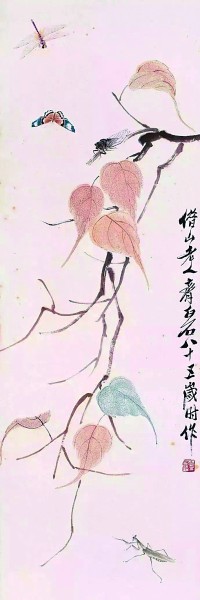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