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不管是否承认,一生当中,每一个人都在行走,在行走中迷失方向,在行走中目光坚定。哪怕是驻足发呆,那也是另一种行走,思绪的行走,甚至,有的时候,思绪的行走远比脚步的行走更有意义。
无一例外,中国的文化散文都是行走的发现,再推而广之,世界上一切文史哲的成果都是行走的结果。“每每寻访遗迹、翻看方志史料的时候,总不免让我感叹古人的了不起。”斯雄在他的新作《皖韵八记》“自序”中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行走已经具有了澄澈的意味。中国的传统文化外化于山川古建,内凝于典籍经史,甚至,像或明或暗的微星一样藏在粗朴的族谱和简陋的乡间文书里。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愈发博大精深,而且玄机暗藏。“随物赋形,人与山尚且能对上眼,说明确实有物我两忘、身心俱悦的欢喜。”我就说嘛,《皖韵八记》与其说是斯雄先生《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的续篇,不如说是他在行走中更多的发现,是更通透的“欢喜”。
中国文化讲求天工开物、道法自然。如果把各类生物也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的衍生物,其实人类是应该和各类生物成为朋友并从万物中汲取智慧。在我的故乡亳州市中心,矗立着一尊华佗的雕像,行色匆匆的华佗腰间挂着丹药葫芦,目视前方,一脸忧色。在亳州,最为当地人频频提起并报以最大敬意的就是乡贤曹操和华佗。而亳州之所以成为“中华药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华佗。每次仰视那尊雕像,我都在想,华佗留给亳州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份名号?
这个问题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才有了明晰的答案。一个流传颇广的视频显示,在武汉市一个方舱医院里,来自亳州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带领患者和医务人员练习五禽戏。很惭愧,自己在亳州的土地上行走了几十年,竟然对五禽戏熟视无睹,竟然对华佗留给后人的这份丰功伟绩视为当然。
而同样行走的斯雄却以如炬目光发现了这则信息背后的宏大叙事,他在《五禽戏记》一文中,由这则信息生发,对五禽戏的历史进行了爬梳,让习练五禽戏的功效与一度困扰人类的新冠病毒碰撞,“在疾病面前,人类其实是很脆弱的。真要直面生死的时候,人的想法反而变得简单了。首要的当然是活下去,进而肯定也会想到;早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啊!”
这是振聋发聩的喟叹。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路径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但我们在期待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否道法自然?如果不能做到,是否退而求其次,去师法前人的优秀遗产?所以,行走的另一面,就是把个体打开,去除人为设定的枷锁。当然,这同样需要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因为生活从来不在别处,生活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却又需时时追寻。
还是2020年,淮河遭遇历史上最大洪水。7月20日8时32分,“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自1953年建成后第16次开闸,咆哮汹涌的洪水被“牵”进本为良田的蒙洼等7个蓄洪区。“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这一次,又是蒙洼人含着眼泪扛起所有”,各种媒体上,类似的悲壮故事被反复提及。
开闸的那一历史时刻,我是在现场的,出于职业需要,也在第一时间采写了报道。当时,斯雄先生也因为工作缘故在现场。但之后不久,他又写了《王家坝记》,把看似新闻的边角料整合出一篇极具史料价值和当下意义的作品,既有作者身临其境的独特感受,又有淮河和王家坝历史的变迁,最难得的是那种伴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后的理性思考。
“遥看王家坝闸,如巨龙横卧在蓄洪库上游,确有拒水于千里之势。站在闸的桥面上,虽然脚下洪水仍在咆哮,但已然不再感觉那么惊心动魄、提心吊胆了。”没有到过王家坝,没有亲历开闸那一刻的紧张焦虑,绝不可能有如此真切的感受。更不为人所知的,是流淌着灾难和苦难的淮河从“十年九涝”到如今的安澜,背后是久久为功的治理和智慧,“人和水都有了出路,不再争夺发展空间,自然就能和谐相处了。”
新闻是对现实的烛照和呈现,文化散文如何介入现实并为现实“兼收并蓄”,可能是当下很多书写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你可以因草木而欢喜,可以品茗而自得,可以经山川而自乐,问题在于,如何把小欢喜变成大欢喜,如何把一人之乐演绎成众人之乐,如何把个体自得上升为全体自得,一方面需要脚步向前,另一方面,恐怕还要把视线从内向转为外向。具体地说,新闻界惯常使用的“宏大叙事和微小切口”的合一,可能是对现实最好的表达。
我一直认为,斯雄先生的职业习惯成就了他的行走,练就了他的深邃,而对文字的敬惜和执着,又让他的行走和行走中的发现有了厚重且色泽浓郁的“包浆”。《皖韵八记》中的《天柱山记》《六尺巷记》《“七仙女”记》《八公山记》等,莫不如此
得知他要写《天柱山记》,我是很为他捏了一把汗的,诚如作者所言,“一山而多名,背后一定有文章”,同理,一山而多名,先后一定也有无数名人“留下文章”,比如余秋雨的《寂寞天柱山》对很多试图品读天柱山的人来说就是一座“大山”。但斯雄先生另辟蹊径,把眼光投注到天柱山下三祖寺旁的摩崖石刻上,尤其对“止泓”两个大字情有独钟,这就很符合登山观景的意趣了——埋头登山,移步换景,唯于心仪的景色前久久流连,心心念念。一番和“止泓”遍历千年的对话和会心之后,“心中默念‘止泓’,回看天柱峰,不免有望峰息心之慨。盘桓山谷泉边,仿佛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不知不觉中,真要‘坐石上以忘归’了”。
这一番,登山如行云,文字如流水了。
休谟在《人性论》中说:“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我同意。也因此坚定地认为斯雄是幸福的。
据说,坐了江山后,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原本是打家劫舍,不承想弄假成真。第一本《徽州八记》后,斯雄曾言之凿凿地谦称“游戏之作”,谁知不久又有了第二本《江淮八记》,接着在他离开安徽后又推出第三本《皖韵八记》,而且篇篇是精品,篇篇被广为传诵。这种“弄假成真”,幸福的意味可想而知。
疫情期间,已经“行走”到吉林的斯雄通过微信发来一张照片,一改昔日的清癯,有些微胖了,衬以杂沓的胡子,反倒有那么一丝仙风道骨的意蕴了。他自嘲是“封城居家办公的老人”,呵呵,这个人,分明是居家却放飞思辨行走不已的小老头嘛。
(作者:常 河,系本报高级编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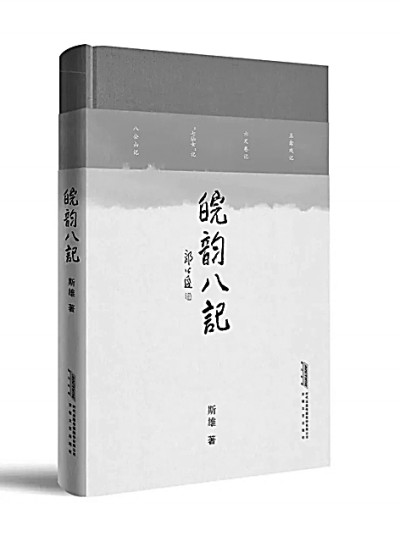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