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张清华教授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以1916年至2015年百年历程为时空刻度,以编年体方式,遴选新诗凡十卷,厚可盈尺。或如鲁迅所言,选本所体现的,未必是原作者的水平,倒深深折射出选家的眼光。且不论选家之意图与眼光,从其编选体例和历史意识来看,《编年》既是选家依据心中或隐或显的一定文学史观念遴选的集成式诗歌选本,又是以诗歌个体面目呈现的陈列式百年诗歌史。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是什么样的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编年》一经问世,和其所选诗作一样,自然也要接受坊间的说长论短,尤其是在世诗人们的称赞或腹诽。
世间的选本或文学史著,均以遴选品评杰作为要务,似乎还没有以劣作、疵品为中心者。从时空跨度、遴选数量、编者队伍等诸要素看,编选出一部令大多数人满意的选本实属不易。且不说编选者钩沉辑佚、品评判断之功力是否举案齐眉,就是主编之意图能否较完美实现,也非举手之劳。更不用说入选作品,既要有思想深度,又要有精神高度;既要有心理阔度,又要有审美温度等等高标准严要求的落实了。纵览《编年》,无论是作为学界翘楚的总主编,还是作为分卷主编的学界新秀或新晋博士,在遴选各自心目中的杰作佳篇时,颇多用心尽力。随手细读并核对了第二卷部分诗作的出处,明显看出编选者爬梳、校勘和择取之功力。这既体现出编选者的诗学标准与眼光,也凸显出编选者文学史观层面的有意识的努力,比如以小说名世的沈从文、老舍、吴组缃、蹇先艾等人入选,无论是人头还是篇目,数量还不少。这至少说明是编选者对既有文学史(诗歌)价值体系与意义系统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编选体例、诗学标准、文学史观念等等属于文学内部的技术事务,编选者尚能左右之,那么有一个外部问题则需要穿梭的时光和绵延的人群去检验:如何让新诗持久地活着,同时选本自身也获得某种权威资格?换言之,如果把编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文化事件乃至历史事件,那么编选这么一个大部头诗选的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效果?浏览《编年》,实事求是说,首先引发我兴趣的不是哪位诗人及哪篇作品入选,不是诗歌作品搜集、整理和遴选的水平高下,也不是编选者诗学标准的长短和文学史观念的是非。
事实上,这是一个摆在所有文学研究者面前的关于自身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很空。恩格斯评价拉萨尔的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提出过有名的“历史的”与“审美的”两大标准。考诸我国之历史与现状,我想还应该加上“世界的”这个标准。从这个视野看,《编年》的编选意图与预期效果至少是与之不悖的。《编年》总序所谈的六个问题:“一、写作资源与外来影响:‘白话’与‘新月’的两度生长;二、象征主义、现代性与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三、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四、边缘与潜流,现代性的迂回与承续;五、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六、经典化、边界实验,以及结语”,是以专业语言从专业表述层面,事实上也是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世界的三个维度,与之不谋而合。由此来看这部《编年》,其意义恰如总序所言,“或许可以部分地彰显了”。
如果说历史的、审美的和世界的是一种外在于作品本体的总体性要求与标准,那么这三个维度凝聚到作品本体作品自身,可以凝结为一个术语:经典。应该说,《编年》的编选意图和预期效果肯定不会局限于经典化,比如还有为研究者提供案头资料、为普通读者提供阅读渠道、为入选者有意无意排座座吃果果之类。我想,这些或许都不重要。对一个选本来说,在立此存照的同时,如何实现经典流传才是第一要务。在业内,有许多研究成果许多选本,被称为不刊之论或绕不过去的案头之作,被称为一时之选、不二人选。但历史注定要大浪淘沙,要说绕不过去的案头之作,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新华字典》更有资格呢?诗歌经典是人类的诗歌经典,体现的是深刻而普遍的人性内涵、时代精神、社会趋向和历史意识,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歌哭吟唱,是人类面对星辰大海时的怅惘与喟叹,更是人这个物种内在宇宙力量的凝练爆发。
这就涉及《编年》怎样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问题:在让入选诗歌永流传的同时,自身如何获得某种“经典”的资格?遥想中国诗歌鼎盛而璀璨的大唐,诗歌有四万多首,传唱至今者有多少呢?其选本自然也是汗牛充栋,名家选本更是百舸争流,可是有哪个选本能比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更深入人心呢?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尽管蔚然大观,但所入选诗歌肯定不能等量齐观,甚至也可以说是良莠不齐,还需要历史长河去大浪淘沙,需要星辰大海去遗忘与丢弃。如何在《编年》已有基础上,遴选出一部类似《唐诗三百首》的简明选本,是不是摆在主编面前更有挑战性的一个社会行为、历史行为与文化行为呢?
(作者:贾振勇,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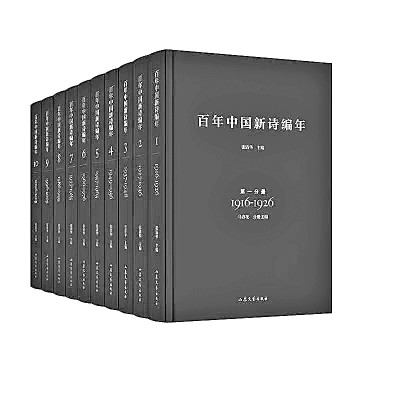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