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五百卷文献,尽可能“稀见”
光明悦读:近日,《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汉译文学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前,它的戏剧、小说、散文等卷也已出版。作为整套丛刊的主编,您能否介绍,是一套怎样的书,它的编辑缘起是什么?据您了解,当前我国近代文献的保存与分布,大致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
陈平原:“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是一套旨在收录与影印出版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丛书,拟用十年时间,推出数千种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图书,含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译作六大类。
相较中国古籍有系统的整理与出版规划,中国近代文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近代文献,被收藏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也有大量散落在海外,目前还没有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丛刊予以收录。考虑到大部分图书的纸张已十分脆弱,经不起再三翻阅,很多图书馆已不再出借。这个时候,采取必要的手段,以出版的方式,让更多作品能面世并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就显得较为紧迫。
晚清以降出版的书籍,近二十年虽也有不少整理与重印,但像“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这样网罗八方、规模宏大的计划,尚属首见。若能顺利完成,则能嘉惠学界,让更多人得以看见近代文献的原貌。
光明悦读:目前业已推出的诗歌100卷含260余部诗集,戏剧100卷含260余部戏剧,小说第一辑100卷含210余种作品,散文100卷含190余部散文集,汉译文学100卷含170余部小说或作品集,它们是从多少部文学作品中遴选出来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怎样的文学图景?
陈平原:已出版和拟出版的文学文献,是从约5万种文学书籍中选出来的。选择的主要标准是稀见性。当前已刊出的500卷,加上三联书店马上推出的文学研究40卷,共计有1000余部各类文学作品,约80%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再没印刷出版过。
梳理已出版的作品目录,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既有鲁迅、沈从文、冰心、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更多的是今天大家已不太熟悉的作家的作品。名家作品,其相关文集已有系统整理,并不稀见,只有较为珍贵的版本,如鲁迅《呐喊》的首版,我们会选进来。关于其余的作家及作品,我们的辑录思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不妨把眼光放远、门槛降低,让更多图书入围,尽可能扩大“保护圈层”。至于呈现了一幅怎样的文学图景,我认为是尽可能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
存一代史料,赓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
光明悦读:您在丛刊总序里写道,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且更为切近当下国人的习惯。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传统?
陈平原: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我不主张将“五四”局限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希望兼及1915至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
那么,什么是“五四”新文化呢?我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一种成功的“文化断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断裂”并非贬义。不仅“五四”,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全民族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都呈现某种对此前历史、文化的“中断”状态。近年来被隆重纪念的已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同样也是如此。
为何它是一种成功的“文化断裂”呢?第一,它并不局限于文化层面,而是牵涉甚广,尤其是在制度性变化层面。第二,它实绩突出,无论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还是制度建设,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贡献全都可圈可点。第三,它的断裂,包含着某种连续性,既不是全然的新,也不是纯粹的旧。第四,它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固守传统。第五,它兼及突破的勇气及弥合裂缝的自觉。第六,“五四”新文化人掌握了话语权,能实现自我经典化。第七,它从未被世人遗忘,而是引来不断的言说,成为一代代人精神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
茅盾曾用“尼罗河的大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适用于“五四”新文化。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保证。
光明悦读:怎么评价“五四”新文化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陈平原:今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专长,挑剔前辈的天真,甚至认为他们浅薄,其实,“五四”新文化人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文采飞扬、思想深邃、行动果敢的能力,是后世的我们很难企及的。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而不是“文艺节”,正是看重其青春勃发、上下求索的刚毅与雄健。“五四”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标杆——时代早已变迁,但其生气淋漓的生命形态,依旧值得今人驰想与纪念。
光明悦读:那么,“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怎样体现“五四”新文化的传统?
陈平原:丛刊只是史料,晚清以降产生的文学文本,我们尽量收录其中,还没做太多整理和研究。其内在的叙事逻辑、精神指向、审美情趣,外在的文本特征以及一段时期以来的发展路径等,还有待研究者发掘与阐扬。
光明悦读:那么,这套丛书编辑的目的,其实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您认为,史料之于学术,有着怎样的价值?
陈平原: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跟一个时代史料的发掘是互为因果的。有了新的史料就会有新的眼光,有了新的眼光才会有新的论述。在各个学科中,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这一规律有各种各样的呈现。比如说,我们想了解古代中国,会特别关注考古。考古史料的发现,会打开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新世界。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会特别关注报刊,报刊作为一种史料,其文本的采纳和研究思路的引进,会让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整体论述产生大的变化。
归根结底,史料乃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料积累,学界很难展开深入研究。在此意义上,存一代文献,乃学者及出版人的共同责任。
本固之后,新思方能涵育
光明悦读:您在小说与散文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以小说为例,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如何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范式?这条努力的路径,如何通过这套丛书体现出来?
陈平原:如果范式建立是指叙事模式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基本上是由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的与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两代作家共同完成的。前者以1902年《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正式实践“小说界革命”主张,创作出一大批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时人称其为“新小说”。后者没有小说革命之类的代表性宣言,但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标志,在主题、文体、叙事方式等层面全面突破传统小说的樊篱,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论断,提出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学里,中心文体是诗、词、曲、赋、文章等,但到了20世纪,小说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近代小说,被寄予了改良社会的厚望。要新一国之民,首先要新一国之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套丛书的整理,就有了关照社会变革进程的意味。
至于构建自身现当代文学创作范式的路径,如何通过这套丛书体现出来,我不敢下定论,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只是收录,文本特征还有待研究。
光明悦读:去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您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倡我们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自信。那么,如何建立学术自信?
陈平原:目前我们正在逐步建立对自身文化和学术的信心。这个信心,包含了对中国道路、中国命运的信心,也包含对中国学术信誉的构建。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甚至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忘本来、放眼未来,强基固本、涵育新思。
(本报记者 韩寒)(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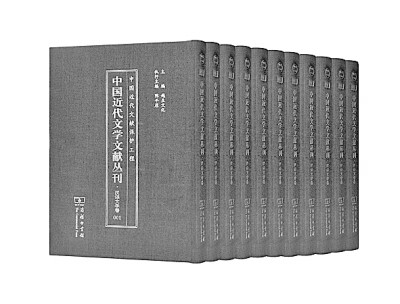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