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让人们眼睛一亮的词语:“美丽中国”。这个词语是古老的,它呈现在一代代中国文人的诗意想象中;这个词语又是崭新的,因为十八大将最宏伟的政治目标和人民愿景赋予其中。自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的丰富内涵便一步步成为现实。回望近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紧踏着美丽中国的节拍,描画着美丽中国的真实图景,从而收获了令人欣慰的文学之“美丽”呢?
1.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空间也开拓得更加宽阔
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们以极大热情讲述中国故事,从而让文学更亲近现实,更贴紧本土。近十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攻坚期,巨变的现实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能衡量作家的现实热情,也取决于作家的现实主义功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文学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经过八年持续奋斗,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有不少作家直接参与脱贫攻坚战,并创作出一批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有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杨遥的《大地》、温燕霞的《琵琶围》等,报告文学有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卢一萍的《扶贫志》、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秦岭的《高高的远古堆》、关仁山的《太行沃土》、蒋巍的《国家温度》等。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事件中,文学同样交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李春雷的《铁人张定宇》、程小莹的《张文宏医生》、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刘诗伟和蔡家园的《生命之证》、何建明的《上海表情》、黄春华的《我和小素》等,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诗人们更是谨记“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古训,以诗歌记录人们在抗疫期间的心灵律动,为人们构筑起一座坚强的精神堡垒。
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空间也开拓得更加宽阔,这是十八大以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在这期间,先后进行了第九届和第十届的茅盾文学奖评奖,茅盾文学奖以倡导现实主义为主旨,我们从这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获奖作品基本上遵循着以现实主义精神去观照世界,在表现方式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梁晓声的《人世间》以个人精神史的结构反映出改革开放的时代轨迹;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跨越百年社会变迁,探询人的精神世界;李佩甫的《生命册》从农民与现代性的关系入手,书写半个世纪来的中国城乡发展史;王蒙的《这边风景》以乐观姿态对特殊年代新疆多民族生活进行了清明上河图式的描画;陈彦的《主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塑造出一个从乡村弱女子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演员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学典型性。这些都得益于作者洞察现实和历史的敏锐目光,以及现实主义的叙述能力。同时,这些作品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徐怀中是军旅文学的一名老兵,他在军旅文学大合唱中一直带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这种音符是一种浪漫情怀和对美的憧憬,正是这种“不安分”孕育出《牵风记》。金宇澄的《繁花》则是用沪语泡出的一壶浓茶,飘逸着上海弄堂的日常情趣。徐则臣作为年轻的“70后”,从《北上》可以看出这一代作家所具备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这又分明是他亲近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结果。苏童和李洱都是当年先锋文学的主力作家,但他们在各自的作品《黄雀记》和《应物兄》中充分吸收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优势,同时自如施展他们处理文学资源的先锋性。总之,我们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有机融合与相互对话,或者说,这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浑然交响。
现实主义深化意味着思想的深度和锐度。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的优秀与否,不在于作者是否抓住了一个重大题材,而在于他面对写作对象时是否有思想的发现。如何建明的《革命者》,内容是在上海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们的事迹,但作者通过对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革命史的再一次叙述,重新阐释了革命者的意义,警示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革命者的精神。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则是借深圳的改革经验探讨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的大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具有特别强烈的生态意识,他们直接干预现实的生态和环保问题,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生态题材作品,如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胡平的《森林纪》、任林举的《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和探秘》等。
思想性更是长篇小说的灵魂,在思想性的开掘上作家们也留下了可喜成果。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通过年轻人爱情危机的故事,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倡导爱的世界的新词——“爱历元年”;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以藏区牧民生活为题材,用孩童的视角展开描述,蕴藏着作者对自然环境、人性伦理、生命存在的深刻反省和理性思考;鲁敏的《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思想点都给人们带来新意和启迪。
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艺术目标是塑造独特的文学人物形象,但受现代小说的过度影响,一些作家不再把塑造文学人物形象作为自己追求的艺术目标。这一现象在近年来的创作中有所改观,一些新的文学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笔下诞生了。如阿来的《云中记》中的藏族祭司阿巴,这是一个由生态意识凝聚成的人物形象,他对大自然的整个生命体系有着一种哀怜之情;胡学文的《有生》以大胆的文学想象塑造了祖奶这一民间接生婆的人物形象,她的灵魂里包蕴着所有关于生命的民间信仰;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中的赵秀英是一位革命战争中的支前队长,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但作者将其塑造成一个闪耀着革命的神圣光芒的文学形象;周瑄璞的《多湾》塑造了一个始终跟不上现代化节奏的乡村女性形象季瓷,但她身上坚韧和坚贞的精神又显得弥足珍贵。
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开拓也表现在小说观的突破和更新上。王安忆始终在小说艺术上精益求精,她的《一把刀,千个字》写一位淮扬菜厨师,精湛的厨艺和酽酽的知识分子情怀完美地融入叙述之中;东君的《浮世三记》以反故事的方式寻求突破,又处处表现出一种对文学的敬畏之心。
2.作家们把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文学是能够抚慰人的心灵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的精神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家们把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了作家以积极的姿态回应现实,作家们的这种努力也大大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
诗歌是最具精神性的文体,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诗人们仍然通过沉下心的现实关怀和对总体性的追求,开垦出一片精神的沃土。比如,工人诗歌和打工诗歌的兴起,就在于诗歌真切地倾吐出打工者的心声。又如,张执浩试图重新建立起诗歌与个人、时代、民族、国家的关系,他的《无穷小》从个人生活经验切入,直抵人类生存的复杂体验;他的《高原上的野花》在日常性中探寻人性乃至神性。最近几年,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写起了长诗,这其实是一种追求更丰富的精神内涵的反应,因为诗歌的长度本身就意味着难度,也意味着一种总体性的建构。近些年的长诗代表作有张学梦的《伟大的思想实验》,刘立云的“战争三部曲”《黄土岭》《金山岭》《上甘岭》等。张学梦的长诗颇得政治抒情诗的神韵,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视,让个人与时代和谐共振。刘立云的“战争三部曲”被诗评家称为“历史之诗”,“是人与历史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
追求丰富的精神内涵在散文写作中也显得非常突出。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讲述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他仿佛置身其中,感知他们的生命温度,展现他们的高贵和尊严,他那真诚的文字里充溢着对人民性的伦理情感。周晓枫的《巨鲸歌唱》书写的是个人成长印记,传达出对衰老、死亡、嫉妒、孤独等生命体验的感悟,以敏捷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边界。
有不少作家一直关注精神现象。如蒋韵在小说中经常表现救赎的主题,她在《晚祷》中写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姑娘要为她小时候的一次无意过失而进行自我惩罚,以这种方式来救赎自我。她在《你好,安娜》中所写的几个年轻人相互纠缠的青春岁月和爱恋既关乎承诺,也关乎救赎,是一种让人的精神获得净化和洗礼的叙述。张炜的《艾约堡秘史》也是一部关于救赎的小说,他为经济时代的“当代英雄”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对人性的叩问和对人心的探询,是很多作家的基本主题。东西的《回响》以一桩案件侦破为线索,将案件推理与人物心理轨迹作为互文关系来推进情节,从而触及人性情感最隐秘处,所谓回响,是纷繁现实投射到人的内心时,作者心生悲悯和大爱的反应。
寻找主题,也是精神性的重要入口。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可以说是她的一次自我精神的寻找。她非常自如地将寻找主题与她温暖、善良的日常叙事糅合在一起。过去她的精神依托主要在故乡,这一回她终于寻找到了内心沉睡着的城市精神。孙惠芬在《寻找张展》中也确定了寻找这一主题,从而将一个关于中学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意。
3.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写作中具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自从一百多年前中国新文学诞生,“世界文学”这个词语一直刺激着中国作家的大脑。中国社会开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了“走向世界文学”的焦虑,到今天,我们逐渐增强了文化自信,焦虑变成了行动,要努力实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文学本无国界,只要全世界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块文学土地,连接起来将无边无际,丰富无比。”2015年,铁凝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的对话和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同样可以佐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写作中具有了一种世界文学的眼光。
说到世界文学的眼光,应该关注王树增的《抗日战争》,这部作品采用宏大的历史视角,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山河破碎、艰难困苦、牺牲巨大的历史现实下如何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书中既展现出澎湃激昂的爱国热情和对抗战英烈慷慨赴死的礼赞,也有对法西斯凶残暴行的揭露和批判,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严肃冷峻的深刻思考。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可以与世界各民族的战争小说进行对话的中国文学作品。作者具有宏阔的胸襟,他将香港保卫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二次世界大战因果链中环环相扣的存在,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思考的深度和视域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都是非常稀有的。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停留在揭露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上,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来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复杂、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一条是今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而且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心——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钟求是的《等待呼吸》试图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让一位中国年轻人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刻爱上一个姑娘的同时也爱上了《资本论》,现实不仅在考验爱情的坚贞性,也在验证《资本论》的真理性。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激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估和认识,并将重点放在从世界文学的视域来思考和总结莫言的创作与中国经验,大家认为,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作家正是在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本土性构成紧张关系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他们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立足于中国大地,同时具备了面向世界的眼光。自获诺奖后,莫言在创作上更为严谨,也更为成熟。他的中短篇新作集《晚熟的人》便体现出他小说观念的新变,他以赤诚之心回归本乡本土,在叙述上由奔放进入收敛,更显思想的深沉,在他对故乡特殊情感的书写中传递出的是对人类共同性的向往。
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和胡丘陵的《戴着口罩的武汉》是两首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反思的长诗,两位诗人不约而同地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行反思,前者从大处着眼,气象宏阔;后者从人民生活细微处入手,气韵绵长。两位诗人忧人类之所忧,关注人间疾苦和人民福祉,共同表达出生命家园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
阿来的《云中记》是将地震置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下来理解的,他就像热爱人类一样热爱大自然。小说写祭司阿巴回村子祭奠地震中死去的亡灵,同时也是在与大自然对话。小说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且开启了生态人道主义的叙述。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具有神圣性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主人公赵秀英身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人性之善之美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朱秀海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重新阐释了革命人道主义。王蒙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历史认知,凝聚成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这在他的长篇小说《笑的风》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王蒙从开始创作起,就以重视人的价值和维护人的尊严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同时他是以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乐观性也是他坚定的理想主义在人道主义精神上的具体呈现。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它所呈现的文学发展态势是积极乐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描绘的美丽中国将会更加迷人,它将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道壮丽风景。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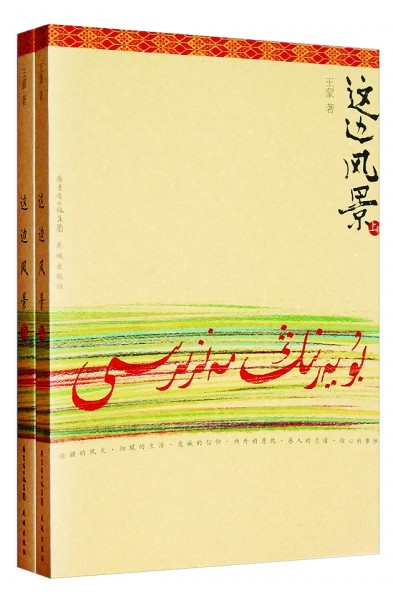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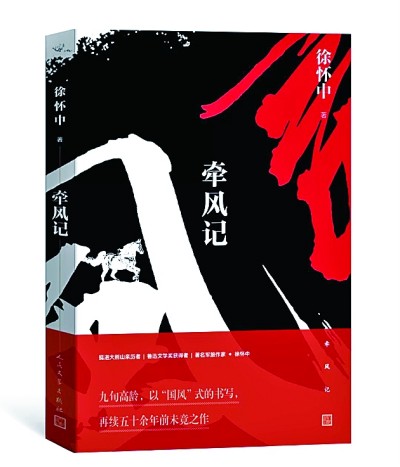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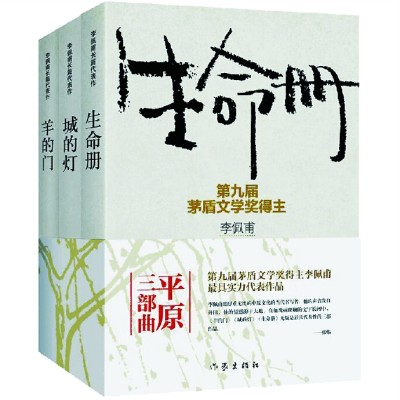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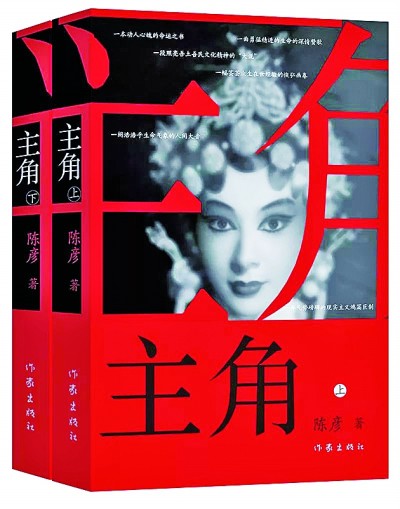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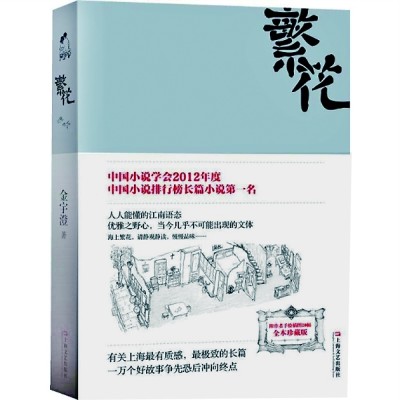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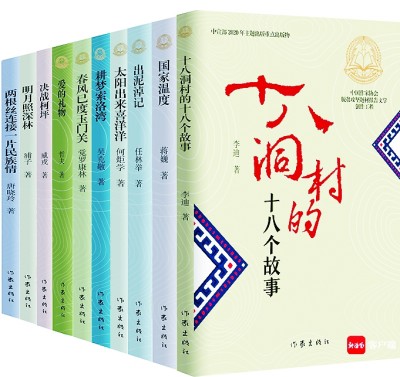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