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论者们发表过种种意见。魏晋玄谈中有“三语掾”的故事:“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世说新语·文学》)“将无”是虚词,阮宣子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同”字。这一看法在古代有其代表性,历代解《庄》者中,就多有以儒释《庄》者。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立论曰:庄子对孔子是“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这是说庄子在字面上是批评孔子的,但实际上是支持孔子的。在当代论者中,最流行的看法是,《庄子》与儒家是对立的,由此又衍生出儒道互补论来。
我的看法与上述看法都不同,我以为从传世《庄子》文本的编排次序来看,庄子学派是先批判儒家思想,后又与之在一定程度上相融合的。兹略述之。
一
《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逍遥游》篇已发其端。《逍遥游》篇在讲到“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时曰:“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此句谓神人的尘垢秕糠,就能造出治世之圣君尧、舜来,怎么肯把治理外物当回事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尧、舜的极度鄙薄,二是不屑于治世。这两点对《大宗师》《应帝王》以及《外篇》之批判尧、舜与治世的一些寓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逍遥游》篇在与儒家思想的对立上,只是发端,并没有展开。
《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三篇均未及于此,虽然在这三篇中,庄子与儒家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比比皆是。《德充符》篇则重又表现了儒道的这种明显的对立,并且比之《逍遥游》更多了一些理论的内涵。
《德充符》中无趾的寓言表现了儒道两家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其曰:“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答曰:“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所谓“尊足者”之“足”,指形体也,指被刖也。因此高于足者,自当是指精神,指一种对于人生灾难的超越。这里展开的正是以超越的态度对待生活与以智识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矛盾。所以,无趾对老聃说:“‘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句谓孔子还不是至人,他何必求以奇异幻怪之名,闻动四方,欲弟子之盛也,他不知道至人正是将此视之为自己的桎梏的吗?这一寓言体现了儒道思想的明显对立。
《德充符》篇中的哀骀它寓言,更将这一对峙引入了政治论的范畴:在这一寓言之末,庄子借鲁哀公的感悟说明:执纲纪而仁爱其民,乃“轻用吾身”的表现,并会造成亡其国的后果。《养生主》篇曾述保身、全生、尽年的三项要求,“轻用吾身”正是“保身”之反面也。
《大宗师》篇则就生死问题,展开了庄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孟孙才居丧的寓言,是使丧礼徒有其仪式,而无其伤痛之实情。意而子见许由及颜回坐忘这两个寓言,则以大化刊落了儒家的仁义礼乐。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大宗师》篇对仁义作了正面的批判。在“意而子见许由”的寓言中,许由对尧教导意而子所说“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的话,回答说:“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成疏:“恣睢,纵任也。转徙,变化也。涂,道也。夫仁义是非,损伤真性,其为残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尧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复能遨游自得,逍遥放荡,从容自适于变化之道乎?”(《庄子集释》)
《应帝王》篇写了一则天根问无名人如何治天下的寓言。天根适遭无名人而问:“请问为天下。”“为天下”,治天下也。无名人斥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走开!你这个鄙陋的人,为什么问这个让人不高兴的问题!这一回答显然直承了《逍遥游》神人不屑于治世的意蕴。
由于《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以及《应帝王》篇从个体存在论上升到政治论的理论发展,这就提供了一个《庄》学与《老》学的汇合点。由此开启了《外篇》中《老》学进入《庄》学的景观。
二
以现存序次,《外篇》首四篇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大体皆主绝圣弃知,绝仁弃义,显然都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我们在这四篇,特别是《胠箧》《在宥》二篇中所看到思想流派的相互关系是:一方面是《庄》学与《老》学的汇流,一方面是《庄》学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激烈批判。
《骈拇》篇“骈拇枝指”“附赘悬疣”的比喻,已表明这是从其本身之性分出发来阐述的,故其主旨乃在阐述“仁义其非人情乎”,而以天下之常然作为对照。
《马蹄》篇则是从被治则伤性的角度来着眼的,所以其以“至德之世”作为善治天下者的榜样。《马蹄》篇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圣人的激烈批判。其中最为突出的几句为:“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道德者,与《德充符》所曰“天鬻”一词同义,天生,天然是也。天性犹存,又何取于仁义!“性情”,即《骈拇》篇所谓“性命之情”,此处当解作天然状态。若没有离开天然状态,则要礼乐何用!这一段话在激愤地否定了儒家的仁义礼乐后,进而将天然状态的毁损,归罪于圣人之推行仁义。
《胠箧》篇对仁义、圣人,对知的批判,都更为激烈,直接以巨盗、大盗为批判对象,锋芒所指乃在于如田成子之窃国为诸侯者也,对社会的决绝感更为深重,并认为天下大乱乃“上好知之过”。
《胠箧》篇揭示了统治者对于道德知识自私的把持和运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盗国者违反仁义,却又以仁义自保,且以治国,故谓“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句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两面性——他们在谋取私利时,对于自己提倡的道德是根本不管的,却又以这种道德来钳制人民,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既是破坏者,又是垄断者。本篇首先揭示了这种现象,它对于唤醒人民、保护民族利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在宥》篇在描绘社会之残象以及对于儒墨之痛斥上,为《庄》书之最。其曰:“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
“以仁义撄人之心”的结果,使得人的自然天性败坏了,各趋一端,此“大德不同”之谓也。自然天性既然败坏了,那么“性命烂漫矣”,亦即出现了上述社会衰败的种种表现。成疏:“烂漫,散乱也。”(《庄子集释》)章太炎说:“‘求竭’即胶葛,今作纠葛。”(《庄子解故》)章说是。“儒墨毕起”,即为天下好知之体现,于是,人与人之间纠葛多矣。这一段话说明以仁义撄人心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从表达上说,似是对历史事实的回顾,其实是为了论证的需要,结合神话传说的资料所作的虚构的历史叙述。
三
当“无为”观的内涵为“无为而治”时,庄子学派对于意在治世的儒家思想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当庄子学派将自然之道与大化观注入“无为”观中,从而兴起了以无为大规模地整合有为的努力之后。儒家的仁义思想就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要被整合的一项对象了。
于是,我们看到在《天道》篇中,仁义成为九个层次中的第三个层次了。其第一个层次“天”,自然也。这九个层次“必归其天”的“天”,乃天性也。显然,这一整合不过是将仁义等七项纳入到庄子学派观念的框架之中。
《缮性》篇的意向深入了一层,欲以庄子学派的观念从内涵上来改造儒家的核心概念,使之《庄》学化。
《缮性》篇曰:“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这一段话从肯定性的推导竟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即从和理到德、道,到仁、义与忠,再到乐、礼,结之于天下大乱。为什么会这样,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对这一段的文字作出训释。
“知与恬交相养。”安命论的知及其人生态度是相互促成的,此“交相养”之义也。“而和理出其性。”“和”者,和同也。句谓此种齐同的认识和胸襟,就如同出自天性一样。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此种齐同的认识和胸襟既然如同出自天性一样,那么这种认识和胸襟就会以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体现出来,这样它就似乎表现为一种“德”。德无不容,正是齐同万物的体现,然而在本篇中却被说成是“仁”。
“道者,理也”的解释便是下文所说:“道无不理,义也。”从自然之道出发,能使君正、官治、君臣之义明、万物之应备。义者,宜也。凡物各得其所,谓之宜。“义明而物亲,忠也。”物各得所宜则物相亲,此谓之忠。按照庄子学派的思想,物各得所宜,即是各按其天性而生活,无所谓相亲与否。而本篇则以为,各得其所宜可以使物相亲,物相亲即是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各得其所宜并非各按其天性生活,而是各得其序,本篇之“义明”实际上就是《天地》篇所说“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之“义明”也。此“义明”,乃君臣各得职分之所宜也。这样的“义明”可以使君臣关系亲,这种亲密的关系,谓之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治理而使物各有序,谓之“道无不理,义也”。
“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中纯实”者,即指“夫德,和也”。详细一些说,便是如同出自天性的对于万物齐同的认识和胸襟。以此种认识和胸襟处世,而外物亦以此种态度反作用于你的性情,因为双方都和顺相容,你就会感到愉快,此谓之乐也。
“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信者,诚实;容者,仪容,指服饰冠戴等。“文”,“节文”,此处指礼节、仪式。行信体容而又顺乎节文,则为礼也。
“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正”字当与《逍遥游》篇“乘天地之正”之“正”同,训为性。“蒙”,受也。“彼正而蒙己德”,是说彼民之有常性受之于自己之天性,亦即民性是天生的。“德则不冒”,是说天性是不可以被礼乐所覆盖的。“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如果要以礼乐去加以覆盖,则人必失其天性。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缮性》篇为何从肯定性的推导竟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了。
本篇作者对知恬交相养的论述,既是为了限制儒墨的求知观念,同时又是为了引入庄子的齐同观。德无不容,正是齐同万物的体现,然而在本篇中却被说成是“仁”,便是作者以万物齐同这一庄子的重要观念来改造“仁”这一概念的表现。用“道无不理”来解释“义”,因为《天地》篇中已然有可用的论述,故还能够说得通。到了要改造“忠”这个概念时,本篇作者的论述,就与《德充符》《刻意》篇产生了不同,但也还有《天地》《天道》两篇之论述可以提供支撑。
再往下改造的概念应该是“孝”,但庄子学派对于生死所取乃大化周流的物化观,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是无法相容的。因此,作者便跳了过去。
“中纯实”一句其实是直承“夫德,和也”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以庄子的齐同观来改造“乐”这个概念。这一改造的结果是作者的论述与《在宥》《天道》篇都不相同,而又从以前各篇中都找不到理论的支撑了。体现作者这种窘境的是,在对“礼”的论述上,作者已经无法体现庄子学派的色彩,而与儒家无异了。
应是本篇作者明白,自己对“乐”与“礼”的《庄》学化改造是失败了,于是,乃回过头重新使用儒家原有的“礼乐”概念,并对之作出批判。这就同上文试图将儒家核心概念《庄》学化的意向来了一个大的转折,这样一个转折给予人们的印象便是:从肯定性的推导竟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
四
《达生》篇标志了《庄子》纳入广泛的社会世俗内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之明朗化。随着社会事项的大量涌入,“为”的话语势必要抬头,于是,在《杂篇》中,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有了调整,作出了新的结合。
在庄子学派的思想渐次变动的背景下,儒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必然的。由《缮性》篇发端的对于儒家概念的改造,在《杂篇》开头两篇对“诚”这一概念的改造中获得了成功。
《庚桑楚》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在南荣趎问道的寓言中体现十分明显。其中,庚桑楚对弟子所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的话,其批判的力度直追《在宥》篇“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那一段话。《庚桑楚》还以“至礼”“至义”“至知”“至仁”“至信”批判了儒家的相关思想。
然而,其第二段第一层,却将“诚己”与“独行”联系了起来,在主要说明人应以其天性而生活的论述中,融合了儒家的诚敬慎独的思想,这种主动吸取儒家思想,从而使儒、道思想呈现出既斗争又融合状态的情况,在《庄》书此前各篇中是不存在的。
《徐无鬼》篇徐无鬼第二次见魏武侯的寓言,从伪行的角度批判了仁义。徐无鬼对魏武侯说:“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统治者伪行仁义,后者必仿而造之,从此生事,最终导致失败。《徐无鬼》篇又对儒士之三个方面作出批判,将之拟人化为三种人并以形象性的描绘出之:暖姝者、濡需者、卷娄者,这是一个新的概括。
另一方面,《徐无鬼》篇对于意思同于《庚桑楚》篇“诚己”的“诚”字则用了三次。“诚己”者,真实的自己,即以其天性生活的人。虽然注入了庄子学派自己的含义,但两篇都加以了使用,仍然表现了对作为一个儒家概念的“诚”的接受。
在《则阳》篇中,这样一个改造儒家概念的趋势,仍然得到了继续,这体现在下面这句话中:“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这是说圣人爱人不能出于有心,而应出于天性。民众对于无心之爱能够安心接受,因为此种出于天性的无心之爱类同于无为,上无为而民性安。以“无心”来限定的“爱人”观念之被肯定,这仍然是庄子学派对儒家概念在其被改造之后的接受。摈斥仁义,是《庄》书一贯的论旨,但“爱人”就是“仁”。
对儒家个别概念作吸收改造的动向在《让王》篇仍然存在。本篇中寓言人物伯夷、叔齐所说“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一语所表达的,便是一种糅合了儒家“忠信”思想的无为而治的观念。
但《让王》篇的特点,恰恰在于本篇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本篇作者在第一段虽仍然坚持庄子学派重生的思想,并承继了《在宥》篇“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的观念,但本篇作者在第二、三段中则已经醒目地直接采用了儒家的观念与立场来说话了,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第二段中,本篇作者直接采用了儒家的观念与立场来说话,主要体现在: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原宪、曾子都是得道者的形象,本段的主旨是讲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在第三段中,瞀光以仁、义、廉作为评论的准则;伯夷、叔齐所说“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的话;以及北人无择、卞随、瞀光、伯夷、叔齐之以节义自许以至于以死殉之之举:皆为儒士的观念及其行事也。
这已经不是对儒家的思想概念作《庄》学化的改造了,而是直接向儒家的思想观念与立场敞开了大门。
由于儒家思想的大举进入,于是产生了一个与《杂篇》中不绝如缕地持续进行着的吸收并改造儒家思想的个别概念相反的动向,这便是庄子学派概念的儒家化。“逍遥”是庄子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在本篇“舜以天下让善卷”的寓言中,善卷在答语中将耕作生活称之为“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当为隐于田者之逍遥。善卷之谓逍遥,即颜回之谓自给自足、自娱自乐也。
既然“诚”字,在《徐无鬼》篇中已训为真,作天性讲了,那么它就与庄子学派的“真”的概念切合了,《渔父》篇正是循着《徐无鬼》篇的上述意脉,将“真”定义为“精诚”的。
虽然《渔父》篇仍有对孔子“审仁义之间”的批评,却又将“忠孝”纳入了“精诚”之中,在“孝”前加个“慈”,“忠”后加个“贞”,如此,孝与忠便出自本性了,亦即具有了“真”的意蕴。儒家思想的关键概念“忠孝”便与庄子学派的思想相融为一体了。
而至《天下》篇,作者论锋批判最利的为墨、法、名三家,对于儒家则取肯定的态度。
(作者:王锺陵,系苏州大学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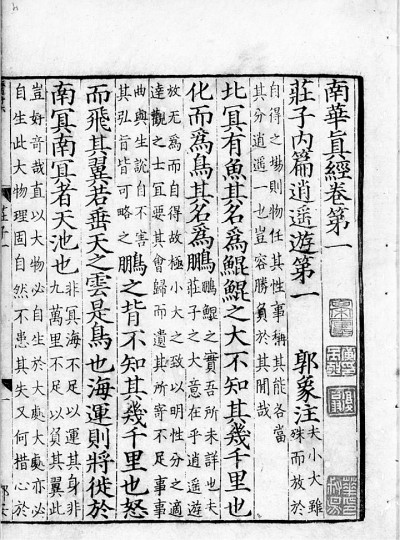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