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读书会】
编者按
1942年,著名作家萧红在香港去世,结束了短暂而凄苦的一生。《马伯乐》作为她最后一部未能完成的作品,成为众多热爱萧红作品读者的一大遗憾。
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老舍、杨绛、莫言、毕飞宇等作家的多部作品,均是经由他的翻译进入西方世界。此外,葛浩文一直钟情于萧红的创作,多次翻译其作品,并撰写了多部研究萧红的著作,堪称萧红穿越时空的跨国知音。70多年后,葛浩文用英文续写完成《马伯乐》,并由其夫人林丽君教授翻译成中文。近期,完整版《马伯乐》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隆重推出,成就了一场穿越时光、连通中西的文学佳话。
9月16日,来自中外文学界、汉学界的众多嘉宾云集一堂,就《马伯乐》完整版各抒己见。本期《光明读书会》特整理其中发言的精华部分,与读者分享。
嘉宾
葛浩文: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马伯乐》续写者
顾 彬:德国汉学家、翻译家
安乐哲:美国汉学家、翻译家
李 岩: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锦琦: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副主任
雪 漠:作家、文化学者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王 宁:清华大学教授
他把萧红带到西方
葛浩文:大概50年前,我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文感觉有一点枯燥,就想找现代文学看看。到图书馆看上了两本,一本是香港再版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另一本就是萧红的《呼兰河传》。我对这两本书看得爱不释手,因此决定去研究萧红。于是我转学到了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的学校,写了一篇关于萧红的论文。
毕业后,我开始翻译《呼兰河传》。萧红的作品看起来语言很简单,但是要想抓住她的情感和思想,是很难翻译的。之后我又翻译了《生死场》。这些作品出版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仍然不断重印,现在美国还有人在看萧红的作品。
1980年,我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好几天,然后又去到哈尔滨呼兰,看了萧红的故居。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毛笔字,但是在那里写了“怀念萧红”几个字,现在还挂在萧红的博物馆里。
《马伯乐》我翻译过,但是没有出版,因为是不完整的。刘强先生在香港又发现了第二部,是刊物上发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最后有八个字,“第九章完,全文未完”。我知道这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但是我为了萧红还是翻译了已有的部分,之后就搁置了。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我是做翻译的,没有写过小说,但后来我开始写一个小小说,写着玩的,最后凑了100多篇,后来出版了。书第一天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一个作家了!我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应该续写,而我的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做一点值得的事情,于是我就这样去做了。
李岩:萧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31年的短暂生命和巨大成就形成鲜明的反差,她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作品,为中国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民立传,体现了文学悲天悯人的动人心魄以及文字背后民族大义的情怀。《马伯乐》是萧红生前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方面令她的读者们感到惋惜,同时也像高山流水一样,召唤着期待着后世的知音。
葛浩文是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通过他的精妙译笔介绍给国外读者的中国作家,包括杨绛、老舍、莫言等数十位,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葛浩文与萧红,乃至与东北作家群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渊源已久,这也令人感叹葛浩文行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开放胸襟,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深爱。葛浩文在续写《马伯乐》之前,用英文书写了《萧红传》,此外他还写有多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文集、随笔集等。葛浩文不仅把萧红带到了西方世界,而且推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体现了中西文学在当代的交融和互动。
这次续写完成萧红的未完成之作,并由其夫人林丽君翻译成中文之后出版,可说是完成了葛浩文的一个夙愿,也完成了一次跨越世纪的对话。葛浩文用英文续写,十分考验译者的中文功底,林丽君的翻译十分贴近萧红的语言特色,为中文版的续写增添了亮色。《马伯乐》(完整版)所完成的中西作家跨越世纪的书写与对话,是非常值得庆贺和纪念的世界文学史的佳话。从1941年到2008年,萧红在上个世纪未书写完成的作品,在本世纪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版本,跨越世纪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锦琦:文学交流是推动文明互鉴、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版图中非常独特的基因片段,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浓缩。因此,中国文学在海外的阅读与研究状况也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一方面,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群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上世纪70年代,葛浩文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读书时就被萧红的文学世界所吸引,其后他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柳亚子先生之子、旅美法学家柳无忌。柳无忌曾向葛浩文深入介绍萧红的作品和她的坎坷经历,促使葛浩文与萧红产生了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情感,并最终促使葛浩文将萧红研究作为终生事业,陆续创作和翻译完成了英文版《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和一系列学术专著论文,为萧红文学作品的世界性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雪漠:萧红非常幸运,有葛浩文和林丽君这样的朋友研究和推广她的作品。这个世界上能得到这种幸福的作家不多,无数的作家,像秋风落叶一样被吹走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好,而是缺少像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的发现和传播。中国文学能够进入英文世界以及更大的世界,就是因为有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
《马伯乐》因为葛浩文的续写得到了升华,同样中国文学也因为葛浩文和林丽君艰辛的劳动能够为世界所知,这是他们为世界留下的最美好的礼物。能够和一些这样优秀的翻译家相遇,并且从中汲取到对文化和文学的信仰精神,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心中多一份温暖。
好翻译使好作品获得新生
顾彬:翻译是艺术,好的翻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如果没有人把复杂的德文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中文,就没有新中国。
在德国和德语国家,甚至在欧洲,葛浩文已成为一个品牌,无论他翻译什么,德国出版社都会马上决定要出德文版。没有葛浩文,德文版的萧红作品是不可能出版的。
葛浩文跟我的友谊已经30多年了,他为我们打开了认识萧红的一扇门。我和我的学生因此开始用德文翻译了萧红几乎所有的作品,卖得都很快。这些作品在德国的读者大都是女人,不是男人,因为女人需要有她们自己的世界。
安乐哲:据我的了解,西方最杰出、最著名的思想家,不管是什么学科,都非常赞赏中国。中国的很多作品已经进入了西方的世界和体系,但也还有很多没有被翻译成英文。
葛浩文的成就在于,他把中国的现代文化传播到了外国。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他跟一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合作的结果。这些作家包括萧红和后来的莫言、毕飞宇等等。
跟葛浩文的研究范围不一样,我是把中国的哲学经典翻译成英文,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外国。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外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语言基础,而把中国的哲学经典翻译成英文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很努力地向葛浩文学习。
王宁:葛浩文通过跨文化、跨世纪的书写,完成了萧红未完成的作品《马伯乐》。这正好又实现了他本人的理念——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改写,特别是伟大的翻译家,能够使本来很好的作品变得更好,而拙劣的翻译家有可能把很好的作品破坏掉。
另外一位汉学家多年前曾经说过,中国文学为什么长久以来不能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重视,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译者。上世纪30年代,如果鲁迅的作品能被翻译成好的英文或者其他语言文字,他可能早就获奖了。
优秀的翻译家不仅是重新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创造,并且使得原文具有了持久的生命。我曾经在许多文章当中都提到,如果没有葛浩文的翻译,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是被延误的。也许有人说他不翻译别人也会翻译,但别人的翻译不一定能把莫言原文的意韵转化出来。中国有一批很优秀的作家,莫言只是其中的一位,只不过他们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文。在此向葛浩文先生致敬。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从事世界文学研究,从事世界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引进世界文学的理念和概念。歌德当年为什么留下许多世界文学著作,就是因为他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作品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之后突发奇想,感到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过了若干年之后,美国的理论家又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新界定,说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得。正是那些辛勤耕耘的翻译家,使得在一种语言语境之下的优秀作品,在另外一种语境之下获得了新生,具有了持续的生命。
这一点已经被葛浩文续写萧红证明。萧红已经离开了我们几十年,当下80后、90后的大学生已经不太知道萧红了,但是葛浩文用英文续写《马伯乐》,再由林丽君翻译成中文,可能会使萧红的这部《马伯乐》在中文世界和英语世界获得新生,并且具有来世的生命。
用续写完成萧红的生命觉醒
雪漠: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是一个引起了许多惊叹和感慨的人物,在她所处的时代,发出了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的光芒。这不仅仅是才华的光芒,更是一种心灵的光芒。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大家,对于萧红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光芒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共鸣与相通。这份纯粹与乐观,在《马伯乐》这部作品的续写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得到。
《马伯乐》是萧红生命的觉醒,但从她的书中完全读不到一丝一毫的个人痛苦和哀怨,而是以一种有趣的眼光消解这个世界的荒淫与黑暗。这就是萧红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
在葛浩文续写的部分,这种精神得以完整延续,并且得到了升华。从写作角度来说,续写在某种程度上更难,因为续写的不仅是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延续原作者的气息和精神。这一点正是葛浩文续写《马伯乐》的最成功之处。
书中马伯乐的命运结局,如同一首命运交响曲的最后乐章,达到了升华的顶点。他的命运交响是悲剧,而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却达到了最华美、最灿烂、最喜悦的层次。葛浩文的续写完成了萧红的生命觉醒与乐章,令人感动和赞佩。
陈晓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葛浩文的翻译作出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非常卓越,甚至可以说无人可与之比肩。
这次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的续写,是现代文史和当代文学史贯通的一个佳话。他研究萧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对文学的理解,给中国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树起了一个典范、一座丰碑。我非常喜欢萧红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葛浩文对萧红的研究。
《马伯乐》的续写和翻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再创造的实验,丰富且独特。葛浩文是美国文化背景,一生热爱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萧红;夫人林丽君有台湾背景,也有欧美学术背景,并且保持了国学的传统。
葛浩文对萧红的理解特别深入,因此非常能够体会萧红的语言风格、人物性格,以及对故事发展的设置。《马伯乐》隐含着萧红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在和鲁迅先生进行对话。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体现的是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后面临的惶惑和困境,而萧红是想通过马伯乐,来观察在民族国家遭遇苦难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什么一种表现。因此,萧红是秉持着鲁迅先生国民批判的眼光,来写马伯乐这样一个让人可恼、可恨、可笑、可悲、可叹的人物。
葛浩文的续写非常精彩,我相信在鲁迅先生的精神指引之下,最后萧红的本意一定是要对马伯乐的命运和选择做出一个决断的。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葛浩文不只是理解了萧红,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了中国,而且内心充满了热爱。
续写对马伯乐的处理是理想化的。这个人物虽然懦弱无能,在不断的逃难中始终满足于一时的口腹之乐,但是越到后面越滋长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续写一方面延续了马伯乐的软弱和冷漠,但另一方面,民族情感使他最后一定要站起来。葛浩文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成长的过程,完成了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他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当然,这部作品我们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非常大,我相信肯定也会有一些质疑。例如葛浩文的续写和萧红的风格有些不同之处,比如在小说人物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故事和系统的逻辑方面,萧红写得非常随性、放松,有时会显得不太合理;而葛浩文比较强调逻辑性和理性,更注重让故事情节合理地去发展。
(本报记者 吴娜 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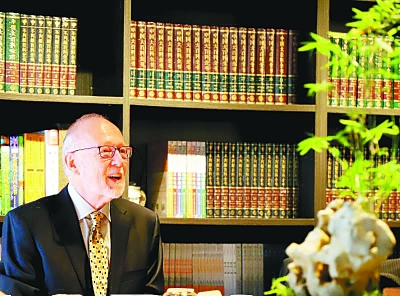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