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作家周健明的《柳林前传》出版。30多年后,《柳林前传》再版,并与《柳林后传》共同组成《柳林传》。
《柳林前传》刚成书时,农村的经济改革刚刚萌动,书中的乡办企业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尚属新生事物。当年,我在评论《柳林前传》时,提出过“双重清醒”:“一重是对‘金本位’造成人的异化的警惕,这一条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另一重,则是对‘金本位’的批判中,可能造成‘权本位’的返潮,倒退到‘人的依附性’上面,这条,却是乡土文学中尚未意识到多少的……”《柳林后传》进一步加大了这“双重的清醒”。“下桩宴”一章,厂长刘斌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表面是让县工业局接管厂子,冠冕堂皇“落实政策”,实际是“避险”。这一章,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还是对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代收店则有着不同的遭遇。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工作组长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读到这里,我思索了很久,毕竟,形象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美学上有“立象已尽意”之说,也就是讲,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要剖析形象及背后的一切,思维甚至都为之苍白。好在这20多年的历史为这些形象做出来很多具体、鲜明的注释。
诚然,乡村也在变化,如《前传》中颇具有典型意义的冷满爹、凹花生、朱冬生,在改革中变了,《后传》中更是承包了别人不敢承包,看上去没收益的荒洲、池塘,动手改造,投下鱼苗鳖种,一举成了万元户。《柳林后传》第一章中,惠兰执意去喂湖鸭,而碧波荡漾中,湖鸭们戏水,扑打,又是一幅怎样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情景。这还在其次,年轻人的生活,谈情说爱、嬉戏嬲打,抑或含而不露、欲言又止——如惠兰明明走到心爱的人的身边,却又胆怯了,换上了另一句:“我从这里路过,采几朵野花……”将情感波澜掩盖。读到此,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情感的含蓄、升华,无疑更是一种美。然而,《后传》无疑也是一曲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挽歌。进入第二章,县城那种进步与落后的交错,那种鱼龙混杂,已开始让人喘不过气来。下面的章节更是如此。莫非,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么些年,我们付出了生态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代价是否太大了?在《后传》中,已经有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有了相应的情节与场景,不失为一大亮点。不过当时,作者不可能就此深化下去,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此。
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胜利”,为我们揭示出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或者章太炎所说的“俱分进化”。科学技术与道德文化的进步,未必是同步的,亦可能一进一退,科学的发展甚至会造成道德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从《柳林后传》,回溯到《前传》,再往前,则是《湖边》,还有其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同样是农村,愈往前追溯,父子二人笔下的农村愈是清秀、明丽。
当年的评论言犹在耳: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周健明的《柳林》系列,无疑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封建宗法关系的批判与对普遍异化的警惕——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充满悲剧性的冲突,表现出一种温厚的、历史的而不只是拘于道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人的尊严、审美情趣以及自然生态的向往,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假、丑、恶以及可悲的人的依附,还有物化的种种负面现象。
近几年,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创作,似乎远不及纪实作品丰富,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纪实作品引起的反响迄今仍在发酵。在这些纪实作品的参照下,人们自然会关心,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是怎样的?当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怎样的隐患与欠缺?今天,哪些前进了,哪些倒退了,哪些坚守了,哪些放弃了,甚至哪些失去了、破坏了,一去不复返了?《柳林后传》及《柳林前传》提供了最鲜明的、也最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作者:谭元亨,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良生,系华南理工大学博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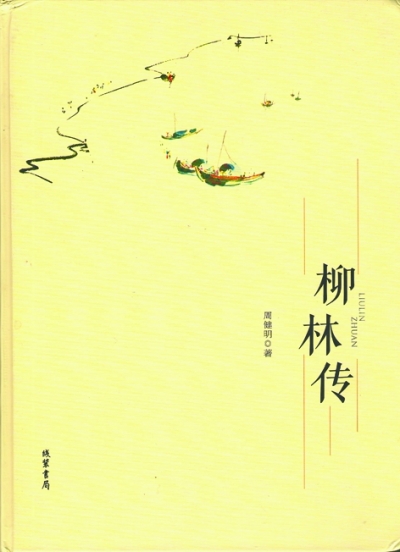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