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挂着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权威、九十六岁的张世英先生给我写的条屏:“超越现实只有两条:诗和哲学。”这是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话。在精神的自由王国中,诗和哲学乃至宗教都是相通的。诗,是人精神皇冠上的明珠。张先生勉励我,做美学研究,不能忘记诗。
诗的力量是巨大的。读先秦文章,《左传》之类的历史著作记载着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的历史,而《诗经》不啻为那个时代心灵史的记录,它使我们在朝代更替、钩心斗角之外,又能聆听到那个时代青春的声音。读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样的诗句,突然心敞亮许多,觉得人世原来如此美好;读“荏苒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警句时,有一种切理厌心的通透,瞬间里,自己的心灵也似乎变得柔软起来。
诗是美好的,它是天国的逸响,触及人的生命深层。古往今来留下来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多半是诗人在惨淡遭际中抽绎而出的。诗能穿透时间的帷幕,将千年之前曾经有过的欣喜和感动,在一个片刻降临到你的心扉。读“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生命脆弱所带来的惆怅一下涌起,在惆怅中体会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或许能坚定你汇入这个世界的决心。
诗,是人精神书写的简洁化表达。不要总将它看作无病呻吟、絮絮叨叨。我们国家的哲学常常是以诗书写的,我们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诗缔造的。我在做中国传统艺术研究时,深深感到,中国艺术其实就是诗的变奏。没有诗,我们的文明将是暗淡的。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文明基因,它是一种无形的维系,将上下四方、古往今来裹为一体。阳春助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我们无时无刻不沐浴在诗意的氛围中。
诗,是自我的吟咏。有人说,这里多半是逃离现实的遁词。但在我看来,诗,非但不是躲在自己篱墙内的孤独吟唱,而是汇入到更宏阔世界的必然进阶。读诗,爱诗,培植诗的情怀,点亮心灯,汇入到天地间无限的光明中。诗,往往被视为不切实际,是出离现实后的清唱,似乎总带有空幻不实的意味。但细细想来,难道我们天天纠缠在现实的功利中就是关心现实,计较着与自己相磨相戛的利益就是脚踏大地?诗,使人跳脱现实的漩涡,更好地俯瞰现实和人生,在变化的世界表相背后,看那不变的真实。“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样的诗,似乎给我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门。
诗,常常和感伤联系在一起。“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读之使人情动;“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回味让人情迷。然而,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我们的感觉加速钝化,甚至没心没肺成为流行色,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敏感,面对寸断柔肠,也能漠然处之。这样的当下,是需要诗的。当一个生命没有诗时,有些东西就开始枯萎了。你不一定成为诗人,但不能丢失诗的情怀。宇宙生命是以诗写成的,没有诗,天地将失落光彩。当一切都以物质的价值来衡量时,当面对生命的凋零无动于衷时,当垂暮的气息笼罩着少年的面庞时,当污秽的语句从曼妙的身体中传出时,我们知道,这时候,是需要诗来出场了。识字不等于识事,知识不等于智慧,油脑肥肠并不决定生活质量的提升。其实,诗,不是让你颓废,只是让你恢复被物质洪流夺去的动能。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但我们必须首先有这个意愿。
宝宝念诗,与其说将诗性种在幼年的心灵中,倒不如说发掘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诗的基因。脱略外在大叙述,激活孩子心灵深处的言说系统,抖落文明中附带的虚与委蛇,以天真、平和与开朗去塑造生命。世味年来薄似纱,从孩子做起,或许能让未来多一些理想。一个诗意的时代,一定是有意味的时代;一个诗意的人生,是可以期待的人生。可胜兄要做的,就是在这开始处用力,在起点里立意,在还没有很多尘染的时候,呵护真性的因子。人在这世界上,不可能不被染,或净染,或污染,读诗,其实就是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清净,给这场生命的拔河送去赢的力量。
(作者:朱良志,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为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韩可胜等著《诗词日历》《最美的节气诗词》等丛书的总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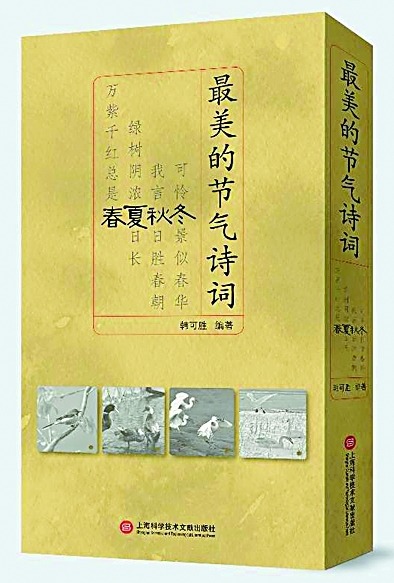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