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历史人物,因他们的出现,历史发生了改变,所以人们难以忘怀;又因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按常理出牌”,导致评价不一。书写历史绕不开他们,绕开了,许多历史说不清;研究他们,难以走近,又唯有走近。谈这样的话题,与笔者最近读的一部书有关: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写张学良没有不想走近张学良的,可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万花筒,人生大起大落,所行多系大是大非,而在人们眼里,是非又多模棱两可、正误难辨,主要因为他身上的颜色太杂,可谓“色色俱全。有蓝色,他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有红色,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有褐色,他崇拜过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有粉色,‘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面对这样一位历事复杂、色彩纷呈的人物,如何才能走近?怎样才能算走近?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须找到他的人生底色,唯有找准他的人生底色,方可走近。”什么是他的人生底色?作者开门见山:“思想是他的人生底色。”“张学良是个传奇人物,使他成为传奇的首先是他的思想,搞清了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再看他身上的五彩缤纷,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说‘他是个怪人’,究竟‘怪’在哪里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一般传记的传统写法,既没有依时记事,也没有择“色”分描,而是独辟蹊径,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他用一生搭建的思想舞台”上。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的思想、个性,带有鲜明的双重色彩。“有时他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有时他钻进了传统的象牙塔,拉都拉不回来。严格说来,张学良既是历史传统的传承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样,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两种偏执者的反对。”
同情的理解是历史学本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了贡献,却遭到幽禁5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而需要同情。正如近代学人陈寅恪所说,研究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当然,“同情的理解”,强调的不是张学良说什么就信什么,做什么就赞同什么,而是与之“同行”,了解他当时何以那样思那样行,避免的是“空间错位”带来的误读。
“同情”是为了缩短史家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离开了对张学良所处时代的了解和处境的同情,就不会有主动地走近,不走近就得不到历史的真实,离开真实,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就是一句空话。同情的理解只是走近历史人物的进路之一,而走进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必由之路。试想,如果我们离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还怎么理解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离开了对杰出人物的同情和理解,还怎样去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呢?
走进传主所生活的群体,对张学良整个人生做系统考察。
“任何人都生活在由群体构成的生态圈之内,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不了解东北人、东北军乃至当时中国人的所思所盼,就无法读懂张学良。”忽略了东北人恨日情绪和东北集团内部“老派”“士官派”对张学良的影响和掣肘,很难说清楚他在东北易帜问题上的“草率”;听不到东北军“少壮派”和西北军民的“杀蒋”呼声,很难理解他只身送蒋的“鲁莽”。作者的研究脉络并不局限于张学良个人,而是把他置身于所在群体之中,置身于民国政治漩涡之内,置身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空之中去做多角度考察。
研究张学良,不仅要研究他身边的一群人,还要把他的重大言行作为一生的组成部分做整体考量。“历史的真实是由具体的真实链环构成的复杂链条,而这个链条是不可割裂的,单独拿出任何一环,极易陷入众盲摸象的误区。只看局部,象的腿若柱子腹如鼓,并不为错,可用之以言象之整体,得出的必然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颠倒是非”。如果只截取“九一八”一段历史,不与后来的“双十二”联系起来,他就是个“孬种”;如果只看他临潼捉蒋,隐去此前的劝谏、苦谏、哭谏环节,隐去他晚年的“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那么做”,自然可以说他是“逞一时之勇”。但他的传奇并非仅凭勇气。“采用‘重点截取’法确实较为简便,不过,这样做极有可能陷入历史片面论的窠臼。”所以作者要求自己:“每写一事,要从清朝的奉天府放眼到美国的夏威夷。”
走进张学良的内心世界,理性分析张学良所说的话。
人的内心世界属于私密空间,探知尤难。为此,作者不仅阅读了各种版本的张氏传记、文电集、日记,还广泛搜集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书信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张学良口述的重视。张学良看写他的书时常常说:“他又不是我,他怎么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幸好,张学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口述资料,作者参加了存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145盘口述录音的整理,这种得天独厚的学术经历为此书增色不少。
运用传主口述探索传主内心世界是本书的亮点。“口述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谈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不管其他史料如何记载,都属间接材料,只有他自己说,才是第一手。”大量口述史料的入书,澄清了诸多迷雾。如他何以放弃“东北王”不做,甘心向南京政府“俯首称臣”?日本和他有杀父之仇,执政之后为何打苏联?他谈“九一八”时为什么说“怎么不想打,打了会更糟”……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人生,有怎样的人生也就有怎样的思想。”张学良的思想曲折、复杂,甚至混乱,任何研究只能研究其一部分,史家的选择最见功夫。作者专以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之形成与演变为研究对象,进而得出结论:“他的思想人生如同一条不靠岸的船,在以中西文化为两岸的风口浪尖上漂泊、挣扎,因不被时人理解而孤独,又因‘毁誉由人’‘但求无愧我心’而享受孤独。”这样写,既突出了人生的思想性及解读人物的方法论意识,又恰当地概括了最能反映张学良人生本质的思想特征。
这是一部思之有深度,读之有美感的书。其深度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探底,其美感在于文字表述的轻巧。论述结合,见解独到,不为尊者阿,不为尊者讳,对张学良时而“豪气冲天”“敢把天捅个窟窿”的冲动,时而“优柔寡断”“一个稻草人就会挡住去路”的懦弱秉笔直书。
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史学智慧与现实关怀、思辨色彩与“工文”散笔相映成趣的学术著作,堪称一部深入了解传主和弘扬正能量的力作。
(作者:毕万闻 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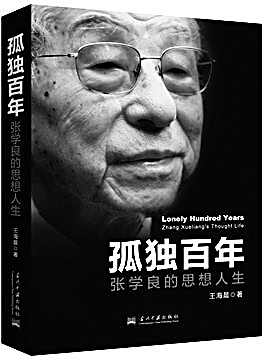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