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耸古今 星光耀中西④——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
海涅有一句名言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可谓至高评价。然而,与另两位同年逝世的大文豪相比,塞万提斯在世时既无莎士比亚的“闻达”,亦无汤显祖的“潇洒”。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生前从未享受过大作家的荣耀,塞万提斯身后却因其创造的骑士堂吉诃德形象而享誉全球。
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说“作家的笔高于作家”。这是有道理的。他指的是优秀作家会超越自己的偏见,达到艺术的抽象和具象、升华和净化。换言之,作家是人,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和时代社会的制约、生老病死的牵缠,但作家的作品却可以塑造完美,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物得到永生。
有心栽花
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塞万提斯最初的梦想是成为诗人。他创作了一首长诗《帕尔纳索斯山之旅》,以及无数短歌和十四行诗。后者大都散佚。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
这是诗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总结。但他所说的“老天无情”,首先是文坛泰斗洛佩·德·维加的鄙夷,其次是时人——读者的疏虞。且说前者对塞万提斯横挑鼻子竖挑眼,谓“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这在当时无异于“死亡判决”。
洛佩虽然比塞万提斯年轻15岁,却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连塞万提斯本人也对其赞颂有加。巧合的是两位作家曾为邻居,一度同住弗朗科斯街(今塞万提斯街),一个在今11号的位置,另一个在今18号的位置,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更加凑巧的是,二人都曾是喜剧演员赫罗尼莫·委拉斯开兹家的常客。洛佩屈尊降贵是因为委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名伶埃莱娜·委拉斯开兹;而塞万提斯所以踏破门槛的原因,却是推销作品。更巧的是,塞万提斯一家墓地所在的坎塔拉纳街如今成了洛佩·德·维加街。此外,二人曾两次在相近的时间参加相同的教团,还曾先后或同时服务于莱莫斯伯爵和“无敌舰队”。至于二人的创作道路,则更是出奇的雷同:涉足所有的体裁,尽管效果大不一样。可怜的塞万提斯生前从未享受到大作家的荣耀,并且可能至死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洛佩何以轻而易举地在文坛独占鳌头。
戏如人生
作为剧作家,塞万提斯同样没有获得期望的成功。塞万提斯在《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的序言里历数西班牙戏剧传统而聊以自慰,说:“我头一个大胆地将五幕剧变成了三幕剧,而且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想象和隐情。我还把伪道士搬上舞台并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写了数十个剧本,却从未在舞台上丢人现眼,也没有人对它们喝倒彩、扔垃圾……后来我诸事缠身,不得不离弃戏剧,却冷不丁冒出个大自然的怪物来——洛佩·德·维加。他在喜剧王国一统天下……”
众所周知,喜剧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主要体裁。它无疑是资本的温床,甚至一直是资本主义快车的润滑剂,其对近现代文学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它甫一降世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神学的庄严,扫荡了封建残余。它在嬉笑怒骂中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理性和文化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而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载体,喜剧无疑也是市民文化首要表征。关于这一点,早在14世纪初,但丁就曾有过描述。具体说来,他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物欲和狂妄自大。果不其然。未几,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无所不能,薄伽丘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人间喜剧”《十日谈》,拉伯雷则用大话式的狂欢将神话中的巨人和教会踩在脚下。15世纪初,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16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畅快的笔调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那样东西”。直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有莎士比亚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里左右开弓,并以充满批判精神的几大悲剧(对金钱、社会、人性的批判)使自己成为经典;而塞万提斯却通过否定之否定,即反狂欢的狂欢、反喜剧的喜剧——《堂吉诃德》——展示了日下世风和遍地哀鸿。某种意义上说,塞万提斯侥幸存世的八出喜剧和同样数目的幕间短剧最是吻合他的人生:艰难时世中顽强拼搏,身残志坚、做过奴隶,事事不顺、三陷冤狱,锲而不舍的苦中作乐——泪奔并苦笑着。
无心插柳
《堂吉诃德》几乎是塞万提斯无心插柳的产物。塞万提斯命途多舛,出生在没落乡绅家庭,从小颠沛流离。弱冠之年在意大利驻防,并在一次抗击土耳其海军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回国时遭土耳其海盗袭击,被虏至阿尔及尔为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西班牙,却屡屡为生计所累,还多次因莫名其妙的官司锒铛入狱。《堂吉诃德》正是在狱中构思的,而创作这部小说竟是在一间四面“漏风”的小阁楼里: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
四百多年来,有关《堂吉诃德》的价值早已是众说纷纭。最早的评价来自同时代文人,其中洛佩的嘘声和判决奠定了负面基调。而笑声则是一般读者给予塞万提斯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便是视其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世纪、启蒙运动的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世纪,但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继续面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接受与评骘。先是英国翻译家彼得·莫特乌斯开启了正面评骘的先声;但紧接着,法国翻译家阿兰-热内·勒萨热反戈一击,否定了彼得的看法。塞万提斯必得等到19世纪才因浪漫主义而扬眉吐气。浪漫主义定塞万提斯为一尊,对《堂吉诃德》可谓推崇备至。德国作家先声夺人,于1800年和1801年率先推出了两个版本。首先是施莱格尔兄弟,继而是谢林和海涅。与之遥相呼应的当然还有英国诗人拜伦等。他们对《堂吉诃德》的高度评价一扫笼罩在塞万提斯头上的阴霾,并奠定了塞万提斯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本土的塞万提斯研究迅速升温,并在生平和版本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此后,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塞学展示了新的维度。司汤达、屠格涅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将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研究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而,20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批评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了挤压;但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强劲,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塞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环或一隅,变得越发的汪洋恣肆,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又何啻五花八门!
降临中国
虽然塞万提斯戏说其小说得到了中国大皇帝的赏识,谓后者急于让他来做西班牙语文学院的院长并用《堂吉诃德》做教材;他甚至在第二部中让堂吉诃德胡诌了一个叫安赫丽卡的美人,还让她“即位做了中国女皇”,但事实上,不仅他的中国梦未能做圆,就连他的作品也姗姗来迟。
1918年,周作人率先在《欧洲文学史》中对《堂吉诃德》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介。1922年,林纾、陈家麟翻译的《堂吉诃德》第一部——《魔侠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9月,周作人撰文介绍《堂吉诃德》,并将屠格涅夫的观点引入中国,认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哈姆雷特)代表怀疑与分析”。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周作人后称《堂吉诃德》是他“很喜欢的书”,“随时翻拢翻开,不晓得有几十回,这于我比《水浒》还要亲近”。
鲁迅对《堂吉诃德》的接受与周作人相仿,他不仅一直珍藏着“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而且自20年代起陆续收集了好几种日译本。鲁迅的阿Q(《阿Q正传》发表于1924年)则被认为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或谓反堂吉诃德:一个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反堂吉诃德。且阿Q的“Q”恰好是吉诃德的第一个字母。
鲁迅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并说“后来又有人和这些专凭理想的堂吉诃德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马克思式’”。同时,他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一个“可读的”《堂吉诃德》译本(当时行世的唯有《魔侠传》,但30年代接连出版了四种新译本,即1931年开明书店的贺玉波译本、1933年世界书局的蒋瑞青译本、1937年启明书局的温志达译本和1939年商务印书馆的傅东华译本)。而这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作家正冷嘲热讽地攻击鲁迅为中国的吉诃德先生。鲁迅于1932年撰写了题为《中华民国的“堂吉诃德”们》的杂文,之后又于1933年和瞿秋白一同发表了《真假堂吉诃德》,对某些口头英雄及其精神胜利法进行了抨击。与此同时,鲁迅还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译出了第一章,后者从俄文译出了全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瞿译《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事实上,问题既不在骑士道,也不仅仅在打法,而是在于理想主义的脆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任何萦纡的道论都一样乏力。
为了团结鲁迅,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前去做两社的工作,于是围绕“中国堂吉诃德”的交锋宣告终结。较之两社的冒进,鲁迅显然“太文学”;而周作人则更是书生气十足了。后者除了自己在著述中倾情介绍《堂吉诃德》,还深刻地用堂吉诃德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其中,废名就曾以小说《莫须有先生》模仿了《堂吉诃德》。
一晃近百年过去,而今又有三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陆续问世,我们或可使塞万提斯这杆“精神之矛”焕发出新的光芒:在道与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天平中成为某种积极的砝码。
说到《堂吉诃德》在中国,我们不免想起杨绛先生。前不久,她以105岁的高龄在京仙逝。她翻译《堂吉诃德》这段故事便再度被人提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杨绛版《堂吉诃德》固非无懈可击,但它确实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首先,杨绛先生的小说翻译深得朱光潜、林默涵等人的推崇。正因为如此,当上世纪50年代由中宣部牵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几个外国文学研究室(1964年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的“三套丛书”工程启动伊始,林默涵同志便将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了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几种译本,发现彼此并不一致,于是颇为踟蹰。为保证忠实,她考虑再三,终于决定直接从原文翻译,并下决心自学西班牙语,而且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塞万提斯专家马林版注释本。她边学边译,边译边学,每天只译几百字,以便反复推敲。其次,在“洗澡”般的政治运动中,她不得不时常放下译笔,直至深陷“文革”乱境。令人慨叹的是,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她也没有放弃《堂吉诃德》,没有放弃学西班牙语。正所谓苍天不负有心人,“文革”结束后,杨绛先生重拾译笔,历经22年,终在1978年出版了《堂吉诃德》。而她的执着成了我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上世纪末,痛失亲人、年事已高的杨绛先生对于有人指摘的“误译”并未刻意解释,只是在再版时又参照两个原文本改易了一些字词和语句。作为她的晚辈同行,我一直感念她的历史功绩,感佩她的非凡毅力。她的一些译法(无论归化、异化)皆值得尊重,一些“误译”则是可以商榷的。然而,早在后辈质疑她的译文之前,她就“从实招来”,写过《失败的翻译》等心得文章,认为翻译实在是一件“一仆二主”的苦差事——既要对原文这个老主子忠心耿耿,又要全心伺候读者这个新主人。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却是翻译永无止境,因为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人的一生又有几个22年可以付出呢?
无论如何,杨绛先生功不可没,她的译本推动了《堂吉诃德》在我国的传播,也在诸多方面为后译提供了可资借鉴之法。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迄今累计发行近百万册。尤其是杨译本文字晓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了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了西班牙汉学家的称赞。杨绛本人则因为翻译该书,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
经典现状
今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三位世界级的大文豪共同逝世400周年,国内外都展开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然而,我们对于经典的阅读情况却不容乐观。且不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处于世界中下游(2016年“世界读书日”公布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人均年读书量不足5种),较欧美国家和亚太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同时,青少年的电子阅读量虽迅速飙升,但其内容多为快餐类作品和网络闲聊,即主要属轻阅读、浅阅读范畴,罕有经典上架。更令人瞠目的是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居然被称“死活读不下去”,而且在“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上赫然居于榜首。与此同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其做法无非是将它们剥离历史土壤,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至于《西游记》,尽管一直是我国少儿读物中的第一经典,却被反复恶搞。这令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颇为愤懑,以至于不惜“以身试法”、对簿公堂。
当然,情况远不止于兹。屈原遭到了“弗洛伊德的攻击”,成了“同性恋者”,于是其爱国主义精神被“恋君情结”所颠覆。此外,从杜甫到鲁迅,无数经典作家被或多或少穿上了小鞋。于是,经典作家作品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或染色体地位被彻底撼动,甚至颠覆。这当然不是个别文人墨客或影视大腕心血来潮、指点古今的结果,其背后是资本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强劲推动,也是“全球化”时代“去民族意识”“去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轻易瓦解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审美认同重要根基的文学经典,那不是犯傻或别有用心又是什么?
话说回来,颠覆“经典”的做法原是文学的本分。但这个“经典”始终是加引号的。譬如塞万提斯颠覆的“经典”是以消遣为目的的骑士小说。曾几何时,骑士小说和喜剧在欧洲风靡一时。从最简单的话说,骑士小说之所以风行欧洲,尤其风行西班牙,是因为王国的复兴或建立使骑士阶层完成了历史使命。骑士们被封官加爵,远离了金戈铁马、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成为新兴市民阶层梦想的归宿。后者正是“航海大发现”的精神基础。哥伦布所率领的西班牙冒险家并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大中华帝国”,只是阴差阳错到达了美洲,并误认为那是印度。稍后历任菲律宾总督的西班牙人一直觊觎富饶的中国,并多次上书国王派兵“占领”。只不过西班牙帝国早被野心所累,已然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但骑士梦想仍萦绕在西班牙市民阶层心中,于是,过去的骑士生活被逐渐艺术化。比如,多数骑士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手举剑、一手握笔,就是浪漫的冒险家;他们为了信仰、荣誉或某个意中人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往往孤军奋战、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同时不乏神秘色彩。塞万提斯则开宗明义,要用《堂吉诃德》来扫除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有害心灵的无稽之谈。于是,骑士小说被淋淋漓漓地戏说了一番。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孩子们看《堂吉诃德》会笑,而成熟的读者却每每在堂吉诃德的疯癫面前潸然泪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堂吉诃德的长矛》《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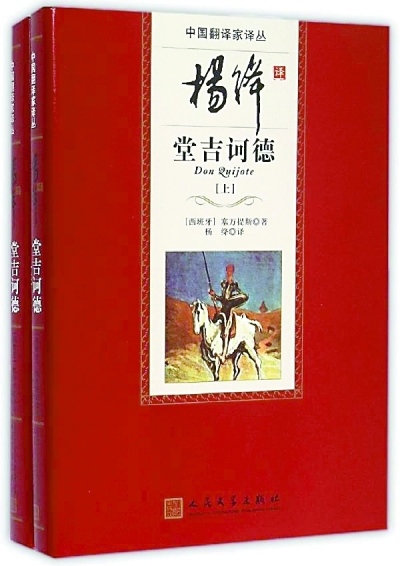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