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出版后,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和机关刊物《民间文化论坛》的极高评价,在此刊物2014年第2期的封2版面上刊登了幅红色的书影和一篇专门推荐评论这本书的文章,说“全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学派,网罗殆尽”。
后来我找来一本看了,发现此书存在问题,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提出我的一些具体意见。
一
我以为,一本学术史起码应该把100年来中国民间文学调查研究的历史进步轨迹的历程弄清楚,但是,此书并没有提出这个任务。为了达到这个基本要求,学术史应该以学术思想的进步、创新为线索,来组织篇章结构,以学术为主,而不能以人为主,而此书却是以人为主进行论述的。这样学术史就成了人物的历史,成了一部学术资料集。
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特殊在哪儿呢?作者说,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就表现在它是“不自觉的文学创作”,也就是“无意识的文学创作”。他说:“民间故事是一种有别于文人创作的创作,原则上说,它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创作。”所以反对“用思想性、艺术性、创作方法”的概念来分析民间文学,这当然取消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反对文学角度的研究,从而只肯定“民俗学派”。
不能讲思想性、艺术性,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去写学术史,还会否定民间文学的社会作用,否定革命的民间文学。
此书在谈到延安学派时说,何其芳、林山、周文等人的延安学派,只重视文学,所以“有严重缺点”。对此派基本上是否定的,并且讲的很少,似乎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了,甚至连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都没有提。对贾芝同志这样的重要人物,也不怎么提,甚至说50年代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极左”,用“基本上堕入了庸俗社会学和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否定。民间文学几千年来就是人民革命的斗争工具,红色歌谣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怎么能够随便否定呢?这是不科学的。
对民俗学派则评价很高,说“民俗学派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至今仍然活跃于学坛上的流派(学派)”。相比之下,这当然也是取消民间文学文学性的一种表现。
作者在《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还有一段话说得更清楚,“不幸《歌谣周刊》刊行的动机是由于少数文学家的一时高兴,并且是偏重在文艺方面找材料”“到了广州又有《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而投稿的依然偏重在含有文艺性的歌谣、故事或传说,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因为作者只强调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史价值”,所以对胡适1936年主持的北大《歌谣周刊》复刊后,朱自清、朱光潜等许多人的文学研究,都是否定的,说:“在方法和研究水平方面,说不上有什么大的进展。”
二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对许多重要人物有重大的缺漏。
例如蔡元培,书中只肯定他支持搜集歌谣,一带而过。但蔡元培在民间文学、俗文学、民俗学、人类学四个学科都有许多杰出的贡献,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有巨大的影响。我曾经花大力气写过几篇长文——《蔡元培先生与民间文学》《蔡元培先生与俗文学》《蔡元培先生与民俗学》《蔡元培先生与人类学》,用大量资料证明蔡元培在国外留学学的并不是哲学、教育学,而是人类学。如此重要人物的学术成就,一点不写,实在是重大的缺漏。
鲁迅先生的《不识字的作家》,是一篇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章,全面论述了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在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是这本书,却对民间文学这样重要的纲领性文章,一点不讲。大概讲民间“作家”就是讲“文学”了,当然与他的学术史无关。何况晚年的鲁迅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民间文学,就更不值一提了。
在民间文学理论上,应该有民间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理论,学术史不能不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间文艺学在本体论方面有重大的创新,突破了过去民间文学三大性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对此,车锡伦教授认为立体性理论已经在学界成为共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民间文学的主讲教授陈劲榛先生写了两篇长文,研究立体性和立体思维,认为是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主要创新。可是,此书却完全看不到这些本体论创新价值的具体内容。
在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对多种民间文学调查研究方法有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方法”,对调查中如何保存活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面貌,做了具体的分析。这是方法论上的重大理论创新。这种方法论的创新,在1981年的《加强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一文中,就有了具体论述。此文曾经被贵州、广西、青海等地民研会的刊物所刊载。后来,“要使人看到活鱼,而不是鱼干儿”的民间文学调查记录要求,已经深入人心。贾芝同志在云南山区曾经听到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说过这句话,认为很好。这说明立体描写的方法论影响深远,可是此书中却完全没提这样重大的理论创新。
三
书中存在一些知识性错误和缺陷。
例如,把谭达先的《民间童谣散论》说成是天鹰的作品;把文人的隐语说成是民间谜语;把文人的词也都说成是民间文学;不知钱毅是阿英的儿子;不知《民间文学集刊》是贾芝同志主编的,更不知这个刊物出了三期就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冯雪峰要解散民研会,而说它“因为抗美援朝而停刊”。
我记得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同志说过,民间文学与文人作家的创作不同,就在于它没有现成的书,要下去调查记录的。贾芝同志也非常注意民间文学这个活态文学的特点。而这部学术史中,却往往只是罗列书目,不谈如何记录,也不谈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者。
例如,不知阿凡提故事的调查记录和翻译者赵世杰等同志和新疆出版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论文集》,此书有文章批评“西方喜剧美学有严重不足”的学术创新,1984年和1987年曾受到国际学术组织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而此书却一字不提;此书不提北大中文系和北大民俗学会进行民间文学实习调查的重要实践;不知北大与民研会合作编辑出版的三大本《中国歌谣资料》和十几本油印资料。
更大的缺漏是,此书完全不提1978年10月在兰州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与学术讨论会。而这是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大发展的光辉起点。
该书作者曾在会上呼吁“建设我国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作者没谈过。而在学术史中,这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学术事业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一定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用真正的科学标准去衡量,才是可靠的。我愿意坚持这个标准,欢迎不同意见的争鸣。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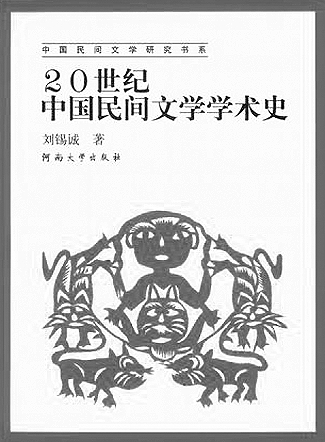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